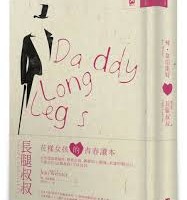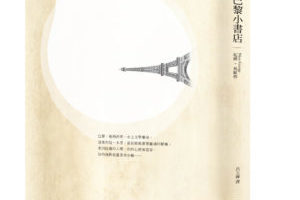童年
1
莉拉出現在我生命裡是一年級的時候。我馬上對她印象深刻,因為她很壞。
在班上,我們每個人都有點不乖,但只有在導師奧麗維洛沒看見的時候才耍花招。可是莉拉不同,她隨時隨地都很壞。
有一次,她把吸墨紙撕成一小片一小片,泡進墨水裡,然後用筆撈起來,丟到同學身上。我的頭髮被砸中兩次,白色的衣領也被丟中一次。老師一如既往扯開喉嚨,用我們很害怕的那種像針般又尖又長的聲音叫她去黑板後面罰站。
莉拉理都不理,甚至一點也不怕,還是不停丟著浸滿墨水的紙片。
奧麗維洛老師在我們眼中是個很老的胖女人,雖然她當年頂多四十出頭。她從桌子後面走過來,想狠狠修理一下莉拉,卻不知道絆到什麼東西,一個踉蹌,失去平衡然後跌倒,臉撞上桌角,躺在地板上,像是死了。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我並不記得。我只記得老師那一團黑黑的,一動也不動的身體,以及莉拉盯著她看的嚴肅表情。
我記得太多這類的意外了。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裡,大人小孩都經常受傷,傷口會流血,化膿,有時候還會死掉。
賣蔬菜水果的阿珊塔太太有個女兒踩到釘子,得破傷風死了。
斯帕努羅太太的么兒因為格魯布性喉頭炎而死掉。
我的一個表哥二十歲的時候死了,因為那天早上出門搬瓦礫的時候被砸了,當天晚上就耳朵嘴巴冒血而死。
我外公是從建築工地的鷹架上跌下來摔死的。
佩盧索先生的父親少了一條胳臂,因為一不小心被車床給軋到了。佩盧索先生的太太姬塞琵娜,她姐姐得了結核病,二十二歲就死了。
阿基里閣下的大兒子——我從沒見過他,卻好像記得他——上戰場打仗,死了兩次;先是在太平洋淹死,然後又被鯊魚給吃了。
梅契歐瑞全家人在大轟炸的時候驚恐尖叫,抱在一起死掉了。
老葛羅琳達太太死掉,因為吸進瓦斯而不是空氣。
我們上一年級的時候,四年級的吉安尼諾有天看見一顆炸彈,伸手去摸,就被炸死了。
和我們一起在院子裡玩的盧吉娜(也不算是玩伴啦,我們只知道她的名字而已)得斑疹性傷寒死了。
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充滿會要人命的辭彙:格魯布性喉頭炎、斑疹性傷寒、瓦斯、戰爭、瓦礫、工作、轟炸、炸彈、結核病、感染。就因為這些辭彙和那些年的經驗,讓我終此一生都懷著許多的恐懼。
你也可能因為那看似正常的東西而死掉。
比方說,如果你渾身是汗,沒先將手洗乾淨,就從水龍頭捧涼水喝,很可能會死掉:你身上會起紅疹,開始咳嗽,無法呼吸。
你可能因為吃黑莓沒吐籽而死掉。
你可能因為嚼美國口香糖,不小心吞下肚而死掉。
你可能因為撞到太陽穴而死掉。太陽穴是格外脆弱的地方,我們向來都很小心的,被石頭丟中就可能死掉,但是丟石頭又是司空見慣的事。
放學的時候,賣蔬菜水果的阿珊塔那個不知是叫恩佐還是恩祖席歐的兒子,總會領著院子裡的一幫男生,朝我們丟石頭。他們很不高興,因為我們比他們聰明。
石頭飛來的時候,我們都快快跑開,但是莉拉不這麼做,她還是保持正常的步伐,有時候甚至停下來。
莉拉很厲害,超會觀察石頭飛來的軌道,那種輕鬆閃避的姿態,如果是在今天,我就知道要形容為「優雅」。她有個哥哥,說不定她是從他那裡學來的,我不知道,我沒有哥哥,只有弟弟,從他們身上我什麼也學不到。
但是,只要一發現她落後了,我就會停下來等她,儘管我很害怕。
即便是在當時,我就已經不知為什麼,無法拋下她了。我和她不太熟,我們從沒講過話,雖然我們不管在課堂或課外,都不時較勁。很難以解釋的,我總覺得如果拋下她,和其他人一起跑掉,我身上的某個東西就會留她身邊,而她永遠不會還給我。
起先我躲在牆角後面,探頭看看莉拉來了沒。然後,既然她不肯讓步,我也只好勉強自己加入她的陣營。
我遞石頭給她,自己也丟幾個。但我其實沒什麼把握,我這輩子做很多事都沒什麼把握。我總是覺得,我的行為好像和我自己有點脫節。
但是莉拉不同,她從年齡還很小的時候——我沒辦法精確地說是在六、七歲,或是我們一起爬上阿基里閣下家樓梯的八歲快九歲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絕對堅定的個性。
不管手裡握著的是三色筆的筆桿還是石頭,或漆黑樓梯的欄杆,接下來要做什麼——把筆精準地戳進課桌木頭裡,丟墨水彈,把那些男生趕出院子,爬上阿基里閣下家的樓梯——她都半點也不猶豫。
那幫男生從鐵道的路堤發動攻擊,武器就是鐵軌路基的石頭。帶頭的恩佐是個很可怕的小孩,一頭金髮剪得短短的,眼睛顏色很淡。他起碼比我們大三歲,但是留級一年。
他丟的是個頭小,但邊緣尖利的石頭,而且丟得非常之準。但是莉拉總是等著他的石頭飛過來,再好好表現她的閃躲技術,這讓他更生氣,丟石頭丟得更凶狠。
有一次我們擊中他的右小腿,我之所以說「我們」,因為是我把一塊邊緣尖銳的扁平石塊交給莉拉的。這塊石頭像刀片一樣劃過恩佐的皮膚,留下一道紅色傷口,立刻冒出血來。
恩佐看著自己受傷的腿。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用拇指和食指夾住一塊石頭,準備要丟,他的手臂已經舉了起來,卻停住了,非常迷惑似的。他麾下的那些男生也不可置信地看著他腿上的血。
然而莉拉沒對自己的戰果表現出絲毫的滿意之情,彎腰撿起另一塊石頭。我拉著她的手肘,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肢體接觸,猝不及防,膽顫心驚的接觸。我覺得那幫人會更火大,所以想要徹退。
但是來不及了。恩佐雖然小腿流血,卻從恍惚的狀態醒過來,丟出手中的石頭。那塊石頭擊中她的頭,打得她從我身邊晃開。一秒鐘之後,她倒在人行道上,額頭有一道傷口。
2
奧麗維洛老師從課桌跌下來撞到頭那天,如同我之前說的,我以為她死掉了,在工作的時候死掉,就像我祖父和玫利娜的丈夫一樣。在我看來,莉拉也會因為自己招來的嚴厲懲罰而難逃一死。
結果呢?經過一段我也說不上來多久的時間——不知是短是長——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她們就只是消失了,老師和學生,兩人消失了好幾天,從我們的記憶裡消失了。
接著,一切都出人意表。奧麗維洛老師回到學校來,活得好好的,開始關心莉拉。我們以為她會懲罰莉拉,因為這是很自然的事。但她沒有,反而表揚莉拉。
這個新的階段是從莉拉的媽媽,瑟魯羅太太被叫到學校來的那天開始的。
有天早上,工友敲敲門,說瑟魯羅太太來了。倫吉雅.瑟魯羅走了進來,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讓人認不出來。
她就像我們街坊大部分的婦人一樣,平日裡總是邋邋遢遢,穿著拖鞋和寒酸的舊衣服,但這天卻穿上正式的黑色洋裝,提著閃亮的黑色皮包,踩著讓她腫脹的雙腳飽受折磨的低跟皮鞋。
她把兩個紙袋交給老師,一個裝著香腸,一個裝著咖啡。
老師高高興興收下禮物,看著低頭瞪課桌的莉拉,對她,也對全班說出了讓我極為不解的話。當時我們才剛開始學字母和1到10的數字。我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認得所有的字母,也知道怎麼數1、2、3、4到10,而且我寫的字常常得到讚美,甚至還得到老師親手縫的三色帽花。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儘管莉拉害老師跌倒送醫,但是奧麗維洛老師卻說她是我們班上最優秀的學生。
沒錯,她是調皮搗蛋。
沒錯,她老是往我們身上丟浸滿墨水的吸墨紙。
沒錯,若不是這女生這麼搞怪,身為老師的她就不會跌倒,傷到臉頰。
沒錯,她是常常不得不處罰莉拉,拿木頭教鞭打她,或罰她跪在黑板後面的硬地板上。
但是,身為老師,身為一個人,有個讓她喜悅萬分的事實,她幾天前不小心發現的驚人事實。
說到這裡她停了一下,彷彿言語還不足以形容,或者是她希望讓莉拉的母親和我們知道,這偉大的功蹟永遠難以用言語道盡。她拿起粉筆,在黑板寫了一個字(我其實不記得是什麼字,因為當時我還不識字,所以現在這字是我隨便亂掰的):「日」。然後她問莉拉:
「瑟魯羅,黑板上是什麼字?」
全班好奇地陷入沉默。莉拉要笑不笑,露出一臉怪相,身體往旁邊一歪,靠到顯然很火大的同桌同學身上。然後,鬱鬱唸道:
「日。」
倫吉雅.瑟魯羅看著老師,表情很遲疑,近乎恐懼。
老師起初不懂,為什麼她自己的熱情沒有映照在這位媽媽眼睛裡。
接著,她揣測,說不定倫吉雅自己並不識字,或者並不確定寫在黑板上的字就是「日」。
老師皺起眉頭,半是為釐清瑟魯羅太太的情況,半是為表揚我們的這位同學,所以對莉拉說:
「很好,黑板上這個字的確是『日』。」
接著,她要求莉拉:
「過來,瑟魯羅,到黑板這邊來。」
莉拉很不情願地走到黑板前面,老師把粉筆交給她。
「寫,」她對莉拉說:「『粉筆』。」
莉拉用顫抖的手,非常專心地寫,一個個字母高高低低的,寫出:「chak」。
奧麗維洛老師添上一個「l」,瑟魯羅太太看見老師修正這個字,很絕望地對女兒說:
「你寫錯了。」
「不,不,不,莉拉是需要練習沒錯,但是她已經會認字了。她已經會寫字了。是誰教她的?」
瑟魯羅太太垂下眼睛,說:「不是我。」
「但是在你家,或你家的那棟樓裡,有沒有人可能教她?」
倫吉雅不太肯定地搖搖頭。
於是老師轉頭看莉拉,用非常真心讚賞的語氣,當著我們所有人的面問她:「誰教你認字和寫字的,瑟魯羅?」
瑟魯羅,這個黑髮黑眼,黑罩衫領口有條紅緞帶,年僅六歲的小女生回答說:「我自己。」◇(節錄完)
——節錄自《那不勒斯故事》/大塊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