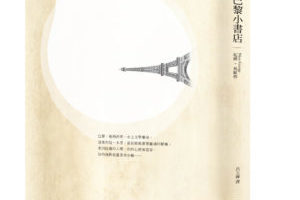蘇東坡的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這座人潮似海的巍巍大城,真能藏住所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還是就像籠罩城頂的霧霾一樣,人們只能避它防它,束手無策?
該做好人還是壞人?霧霾深罩的北京城,上演著不見天的罪與罰。
──《王城如海》
幽嚥如訴的胡琴曲〈二泉映月〉響起,表情狂亂砸家什的余松坡逐漸平靜,緩慢步入臥室安睡。北京做為中國的首善之都,既是歷史古城,也是政經巨邑,千千萬萬的鄉下青年進京後,委身於逼仄的陋室內,成為蟻族,維持最低的生活需求,只為在首都中佔得一席之地,力圖他日的功成名就。余松坡也曾是千萬人中的一員,為求前程費盡心機,如今做為海外歸國成功人士,原本是票房毒藥的舞臺劇導演,此次的《城市啟示錄》卻空前叫座,但也因為演員對「蟻族」青年流露出鄙夷的神色,引來輿論的撻伐。鋒頭正健的余松坡,因遇見在天橋販賣新鮮空氣的痴傻流浪漢後,勾起昔日鄉下往事,引得他夢遊症又犯了,只有〈二泉映月〉能安撫噩夢,這首曲子背後,究竟有什麼祕密?
羅冬雨身為余松坡因霾害為氣喘所苦的兒子的保母,她讓同是鄉下進京的男友與弟弟繞著余松坡的生活打轉,他們的朋友因為霧霾視線不佳車禍喪命,女友為當舞臺劇演員寧願脫衣接受潛規則。然而北京正是靠著這群鄉下人,維持京城的氣派,他們的苦處被這座妝點得繁華明豔的城市隱沒。一個偶然,壓抑的青年抓住了機會,準備揭開華麗面具下的黑歷史。「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這座人潮似海的巍巍大城,真能藏住所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還是就像籠罩城頂的霧霾一樣,人們只能避它防它,束手無策?
繼《耶路撒冷》後,最受期待的青年小說家徐則臣,將視角從「走向世界」的京漂族移到北京海歸派。透過主角導演的舞臺劇探討北京城的本質,巧妙地將城市個性、霧霾聯結謀求功名的真實人性。全書故事僅短短數日,卻羅織了層層相疊的往日雲煙,不堪的祕密,不安的靈魂,上演了一則罪與罰的現世寓言。
【作者簡介】
徐則臣
一九七八年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現居北京。
著有《午夜之門》、《夜火車》、《跑步穿過中關村》、《居延》、《到世界去》等。
【主文】
合租客甲 從前有個人,來到一片茂密的森林,想栽出一棵參天大樹。
合租客乙 結果呢?
合租客甲 死了。
合租客丙 該。
合租客甲 他又栽,死了。他還栽,繼續死。他繼續栽,還死。再栽,再死。
合租客乙 上帝就沒感動一下?
合租客丙 你看,想到上帝了。為什麼一定得想到上帝呢?
合租客甲 上帝沒感動,上帝看煩了。他說你為什麼不試試種點草呢?
合租客乙 跑森林裡種草?頭腦被上帝踢了?
合租客丙 他種了沒?
合租客甲 他彎下腰,貼著地面種出了草原。
——《城市啟示錄》
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先是脖頸處薄薄地一凜,然後才感到線一樣細長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風穿過洞開的推拉窗吹進來。他咳嗽一聲,肥壯的血紅蟲子從脖子裡鑽出來,緩慢地爬過鏡子。余松坡抽紙巾捂住了傷口,抹掉剃鬚泡沫,腦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個人在花園旁邊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對方的裝束,那個男人已經消失在霧霾裡。
能見度一百米。天氣預報這麼說的,中度轉重度污染。
余松坡覺得氣象部門的措詞太矜持,但凡有點科學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夠用的。能見度能超過五十?他才跳幾下我就看不見了。他對著窗外嗅了嗅,打一串噴嚏,除了清新的氧氣味兒找不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
一刻鐘前他醒來,躺在床上打開手機,助理短信問:PM二點五爆表,預約的訪談照常?他回:當然。只能照常。霾了不是一天兩天,一爆表就不幹活兒,現在就可以考慮在家裡養老了。
他拉上百葉窗。霧大霾重天冷,擋住一點算一點,然後去廚房看另一扇窗。
那人先砸碎的是廚房那扇窗。衛生間的門和廚房都關著,聽著聲音悶悶地遙遠,余松坡沒當回事,他早把砸玻璃從現代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麼年代了,誰還玩這種粗陋幼稚的把戲。他撅起下巴,讓吉列剃鬚刀繼續往下走。然後衛生間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
羅冬雨穿著睡袍走進廚房,余松坡正在比畫窗戶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間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跡,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頭還齊嶄嶄地留在那裡,茬口切割一般的整齊。
羅冬雨打了個哆嗦,把睡袍的下擺裹緊了,遮住露出來的一線光腿。她醒來是因為余果咳嗽。這孩子對霧霾和冷空氣都過敏,一有風吹草動就咳。咳嗽第一聲羅冬雨就醒了,下意識地看窗戶和空氣淨化器。
窗戶緊閉,空氣淨化器還在工作。但余果還是空蕩蕩地咳。聽不見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她聽見廚房的門響,穿上睡袍就起來了。果然是冷風和霧霾。
「待會兒就收拾。」她說的是地上的碎玻璃。
「保留現場」,余松坡說話的時候能感到喉結在手底下艱難地蠕動,「出現了恐怖分子。」他想把這個清早弄得輕鬆一點。他很清楚,這幽默不是為了寬慰羅冬雨,而是緩解自己的焦慮。
惹事了。但他搞不清惹下的事對正在演的戲和自己的藝術生涯有多大影響。他確信自己是個優秀的戲劇導演,他也確信自己不是一個優秀的戲劇演員,他的表情已經跟剛才的幽默貌合神離,所以他如實地補了一句,「有人砸了咱們的窗戶,我馬上報警。」
他把紙巾從傷口上拿下來,血還在往外滲。
「我去拿創可貼。」
羅冬雨轉身去找藥箱。睡袍擺動,余松坡看見她光裸圓潤的腳後跟。他把廚房的百葉窗也拉下,霧霾鎖城,兩個好看的腳後跟是多麼奢侈。
從房間裡出來,羅冬雨已經換上了家居服。她在穿衣鏡前給余松坡貼創可貼。先用酒精棉球消毒,余松坡痛得暗暗抽冷氣。他仰著脖子,目光向下只能看見羅冬雨頭髮縫中白淨的頭皮。沙宣洗髮水的味道。
不管他和祁好用什麼牌子的洗髮水,羅冬雨都堅持用沙宣,她自己買。散發著好聞味道的黑髮中間那道筆直的頭縫,讓余松坡發現了別樣的性感。他突然想抱一抱這個在他們家做了四年保姆的女孩子,或者被她抱一抱。跟欲望無關,是脆弱。
好女人總能讓男人感覺自己是個孩子。他有點覺得自己不容易了,媒體和輿論對他的新戲似乎已經不是感不感冒的問題了。
「該嫁了,小羅。」他說。
「等一下。」羅冬雨說。她是讓他別說話,喉結上下躥動影響她操作。
余果在咳嗽。她把創可貼的兩端按了一下,去冰箱裡取出昨天調製的蘿蔔蜂蜜水。霍大夫說,別沒事就給孩子吃藥。
兩周前她和祁好帶余果去看傳說中的中醫霍大夫。余果咳嗽一個半月,北京能跑的醫院都跑遍了,能吃的藥也都吃遍了,還是咳。祁好朋友的朋友介紹了霍大夫。
霍大夫很神,他的神不在只有三十二歲就成了傳說,也不在他七歲成了盲人,也不在他極少開常規的藥方,只以食療和推拿手法祛病;他的神在,聽完羅冬雨詳盡地羅列了余果一個半月來的病情與反復,以及余果的日常細節之後,慢悠悠地轉向只能偶爾插上幾句話的祁好,慢悠悠地說:「你這當媽的得上點心啊。」
他一個年紀輕輕的瞎子怎麼就斷定我不稱職?回家的車上祁好一路都在流眼淚。
他們在霍大夫跟前沒有透露出半點私密的信息,三個人自始至終都沒給對方任何稱謂。霍大夫把過脈,說當如此如此。開出的唯一方子是,咳嗽時喝蘿蔔蜂蜜水。管用。這幾天余果幾乎不咳了,但從昨天下午開始,霧霾捲土重來。玻璃一碎,余果在睡夢中也有了反應。
照祁好出門前擬定的食譜,羅冬雨做好早餐。跟一個多月來的每一天一樣,余松坡在早飯桌上都要解決很多問題,家裡的,劇組的,媒體的,好像是余果咳嗽以後他才開始忙的。今天他沒法送孩子去幼兒園了。
當然他也沒送過幾回,余果現在中班,一年半裡送接都算上,他進幼兒園也不超過十次。祁好稍微要多一些,逢年過節給老師送禮這事也讓保姆來辦,有點不合適。在飯桌上余松坡撥打一一○報了案,砸了廚房又砸衛生間,肯定有預謀,姑息只能養奸。
作為在美國待了二十年的「海歸」,這點法律意識還是有的。有話法庭上說,誰都別在背後耍小動作;砸玻璃,簡直可笑到下流,不能忍。
不過他一會兒就出門,錄口供只能羅冬雨代勞了。還有,警察來過之後,趕緊給物業打電話報修,冷風受得了,霧霾受不了。看過那個新聞嗎?科學家做了實驗,小白鼠吸了一禮拜的霾,紅潤潤的小肺都變黑了。黑了就黑了,回不去了。不可逆。
羅冬雨記下了。飯後,余松坡在玄關前換鞋時問:
「你祁姊啥時候回來?」
羅冬雨搖搖頭,機票不是她訂的。◇(未完,待續)
——節錄自《王城如海》/ 九歌出版社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