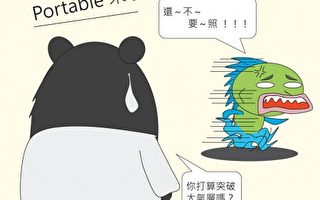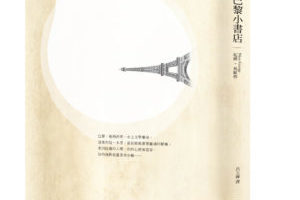艾琳娜與莉拉出生在二次戰後的那不勒斯貧窮郊區,兩人的友誼從六歲時交換娃娃開始,充滿活力的莉拉總是走在前頭,帶著艾琳娜去冒險;個性內斂的艾琳娜總是加倍努力,讓自己永遠可與莉拉匹敵。在重要的時刻相挺,但誰先達標時又不甘落後;這種互相啟發,又視彼此為可敬對手的狀態,是她們六十年友誼的基調。
但兩人六十六歲那年,莉拉突然消失了。莉拉從來沒有出走或改變身分的念頭,也沒想過要自殺。但她曾說過,想要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消失,化為無形,讓人再也找不到她。如今,莉拉要把人生抹除殆盡,且已經付諸行動。艾琳娜決定寫下還留在記憶裡的一切,不讓莉拉消滅人生的痕跡,看看這一次誰是贏家……
《那不勒斯故事》是義大利當今最受推崇的作家艾琳娜.斐蘭德的傑作,以回憶的方式,描述一段長達六十年友誼的四部曲小說。在第一集《那不勒斯故事》中,以二次戰後的那不勒斯為背景:貧窮街區、黑幫橫行、經濟衰退、左翼思想興盛行……斐蘭德述說了一個街坊、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故事,而外在環境的變遷,也反過來改變了兩位主角之間的關係。
這系列更是豐富、深刻、溫暖的成長小說,艾琳娜與莉拉的故事,也可能是每個讀者曾經或正在遭遇的課題,不論男女,都能在其中體會到生命的千般滋味。
【主文】
序幕:抹滅一切痕跡
1
這天早上黎諾打電話來。我以為他又是來開口要錢的,所以也準備好要拒絕了。但這不是他打電話來的原因。他媽媽不見了。
「什麼時候不見的?」
「兩個星期前。」
「而你現在才打電話給我?」
我的語氣想必充滿敵意,雖然我並不生氣,也不覺得他得罪了我,只是有點挖苦的意味。他想要解釋,但卻半用方言,半用意大利文,笨嘴笨舌,夾纏不清。他說他原本以為媽媽只是像平常那樣,在那不勒斯到處遊蕩。
「連晚上都不回家?」
「你也知道她是什麼樣子。」
「我是知道沒錯。但是兩個星期不見人影難道很正常嗎?」
「是的。你已經好一段時間沒見到她了,艾琳娜,她情況越來越不好。她永遠不想睡覺,整天進進出出的,想做什麼就去做。」
反正呢,到最後他開始覺得擔心了。他已經問遍了每一個人,到各家醫院轉了一圈,甚至還去找過警察。什麼結果都沒有,完全沒有他媽媽的蹤影。
好一個乖兒子啊!大個子,四十歲,這輩子沒幹過活,就只是個三流的騙子和揮霍無度的浪子。我想都想得出來他能有多用心去找人。才怪!他根本沒腦袋,而且心裡只有他自己。
「她沒來你這裡?」他突然問。
他媽媽?來杜林?他很清楚狀況,只是隨口問問而已。是啊!他很愛旅行,來過我家至少十幾次,每一次都是不請自來。
而他媽媽,我衷心歡迎的客人,卻一輩子沒離開過那不勒斯。
我回答:「沒有,她沒在我這裡。」
「你確定?」
「黎諾,拜託,我都說了,她不在這裡。」
「那她會去哪裡?」
他開始哭,我隨他去表演他的絕望。
一開始的假哭,到後來好像變成真的了。
他哭完了之後,我說:「拜託,就這麼一次,順她的心意吧:別找她了。」
「你的意思是?」
「就是我說的意思啊!沒用的。學著獨立吧!也別再打電話給我了。」
我掛掉電話。
2
黎諾的媽媽名叫「拉菲葉拉‧瑟魯羅」,但是大家都叫她「莉娜」。但我不一樣,我從來不喊她的名,也不叫她的姓。對我來說,這六十幾年來,她始終是「莉拉」。如果我突然叫她拉菲葉拉或莉娜,她一定會以為我們的友誼完蛋了。
起碼有三十年了吧!她有天告訴我她想要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留一絲痕跡,而我是唯一了解她意思的人。她心裡從來沒有出走或改變身分的念頭,也沒夢想要在其他地方展開新生活。
她沒想過要自殺,因為擔心黎諾必須處理她的遺體,被迫料理她的後事。
她想的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她想要消失;她想要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消失,讓她整個人都化為無形,再也找不著。因為我對她這麼了解,或至少我覺得自己了解她,所以我自然而然地認為她已經找到讓自己消失的方法,在這個世界上連一根頭髮都不留下。
3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檢查電子郵件,檢查郵遞的信件,但是並不抱任何希望。我經常寫信給她,而她幾乎沒回過信:這是她的習慣。她比較喜歡打電話,或趁我回那不勒斯時和我徹夜長談。
我打開抽屜,這裡有我擺各式各樣東西的鐵盒子。但裡面的東西並不多。我丟掉了很多東西,特別是和她有關的東西,她也知道。我發現我沒有她的任何東西,沒有照片,沒有短箋,甚至連一件小禮物都沒有。我很意外。這麼多年來,她沒留給我任何東西?或者更慘的,是我不想保留她的任何東西?真是如此嗎?確實如此。
換我打電話給黎諾。我很不情願這麼做。不管是家裡的電話或行動電話,他都沒接。他到晚上得空的時候才打給我,那語氣我很熟悉,他用的是博取同情的語氣。
「我看見你打電話來了。你有任何消息嗎?」
「沒有。你呢?」
「沒有。」
他東拉西扯地講個不停。他想去找電視臺,上專門尋找失蹤人士的節目,懇求媽媽原諒一切,哀求她回家。
我耐住性子聽他講完,然後問他:「你找過她的衣櫥嗎?」
「要找什麼?」
這麼簡單明瞭的事情當然是不會出現在他腦袋裡的。
「去看就是了。」
他去找了,發現衣櫃裡什麼都沒有,媽媽的衣服,不論冬夏,全都不見了,只剩下舊衣架。我要他搜尋整個屋子。她的鞋子,不見了;僅有的幾本書,不見了;所有的照片,不見了;收藏的電影,不見了;她的電腦失蹤了,包括舊式磁片和其他的一切,一切和她這個早在一九六○年代就使用打洞卡開始操作電腦的電子巫師身分有關的東西都不見了。我告訴他:
「不管花多少時間都沒關係,但是只要找任何屬於她的東西,就算只是一根髮夾,馬上打電話給我。」
他隔天打電話給我,非常激動。
「什麼都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連我們兩個人的合照,她都把她的部分剪掉,甚至連我很小很小的時候的照片都不放過。」
「你仔細找過了?」
「到處都找過了。」
「包括地窖?」
「我說了,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裝她文件的盒子也不見了:我不知道,出生證明,電話帳單,收據。這是什麼意思?有人把所有的東西都偷走了?他們到底是要找什麼東西?他們想從我媽和我身上拿到什麼?」
我叫他放心,冷靜下來。不太可能有人想找什麼,特別是從他身上。
「我可以來和你住一段時間嗎?」
「不行。」
「拜託,我睡不著。」
「這是你的問題,黎諾,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掛掉電話,他再打來,我沒接。我在書桌前坐下。
這是莉拉的典型作風,我想。
她把「痕跡」的概念擴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她不只希望自己消失,在六十六歲的此時,她還要把她拋下的整個人生完全抹除殆盡。
我真的很生氣。
看看這一次是誰會贏,我對自己說。我打開電腦,開始寫——寫下我們故事的所有細節,所有還留在我記憶裡的一切。◇(未完,待續)
—節錄自《那不勒斯故事》/大塊文化
【作者簡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出生於義大利的那不勒斯,行事低調,真實姓名保密到家,也從不在媒體露面,但作品依舊廣受世界各地讀者歡迎。
斐蘭德以女性成長故事著稱。第一部小說作品《不安的愛》(L’amore molesto, 1992)描寫女插畫家返鄉調查母親之死,後來被改編為電影。讓斐蘭德的好文筆更廣為人知的第二本小說作品《放任時期》(I giorni dell’abbandono, 2002),費時十年才發表,敘述單親媽媽如何面對空虛的人生。
從2011年陸續出版的小說《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帶有自傳色彩,描寫女作家與童年好友的故事,內容廣及十個家族與六十年的生命歷程。這系列自2012年陸續推出英譯本後,讓斐蘭德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熱門作家,並獲選為《金融時報》2015年度女性、《時代雜誌》2016年百大影響人物;該系列的第四集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