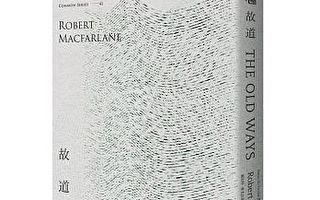人走了,時間也過了,
畫留下來了,時間停止在那裡?
這幅畫變成了歷史。 臺灣是不是這樣?
很多生命在生鏽,而後腐掉?
「會落雨嗎?」
大伯問,身邊站著新的大姆(編注:大伯母)。
「中午以前不會落。」
建墓師抬頭看看遠外山頂,有白色的雲翳竄了上來。
墓地散布在低山四分之一的高度以下的山坡上。墓地裡,擠滿著墳墓,有大有小,四周長著雜草,只有零星的矮樹。
阿公,鎮上的人叫他虬毛伯,因為他有一頭捲髮。
這是阿公的墓地,拾骨以後,改建成家族墓。
建墓師把菸蒂一丟,用腳踩了一下,看看還有些煙,再踩了一腳。
墓地下面,是一片稻田,是一片綠色,第二季的稻子,已長到一尺多高了。
一部計程車在墓地入口處停下,一個穿著深灰色衣裙的女人下來,匆匆越過墓地和稻田之間的小路。
那是大姑。
「這時候也塞車,不像話。」
大姑已滿身大汗,一邊急喘著氣。
大伯和父親商量,決定為阿公拾骨以後,在阿公舊墳地點,蓋一個家族墓。墓已蓋好,今天要把先人的骨甕移過來。骨甕有五個,曾祖父母、祖父母和大姆的。
阿祖貧窮一輩子,從小到處流浪,有時打零工,有時擺攤子,或做流動販,賣番薯、賣土豆,或杏仁茶等。其它,更早的墓,找不到了。因為阿祖並沒有告訴阿公。
家族墓有一點像土地公廟,比小型的土地公廟大一點,比中型的小。
家族墓的內層是階梯式,有五層,每層可放八個骨甕。
以前,家族的五個墓,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每次掃墓,幾乎要花一整天的時間,東西奔走。
這次家族墓完成,重新安置骨甕,父親和大伯商量過,要不要請二伯。二伯已過繼給舅公,已改姓石。實際上,阿公最疼二伯,阿公是船伕,二伯小時候也時常上船找阿公,有時還會和阿公在船上睡覺、過夜。二伯和大伯,以及和父親的關係,完全維持著親兄弟的情誼。
二伯,以前叫阿公姑丈,後來就跟大伯、父親他們叫阿丈。那時候,在農村或小鎮,還有人不叫自己的父親阿爸,而叫阿丈或阿叔。
要請二伯,就要請大姑。
大姑大二伯將近十歲,在二伯還沒有出生之前,已先過繼給舅公了。因為舅公一直沒有小孩。
大姑對舅公很不滿,舅公死後,自己去公所,把姓改回來,不再姓石。
大伯按照建墓師的指示行事,點了一把香,分給大家。
「怎麼不寫『隴西』?」
以前,在墓碑的上面,在顯考的兩側,都刻著「隴西」兩字。這次,新的家族墓上刻的是「李家墓園」。
「大姊,妳知道『隴西』兩字代表什麼?」
父親問她。
「代表李家呀!李家的墓不都刻著『隴西』二字,表示我們的祖先是從隴西遷移過來的呀。也就是我們的祖地呀。」
「妳知道隴西在哪裡?」
「在大陸呀!」
「大陸的哪裡呀?」
「……」
「元玲,告訴大姑隴西在哪裡?」
「在甘肅。」
「在甘肅……」
「妳知道甘肅在哪裡?」
「好了,好了。你們讀書較多,就要欺負人。反正,我也不會埋在這裡。」
大姑說,轉頭過去看看小姑。
小姑丈回中國去了,一年回來一次,回來領退休金,而後再去中國。在臺灣只住四個月,也就是在中國的時候有八個月,占了五分之二。聽說,在那邊還有二個哥哥和一個妹妹,父母在他可以回去之前,就已過世了。他回去,還為他們建造一個家廟。
「妳會埋在這裡嗎?」
「不會。不過,我也不知道要埋在什麼地方。」
小姑說,低下頭。
建墓師依序把五個骨甕放到墓屋裡。最上面的是男女二位阿祖,旁邊兩側是阿公和阿媽。男女阿祖是放一起的,阿公和阿媽卻分在阿祖兩側。他們為什麼不放在一起?
依照建墓師的說法,這樣才能放更多的骨甕。如果一代一層,只能放五代,阿祖,阿公和阿姆,就已占了三代,剩下的,只能供應兩代。
不是放在阿媽旁邊,另外一側,阿公的旁邊留了一個位子給大伯。
那新的大姆呢?
大伯和新的大姆,現在住在一起,不過他們並沒有辦理結婚登記,在戶籍上並不算是正式的夫妻。實際上,他們都是再婚,大姆有自己的子女。
「我們要住在一起,要互相照顧。」
大伯和大姆都這麼說。
「怎麼這麼小?」
大姑看著右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家族墓,看起來像廟宇,有中型的土地公廟那麼大。
「原來的地,只有這麼大。」
父親說。
的確,周圍都是墳墓,緊緊靠在一起,無法擴大。
「有夠了。裡面有四十個位子,現在子女少,四十個位子,不夠十代,也可以用八代了,一代二十五年,也二百年了。有夠了。」
建墓師拚命說,又點了一根香菸。
二伯話最少,從頭到尾,幾乎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二姆沒有來,因為堂姊在美國生產,她去照料了。
不過,元宏堂哥有來,還帶了女友來。元宏堂哥曾經帶女友來看過母親。二姆出國前有交代他,叫他有事要找三嬸,也就是母親商量。他預定要在九月間結婚。
大伯的小兒子,元德堂哥生病,沒有參加,他的大兒子元福堂哥有來,還帶來了兩個小孩,一女一男來參加。
我的大哥元昌,當導遊,目前人在日本。二哥元裕,在美國讀書。
「小心喔。」
大堂哥的兩個小孩,在墓地裡跑來跑去。那個小男孩已跌倒三次了。
「姊,妳將來也要放在這裡?」
「我才不。」
「為什麼?」
「我是女孩子。」
「為什麼女孩子不可以?我們不是一家人?我們不能像阿祖他們,放在一起?」
「大概是吧。」
「姊,我的狗狗死了,要放在裡面?」
「也不行。」
「為什麼?」
「牠不是人。」
「呃。」
他應了一聲,看來,他還是不懂。
「元玲,妳讀什麼?」
上香之後,大姑他們在燒紙錢,二伯忽然走到我的身邊問我。
二伯最像阿公,有一頭虬毛,人也比大伯、比父親高大一點。
「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
「對。」
「師大?」
「對。二伯也是師大畢業的?」
「對,那時候叫師院。妳的論文寫什麼?」
「《十日談》和《聊齋》的比較研究。」
「什麼?」
二伯顯然有點吃驚。
「為什麼?」
「自從上研究所之後,我一直想著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什麼位置。」
「快來燒銀紙了。」
大姑轉頭過來,喊了一聲。
「妳,以後要教書?」
「對。不過,如果可以,我還想攻讀博士。」
「要走研究的路?」
「我也曾經想過,也許,我也可以嘗試創作。」
「妳的計畫真不少。」
「二伯,聽說你喜歡畫畫?」
「妳怎麼知道?」
「母親說的。」
母親和大姑他們在燒銀紙,銀紙的紙灰揚起在空中。
「二伯,你畫什麼?」
「海報。」
「什麼?海報?」
「電影院的海報,也叫看板,就是把印好的小海報,畫成大海報,掛在電影院上面。」
「呃。」
我有點意外。
「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了。」
「現在呢?」
「主要是畫靜物,畫風景,也畫人物,不過不多。」
「畫插圖嗎?」
「還沒有想過。妳為什麼問?」
「我說我想創作,想寫劇本、小說。其實,我最想寫童話。」
「真的?妳寫童話,我可以幫妳畫插圖。」
「真的?」
「當然是真的。不過,那很不一樣。」
二伯說,從口袋拿出紙和筆,迅速畫了起來。
「妳看。」
二伯畫了一隻螞蟻,有動作,有表情,看起來好像在指揮,額頭還灑下汗水。
「二伯,你好像在畫我?」
二伯只是笑著,沒有回答。
「二伯,我已決心要寫童話,你一定要幫我畫插圖。」
「好呀。」
「快收好,可能要落雨了。」
建墓師說。山頂上的雲,已罩到頭上來了。◇
——節錄自《紅磚港坪》/ 麥田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