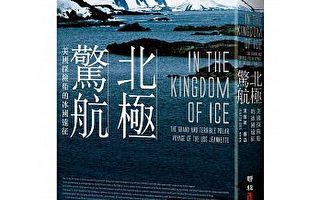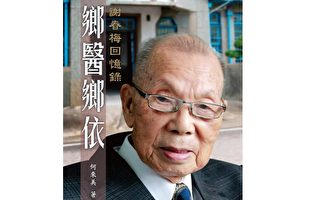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續前文)
*3
薇安對戰爭並不陌生。她知道的不是隆隆的槍砲、煙硝的戰火和鮮血,而是戰爭的後遺症。雖然在承平時期出生,她最早的記憶卻攸關戰事。
她記得一邊跟爸爸說再見,一邊看著媽媽啜泣。她記得餓肚子,而且總覺得好冷。但最重要的是,她記得爸爸返家後走路一跛一跛、唉聲嘆氣、沉默不語,變了一個人。
也就是那個時候,他開始酗酒,什麼話都埋在心裡,對家人不理不睬。之後,她記得房門劈啪關上、爭執聲轟然四起,而後緩緩轉為難堪的沉默、她爸媽搬進不同的臥室。
離家參戰的爸爸和戰後返家的爸爸是兩個不同的人。她試著贏得他的愛;更重要的是,她試著持續愛他,但最終,兩者皆是不可能的任務。
自從他把她送到卡利弗,這些年來,她營造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她每年寄聖誕卡和生日卡給他,但從來沒有收到過他的卡片。他們父女很少交談,還有什麼好說的?
伊莎貝爾似乎始終放不下,但薇安不一樣,她了解——也接受——媽媽一過世,他們的家就無可挽回,支離破碎。他是個再怎麼樣都不願為孩子承擔父職的男人。
「我知道妳多害怕戰爭。」
安托萬說。
「馬其諾防線挺得住,」她試圖讓自己聽起來令人信服:「你聖誕節之前就會回家。」
馬其諾防線是道長達數百英里的水泥牆,一次大戰後,法國沿著德、法邊境築起這道防線,沿牆架設武器與障礙物,防止德國入侵。德軍不可能突破這道防線。
安托萬攬她入懷。茉莉花香令人心醉,頃刻間,她確知從今以後,她一聞到茉莉花香就會想起這次道別。
「我愛你,安托萬·莫里亞克,我等你回家,回到我身邊。」
日後,她不記得他們走進屋裡,爬上樓梯,躺到床上,脫下彼此的衣服。她只記得自己赤裸裸地窩在他的懷裡,躺在他的身下,他一反往常,狂熱、急切……他的吻帶著探索的意味,雙手似乎想要撕裂她,即使是緊緊摟住。
「妳比自己以為的堅強,小薇。」
完事後,他們靜靜躺在彼此的臂彎裡,他對她說。
「我不是。」
她悄悄說,聲音輕到他聽不見。
***
隔天早上,薇安想整天把安托萬留在床上,甚至勸他收拾行囊,一家人像小偷那樣摸黑逃跑。
但他們能逃到哪裡?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整個歐洲。
等她吃完早餐,洗好碗盤,她的頭已經隱隱抽痛。
「媽,妳好像不開心。」
蘇菲說。
「夏天天氣這麼好,而且我們正要去好朋友家裡坐坐,我怎麼會不開心?」
薇安笑笑說,但是笑容有點牽強。
她走出家門,站到前院的一棵蘋果樹下,這才意識到自己沒穿鞋。
「媽!」
蘇菲不耐煩地叫了她一聲。
「我來囉。」
她邊說邊跟著蘇菲穿過前院,走過以前用來養鴿、現在用來擺放園藝工具的木棚和空蕩的穀倉。蘇菲推開閘門,跑進鄰家精心修整的院子,衝向一棟裝了藍色百葉窗的小石屋。
蘇菲敲敲大門,無人回應;她直接推門進去。
「蘇菲!」
薇安厲聲說,但她的斥責有如耳邊風。在好友家不必拘禮,而蕾秋·德·尚普蘭和薇安是十五年的知交。爸爸忝不知恥把她們兩姐妹丟到鄉園後的一個月,薇安就結識蕾秋。
兩人自此就是一對好搭檔。薇安瘦小、蒼白、緊張兮兮,蕾秋個頭跟男孩一樣高大,眉毛的生長速度比謠言的散布更加驚人,聲音跟霧號一樣粗嘎。她們都打不進小圈圈,直到遇見彼此。
她們很快就形影不離,中學畢業後依然是好友,直至今日。她們一起上大學,兩人都成為小學老師,甚至在同一時間懷了孕。如今她們在當地的小學任教,在相鄰的教室裡教書。
蕾秋從敞開的門口露面,懷裡抱著她剛出生的小兒子艾瑞爾。
她們互看一眼,眼神中道盡兩人擔心害怕的一切。
薇安跟著她朋友走進明亮、整潔雅緻的小房間,一張粗拙的木頭長桌擺著一個插滿野花的花瓶,兩側各有一張椅子,椅子式樣並不搭調。
角落有個真皮手提箱,箱上擱著蕾秋的先生馬克喜愛的羊毛氈帽。蕾秋走進廚房,端出擺滿可麗露蛋糕的小陶盤,兩人走向屋外。
小小的後院裡,玫瑰花沿著自家的樹籬生長,一張桌子和四張椅子散置在磚石平臺上,幾盞古舊的煤油燈懸掛在栗樹的樹枝上。
薇安拿起可麗露蛋糕咬了一口,細細品嘗濃郁的香草奶油內餡和香脆微焦外皮。她坐下。
蕾秋在她對面坐下,懷裡的小寶寶好夢方酣。靜默在兩人間延展,滿載彼此的憂慮和不安。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機會認識他爸爸。」
蕾秋低頭看著小寶寶說。
「戰爭會改變他們。」
薇安想起往事,說了一句。她爸爸曾參與索姆河戰役,在這場戰役中,超過七十五萬人喪命,種種關於德軍暴行的傳言也隨少數倖存的法軍傳回鄉里。
蕾秋把小寶寶抱到肩上,穩穩地輕拍他的背。
「馬克不太會換尿布。小艾瑞爾喜歡睡在我們的床上,我猜現在不是問題了。」
薇安感覺自己浮現笑意。這個玩笑不算什麼,但多少有點幫助。
「安托萬的鼾聲很煩人,這下我可以睡個好覺。」
「而且我們可以吃水波蛋當晚餐。」
「髒衣服少了一半,」她說,但聲音逐漸哽咽:「蕾秋,我不夠堅強,應付不來。」
「妳當然應付得來,我們會一起熬過來。」
「我認識安托萬之前……」
蕾秋不以為然地揮揮手。
「我知道、我知道,妳瘦得跟樹枝一樣,一緊張就結結巴巴,對每樣東西都過敏。我都知道,我也在,不是嗎?但這些都過去了。妳得堅強起來,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蕾秋的笑容漸漸隱去。
「我知道我人高馬大——輪廓優美,他們跟我推銷胸衣和絲襪時總是這麼說——但是,小薇,這件事讓我瀕臨崩潰,有時我也需要妳讓我靠一靠。但我當然不會整個人靠在妳身上。」
「所以我們兩人不能同時崩潰?」
「沒錯!」蕾秋說:「就這麼說定囉。好,我們是不是應該開瓶干邑白蘭地或琴酒?」
「現在是早上十點。」
「沒錯,妳說的對極了。那就來杯法式75雞尾酒吧。」
星期二早上薇安醒來時,日光自窗外流洩而入,粗拙的原木蒙上一層閃亮的光影。
安托萬坐在窗邊的椅子上,那張胡桃木的搖椅是薇安第二次懷孕時、安托萬親手所製。多年來,空空蕩蕩的搖椅似乎是個嘲諷。日後想起,她把那段日子稱為「流產歲月」。大地豐饒富足,她的心田卻一片荒蕪。
她四年內三度流產,失去三個氣若游絲、心跳微弱、雙手泛藍的胎兒。而後奇蹟似的,一個小寶寶活了下來:蘇菲。那張搖椅的木頭紋理間收納著幾個瘦小、哀傷的鬼魅,但也承載著美好的回憶。
「說不定妳應該把蘇菲帶到巴黎,」
她坐起時,他開口說:「妳爸爸會照顧妳們。」
「我爸爸已經表明他不想跟女兒住,我怎能指望他欣然接納我們。」
薇安把菱格被毯推到一旁,起身下床,光腳踏上陳舊的地毯。
「妳們沒問題吧?」
「蘇菲和我會沒事的,反正你很快就會回來。馬其諾防線挺得住,況且,天曉得德國人才不是我們的對手呢!」
「可惜他們的武器比我們精良。我把銀行存款全都領了出來,床墊下藏了六萬五千法郎,薇安,請妳善加花用。妳還有教書的薪水,應該可以讓妳們支撐好一陣子。」
她一陣惶恐,心中狂跳。她對他們的財務狀況所知甚少,向來是安托萬管帳。他慢慢站起來,把她摟到懷裡。她好想把此刻的安全感裝入瓶中,日後當她的心因孤寂恐懼而乾涸時,才能啜飲一口。
記住這一刻,她心想。他的亂髮捕捉了日光,褐色的雙眼盈滿了情意,一小時前,他龜裂的雙唇在黑暗中親吻著她。
他們身後的窗戶敞開,她聽到窗外的聲響,一匹馬兒拖著四輪推車沿著小路緩緩前進,馬蹄踢踢踏踏,車輪啪噠啪噠,聲聲平緩。
那八成是奎利安先生載著鮮花前往市場。如果她在院子裡,他會停下來送她一朵花,稱讚她人比花嬌,她也會微微一笑,說聲謝謝,請他喝杯飲料。
薇安不情不願地抽身。她走向木製梳妝台,把藍色陶罐裡的溫水倒進淺盆,洗了臉。在那個充當更衣間的凹室,她隱匿在金黃和乳白的亞麻布簾後方,穿上胸衣,套上蕾絲花邊的底褲和襪帶,沿著大腿順順絲襪,繫在襪帶上,然後穿上一件方領束腰洋裝。
等她拉上布簾、轉過身來,安托萬已經不在房裡。
她拿起皮包,走到走廊另一頭的蘇菲臥房。女兒的房間跟他們的一樣狹小,天花板斜向一側,地上鋪著寬長的木板,還有一扇俯瞰果園的窗戶。房裡一張鑄鐵床鋪,床邊的小桌上擱著一盞二手檯燈。漆成藍色的大衣櫥占據了剩餘的空間,蘇菲的繪畫妝點了牆面。
薇安拉開百葉窗,讓陽光流洩到房裡。
夏夜炎熱,蘇菲跟往常一樣半夜就把被單踢到床下,她那隻名叫「貝貝」的粉紅絨毛玩具熊貼著她的臉頰。
薇安拾起玩具熊,低頭凝視它那微微褪色、備受寵愛的臉龐。蘇菲去年迷上了新玩具,貝貝受到冷落,被丟置在窗邊的架子上。
這會兒貝貝再度受寵。
薇安傾身親吻女兒的小臉。
蘇菲翻身,眨眨眼睛,醒了過來。
「媽,我不要讓爸爸走。」
她輕聲說。伸手拿玩具熊,幾乎從薇安的手中搶走貝貝。
「我了解,」薇安嘆氣:「我了解。」
薇安走向大衣櫥,從櫥裡挑出那件蘇菲最喜歡的水手洋裝。
「我可以戴爸爸幫我編的雛菊花冠嗎?」
所謂的「花冠」皺皺地擱在床邊小桌上,小小的花朵已枯萎。薇安小心拿起,戴在蘇菲的頭上。
薇安以為自己應付得不錯,直到她走進客廳,看到安托萬。
「爸?」蘇菲摸摸枯萎的雛菊花冠,猶豫地說:「別走。」
安托萬蹲下來,抱住蘇菲。
「為了確保妳和媽媽的安全,我必須上戰場,但我很快就會回來。」
薇安聽出他話語中的哽咽。
蘇菲抽身,雛菊花冠斜斜地從頭上滑落。
「你保證你會很快回來?」
安托萬掠過女兒神情急切的臉龐,迎上薇安憂心重重的凝視。
「我保證。」他終於說。
蘇菲點點頭。
他們一家三口沉默地走出家門,手牽著手走上山丘,朝灰黑的穀倉前進。及膝的金黃野草覆滿渾圓的山丘,一叢叢跟乾草車一樣巨大的丁香花沿著地產的邊界蔓生。
三個小小的白色十字架立在山丘上,世間只剩下這三個十字架緬懷薇安失去的胎兒。今天她不許自己看十字架。心情已經夠沉重了,她不能再想那些往事,添增心中的負擔。
那部綠色的雷諾老爺車停放在穀倉裡。他們都坐進車裡後,安托萬發動引擎,倒車駛出穀倉,輾過漸漸枯黃的草,開到小路上。
薇安凝視灰塵僕僕的小窗,看著窗外青綠的河谷,鋪了紅磚瓦的屋頂、牧草田園、葡萄園、細長高聳的林木,種種熟悉的影像迷濛地閃過。
車子開抵圖爾附近的火車站。唉,太快了。
月臺上擠滿提著皮箱的年輕男子、與他們吻別的女人、哭哭啼啼的孩童。
一個世代的男人又將遠赴戰場。
別多想,薇安跟自己說。不要回想上次男人們返家時走路一跛一跛,顏面灼傷,缺手缺腳……
安托萬買車票,帶著他們上車時,薇安緊緊抓住丈夫的手。三等車廂非常悶熱,幾乎令人窒息,乘客們有如沼地蘆葦般擠成一列,她直挺挺地坐著,皮包擱在膝上,依然抓著丈夫的手。
火車到站,十幾個人下車,薇安、蘇菲和安托萬跟著其他人沿鋪著鵝卵石的街道前進,走入一個迷人的村莊,這個小村跟都蘭地區的其他村莊一樣典雅幽靜,繁花怒放,處處可見崩坍的古老城牆。
戰爭怎麼可能要來?這個寧靜的小村莊怎麼可能集結士兵、把他們送往戰場?
安托萬拉拉她的手,示意她再往前走。她什麼時候停下了腳步?
前方有一排最近架設、固定在石牆上的鐵製閘門,門後是一排排臨時房舍。
鐵門一開,一名騎馬的士兵出來歡迎來報到的人們,他的皮製馬鞍隨著馬兒的步伐嘎吱作響,臉上都是灰塵,熱得滿臉通紅。他拉扯韁繩,馬兒停步,一邊甩甩頭,一邊嘶嘶噴氣。
一架飛機在上空嗡嗡飛過。
「各位,」士兵說:「請把你們的文件帶到鐵門旁的中尉那裡。來,趕快行動。」
安托萬親吻薇安,這一吻是如此柔情,讓薇安好想哭。
「我愛妳。」
他貼著她的唇說。
「我也愛你。」
她說,但此時此刻,這幾個意義深重的字眼感覺卻無足輕重。與戰爭抗衡,愛情算什麼?
「我也是,爸爸,我也愛你!」
蘇菲哭著說,整個人投入他的懷抱。他們一家三口最後一次緊緊擁抱,直到安托萬抽身。
「再見。」他說。
薇安無法道別。她看著他走開,見他漸漸融入一群談笑的年輕人中,再也難辨身影。
巨大的鐵門「啪」地關上,鋼鐵在熾熱、塵土飛揚的空氣中發出鏗鏗鏘鏘的回音,薇安和蘇菲站在街上,形影孤單。◇(節錄完)
【作者簡介】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已出版二十二本小說。她曾是律師,而後轉行寫作。育有一子,與先生定居美國西北部與夏威夷。
——節錄自《夜鶯》/ 新經典文化出版公司
(點閱【夜鶯】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