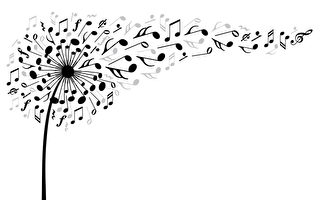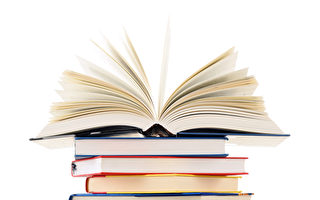大地(3)

在離婚率普遍攀升的年代,閱讀老一輩夫妻相處的小故事,備感淳厚。(pixabay)
【接續前文】
***
他扭頭看了她一、兩次,她寬闊的臉孔毫無表情,踩著一雙大腳,步伐平穩,慢吞吞前行,像是這條路她已走過了一輩子。走到城門口,王龍猶疑地停下腳步,一手穩住肩上的箱子,一手在褲帶裡摸索,翻找那僅存的幾枚銅幣,掏出兩文錢,買了六個青綠色的小小桃子。
「拿去吃吧。」他粗裡粗氣地這麼說。
女人孩子一般飢渴地接過桃子,默不吭聲捧在手裡。走在麥田壟上時,王龍扭頭看女人,女人正小心翼翼啃咬其中一枚桃子。察覺王龍看她,她再度用手掩住桃子,嘴也不動了。
兩人就這麼一路前行,來到土地廟所在的西邊田地。
小小的一座廟,灰磚壘砌,瓦片屋頂,高不過一個男人的肩頭。當年王龍的祖父也耕作著王龍現今生活了一輩子的農田,他用獨輪車從鎮上運來磚瓦,修建了這座廟。牆面塗抹灰泥,有一年豐收,祖父從村裡請來畫師,在白色的灰泥牆面畫上山與竹。然而幾代下來雨水沖刷,竹子僅存幾縷翎毛般縹緲的陰影,山丘則消失殆盡。
廟簷下安坐著兩尊小而肅穆的泥塑神像,是用廟宇周遭田地裡的泥土塑的。兩尊像分別是土地公和土地婆,身穿紅紙金紙裁製的衣袍。土地公留著真髮仿製的稀疏長髯。
每年過年,王龍的父親總買來新的紅紙,小心翼翼裁剪黏貼,為這對神祇添置新袍。而每年的雨雪總是登堂入室,夏日驕陽也長驅直入,神祇的衣袍總是年年損壞。
然而此時此刻,一年方才伊始,衣袍仍新,整潔的外觀讓王龍自豪起來。他從女人臂彎接過提籃,小心翼翼在豬肉之下尋找方才買來的兩炷線香,生怕線香若折斷了,會是不祥之兆,但線香完好如初。
由於左近四周的居民也都敬拜這兩尊小小神祇,因此神像前香灰堆積成小山,王龍把兩炷香插於其上,笨手笨腳地摩擦燧石與打火鐮,燃起一片乾葉來點香。
這一男一女便這麼立在土地神面前。女人看著線香的末端豔紅起來又轉為灰黑,灰燼逐漸沉重時,女人俯下身去,用食指撣去灰燼的頂端,而後又彷彿唯恐自己舉止失當,匆匆往王龍瞥了一眼,目光呆滯。但這動作令王龍心動。她像是覺得這炷香屬於他們兩人。像是這一刻,他們成為了結髮夫妻。
兩人就這麼肩並肩,沉默無語地看著線香燒成灰燼。此時夕陽已西沉,王龍於是扛起箱子,兩人踏上歸途。
老人站在家門口,領受這日最末的一抹陽光。王龍領著女人上前來時,他分毫不動。若是他注意到那女人,就有失身分了。於是他佯作對天邊雲朵興致高昂地高聲說:
「掛在弦月左端那朵雲意味著就要下雨了。最遲明晚雨就會來。」
看見王龍從女人手中接過提籃,他又嚷:「你去花錢了?」
王龍在桌上擱好提籃,答得簡明扼要:「今晚會有客人。」
說完他便把女人的箱子扛進自己屋裡,在自己的衣箱旁擱下,用奇異莫名的眼光瞅著衣箱,但老人來到門邊,喋喋不休地嘀咕:
「這個家花錢如流水!」
兒子邀了客人來,老人暗地裡是心喜的,但他估量在這新媳婦面前不能不發點牢騷,生怕她一進門他們就這樣揮霍,會慣壞了她。
王龍不作聲,逕自進了灶間,女人跟了進來。王龍把提籃裡的食物一件件取出,擱在冰冷爐灶的檯子上,對女人說:
「這裡有豬肉、牛肉和魚,晚上有七個人要吃飯,妳會燒菜嗎?」
他說話時沒有正眼瞧女人,正眼瞧似乎於禮不合。女人用平板的嗓子答:
「打從我進黃府,就是廚房裡的奴婢。我們餐餐都有肉。」
王龍點點頭離去。之後直到客人蜂擁而至時才再度見到她。
他的叔叔樂天貪饞又狡猾,叔叔的兒子是個莽撞的十五歲少年。上門的莊稼漢個個粗笨,怯生生地咧著嘴嘻嘻笑。其中兩人是收割時節和王龍交換種子並互相出力幫忙的村人,另一個是他的隔壁鄰居阿清,個頭矮小,沉默寡言,若非必要絕不開口。
大夥兒在堂屋裡你謙我讓,不肯入座。終於各自就座後,王龍走進灶間,要女人上菜。
女人說:「我把碗碟交給你,請你端上桌。我不想在男人前拋頭露面。」
王龍聽了心生歡喜。這女人是他的女人,不怕讓他看見,卻怕在別的男人前露臉,他感覺驕矜自豪,於是在灶間門口自女人手中接過一只又一只的碗碟,在堂屋桌上一一擺好,接著便拉開嗓門兒吆喝:「叔叔,兄弟們,吃飯嘍!」
叔叔向來風趣,他問起:「我們都不能見到蛾眉新娘嗎?」
王龍答得堅決:「我們還沒圓房,圓房之前,其他男人不宜見她。」
他敦促大夥兒吃飯,大夥兒於是就著一桌好菜默默吃了個盡興,間或有人盛讚魚的棕黃醬汁美味可口,有人大誇豬肉煮得好,王龍則一再謙讓:「粗茶淡飯,燒得不好!」
但內心裡,他暗自為這桌菜色感到光榮,因為女人混合了糖、醋、少許的酒和醬油,巧妙帶出了肉的全部風味,王龍從未在朋友的桌上嘗過這等美味。
那一夜,賓客們就著茶水談天說笑,久久才散,女人始終待在灶下。王龍送走最後一位客人,走進灶房,見女人蜷縮在老牛旁的稻草堆沉沉睡去。
被王龍喚醒時,她的髮絲中混雜著稻草。王龍呼喊她,她恍惚中猝然舉起臂膀,像是要抵擋拳腳。好不容易她睜開眼,用奇異而寧靜無言的眼神注視他,王龍覺得自己像面對個孩子。
他執起她的手,領她走進上午他為了她而洗滌身軀的房裡,點起桌上的一對紅燭。燭光下,他赫然驚覺自己此刻與女人獨處了,驀地羞赧起來,但不得不提醒自己:「我有自己的女人了,這事非做不可。」
他鐵了心開始寬衣,女人則一聲不響,輕手輕腳在床帳角落鋪起床來。王龍粗聲粗氣地開口說道:「妳上床前,先把燭火滅了。」
接著他逕自躺下,厚棉被拉上肩頭,佯作沉睡。但他並沒有沉睡,他躺臥著戰慄,渾身肌理的每一條神經都警醒著。許久之後,燈光乍暗,女人在他身旁緩慢無聲地悄悄挪動,他渾身脹滿近乎破殼而出的狂喜。他在黑暗中嘶啞一笑,伸手擁她入懷。◇(節錄完)
——節錄自《大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簡介】
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
美國作家。出生四個月後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在江蘇省鎮江市度過了十八年。
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年,她視中文為「第一語言」,把鎮江稱作「中國故鄉」。
1931年,其著名小說《大地》問世,農民「王龍」的生活故事使她連續兩年穩居暢銷榜冠軍,並於1932年獲得普利茲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是首位美國女性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者。也是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
【書評】
「賽珍珠的獲獎在於她筆下對中國農民的豐富、寬厚、史詩般的描述。」
────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授獎辭
責任編輯:楊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