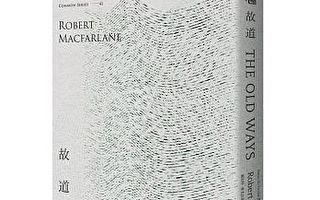誰是旅人?誰是歸者?
歡迎來到西班牙波韋尼爾。
請以溫暖好客的精神歡迎羅莎、莎拉、
愛爾瑪、艾力克斯、希帕提亞……
他們將來到你家,與你同住一段時間。
他們都是波韋尼爾小鎮
參與「信件接力」的居民。
信上的回憶
「展開舊信的樂趣之一,是明白已不需要回信。」——拜倫
「如果已經沒人想寫信,這世界還需要郵差嗎?」
莎拉問,她挫敗的語氣格外沉重,一字一句拉得很長。
半空中迴盪著她悲傷、破碎的聲音,每個角落被深沉的死寂所籠罩。
此刻,她的鄰居羅莎感覺到了,冬天不但造訪了這座小村莊,也探進她的心底。
她凝視廚房的磁磚牆面,有些部分早已剝落,接著她端詳存放鍋碗瓢盆的小櫥櫃。最後,她的視線飄向莎拉幫她補齊日用品的儲藏室。她已經八十歲了,有時連這種日常小事她都無力完成。
老太太弱不禁風的左手上戴有兩枚婚戒,她失神地擦亮著。
只要碰到不開心的事,她就會緊抓婚戒,以尋找平靜。她相信,她的亞伯化為婚戒陪伴她,能為她帶來力量。
「可是,莎拉……」羅莎低聲地說著:
「妳確定嗎?」
就因為害怕聽到答案,她遲遲不敢將問題說完,最終還是聽見答案了。
「波韋尼爾的郵局就要關閉了,他們來信通知,耶誕節過後就要將我調至省都。他們說這是資源重新調配、縮減開支,我也不知道……總局寄來的電子郵件是這樣寫的。」
還有兩個月,老太太心想。
「我已經快四十歲了,還要帶著三個孩子,這對我來說根本一場鬧劇。」年輕的女人說。「我在這座村莊長大,而我的孩子也在此出生,我們全村就像個大家庭。他們如果要把我調走,一切都會改變了。」
女郵差別開臉,看向窗外。像是自言自語,這一刻她低聲說:
「我會在省都的大街小巷裡發瘋,但是除了接受調派,我沒有其他選擇,畢竟我得養活四個人。」
羅莎看了一眼床頭櫃上的時鐘,已接近午夜十二點。向莎拉道別回家後,她的心開始失序狂跳。羅莎的太陽穴砰砰地跳動,想睡也睡不著。
她泡了兩杯椴樹花濃茶。根據醫生的建議,晚餐時她只喝了一碗清湯。她洗好碗盤,將隔天要吃的小扁豆泡水,然後摺好洗乾淨的衣服。
然而,這些瑣碎的工作無法抹去她腦海中的壞消息:她的鄰居將要接受調派了!
她試著想像莎拉搬到外地的生活,可是她辦不到。
「這座小村莊沒什麼特別的,不但沒有前浪漫主義派的隱士,也沒有支持獨立的英雄,但這就是我們的村莊。」
羅莎心想,一邊從櫥櫃找出她的編織工作包。
波韋尼爾,有如一座石砌迷宮,交織著由石頭及石板搭蓋的屋舍,居民不到一千人,此外,還有約十幾棟錯落在鄉野之間。
不久前,村莊外圍開始出現代化的社區,似乎就要吞噬掉所有綠地。羅莎認為,那些剛搬來的陌生人只是過客,搭上高速鐵路和房產投資的熱潮而來。
「怎麼會是莎拉?我親愛的莎拉,竟然會比這些人更早遠離這裡?」
她問自己。
她想起莎拉出生的那一天,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
當時,她家大門傳來敲門聲,樓上的鄰居臉色慘白,他是一位兩個月前才剛搬來的郵差。他心急如焚地告訴羅莎,他的太太就要臨盆了,但醫生卻來不及趕到。羅莎看著自己的雙手,她知道沒其他選擇了。
「是我和妳媽媽一起將妳帶到這個世界的。」
在莎拉小時候,羅莎經常這麼對她說。
「妳爸爸看到第一滴血就昏倒了,醫生趕到時,我們早已幫妳清潔乾淨。」
羅莎自己無法生育,這是她離孕育生命最接近的一刻。
羅莎感覺到心底那股強烈的恐懼。她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雙手環抱自己。她原本雜亂的思緒開始變得清晰立體:如果莎拉搬走,她會留在這裡,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這棟屋子。
一想到那個畫面,她就忍不住開始發抖。
她在這棟屋子第一次過夜,就是她嫁給亞伯的新婚之夜。
這棟屋子由紅褐色的石頭建造,儘管簡陋卻十分堅固。當初蓋屋子的人只答應他們一個要求,就是屋頂架上倉鴞圖案的鐵製風向標。
「倉鴞是一種非常有智慧的貓頭鷹。」她總是這麼對丈夫說。
屋子的一樓是車庫,二樓是他們的住處,三樓住的是她的公婆。公婆過世後,她的丈夫繼承了屋子。當他們得知無法生兒育女,便決定出租空著的房間。幾個月後,莎拉就在三樓誕生了。
對羅莎來說,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
那些回憶讓人幾乎能忘卻憂慮。小女孩在樓梯間跑上跑下的,星期六大家會一起打牌,在頂樓一邊曬床單一邊說悄悄話,夏季他們一起去郊外。後來,莎拉長大結婚,緊接著有了第一個小孩出生,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
然而,有一天,世界毫無預警地被黑暗籠罩。
亞伯在車禍中喪生。
不久之後,莎拉的丈夫消失無蹤,留下她、三個孩子,還有一堆待付的帳單。最後,莎拉的父母生病,也無法幫忙不幸的女兒。羅莎對她說:
「莎拉,我將妳帶到這個世界,卻也送妳的母親前往另一個世界。」
慢慢地,其他人離開後所留下的空白,被三個孩子無憂無慮的笑聲填補了。當莎拉和羅莎終於習慣親人的離去後,省都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卻打破她們好不容易獲得的平靜。
羅莎開始編織,希望撫平自己的焦慮,她一針一針地鉤著,卻不停地圍繞同樣的煩惱打轉。
如果莎拉帶著三個孩子遠離波韋尼爾,丟下家鄉的草地和鄰居,自己怎麼撐下去?
這時,她覺得自己有些自私,但若是少了莎拉的陪伴,自己真的可以嗎?
突然間,她把鉤針放在腿上,浮現另一個擔憂。
如果村莊唯一的郵差被調派至省都,超過百年歷史的郵局勢必要關門大吉。她感覺到,這村莊即將遭逢天大的劫難。
大家都在睡夢中,對悲劇的降臨渾然不知,只有她這個可憐的老太婆睡不著,卻無力阻擋事件發生。
她身心俱疲,已不是休息就能恢復。儘管如此,她還是決定上床躺著。
兩個小時過去了,她還是躺在床上盯著時鐘的指針,她的心無法沉靜下來,她的人生就像一團毛線球,思緒全交纏在一起。
突然間,時間開始倒退,她看見年輕時的自己。
那時候的自己,一定知道該怎麼做吧!
當時,那個大膽的女孩一刻都靜不下來,不是幫老師照顧較為調皮的孩子,就是跟著祖母學編織,不然就是陪爸爸顧著家裡的食品店,亞伯因此愛上她。
他在婚禮上對她這麼說:
「只要有夢想,沒有跨不過的高牆。」
那是她這輩子最快樂的一天……幾乎算是。
她吐出了一個多年不曾說出口的名字:露易莎。
「過去往往也埋葬幾段痛苦的回憶。當你走在回憶的路上,可能會不小心喚醒它們。」
她喃喃自語,並擦乾悄悄落下的眼淚。
從上小學的第一天開始,她與露易莎就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她們無時無刻黏在一起。一個去哪裡,另一個就會跟到哪裡。她的好朋友住得比較遠,位於這村子及另一個村子的交界處。
好友個性害羞、甜美而安靜,相對於她的活潑外向,是完美的搭配。她們從星期一到星期日,不論是冬季或夏季,都玩在一起。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她們一起上國文、數學,也一起翹家政課。
她們冷落了洋娃娃,卻迷上腳踏車。有一天下午,她們一同出遊,在村莊兩公里外的地方突然下雨,她們衝向一間位於公路盡頭的聖母小教堂。
石頭搭建的教堂只有一平方公尺大小,木製屋頂已多半腐壞,門環是天使的頭部,臉上有一對斜眼。據說,這是某位鐵匠的報復。
這位鐵匠再婚娶了一位守寡的村婦,而村婦有個如惡魔般調皮搗蛋的兒子,他鬧得繼父無法好好過日子。有一天,鐵匠氣憤難耐,在工作坊時,依照繼子的臉孔和一雙斜眼打造了雕像門環,嚴肅地看著雕像說:
「我不打你,以免你的母親對我生氣,但現在你得承受所有罪有應得的拍打。」
這兩個好朋友,笑嘻嘻地遵照傳統,拉起門環敲了兩下。當她們推開門後,嚇了一大跳,地上坐著一個年紀比她們稍大的男孩,他正靠著橄欖綠的墊子休息。
他對女孩們一笑,深色的眼睛讓昏暗的小教堂亮了起來,也因而讓她們感到安心。
不知道為什麼,她們覺得像是早已認識了他一樣。
她們在他身旁坐下,等待著外面的暴雨停歇。他對女孩們說,他剛當完兵,今天是他的返鄉日。他說話的時候,那雙寬大強壯的手不停揮動,吸引了羅莎的目光。
每一分如秒般飛逝。雨勢停歇後,年輕的士兵迫不及待想見朋友,幾乎沒說再見就速速離開。他沒將他的名字告訴女孩們,不過沒關係,當晚她們兩都知道了,他是「亞伯」。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兩個好朋友絕口不提及男孩,但關於他的回憶卻悄悄地在她們心中札根。
直到夏末的舞會上,女孩們又遇見他了。
那個夜晚,露易莎打扮得特別漂亮,亞伯與她跳舞的時間比其他女孩還多。羅莎以為自己沒有機會了,決定埋葬她剛萌芽的情愫,戴上冷漠的面具。
那天晚上後,露易莎無法再和亞伯說話了,只因她太過害羞了。在街上看到他時,她會跑去找個門廊躲起來。若碰巧在商店見面,她就垂下頭,直到男孩離開才敢再抬頭。她深深地墜入情網,也可能她是自己這麼認為的。她開始吃不下飯,也會忘東忘西。
羅莎嚇壞了,於是自告奮勇,和好朋友表示自己願意幫忙。她們擬定一個起初看似天衣無縫的計畫:她負責取得男孩的信任,向他轉達露易莎的感受,看看他是否有所回應。
羅莎成了好朋友的邱比特,這個點子安撫了露易莎,某程度上來說,也同時讓她感到踏實。
「當河水開始流動,想要控制波濤洶湧的力量並不容易。」
羅莎對自己說。
這樣的事發生了:在初識亞伯時燃起的熱情,一天比一天更熾烈。理智上,她想要幫忙露易莎,但是她的心卻辦不到。
男孩也有同樣感覺。他對那場舞會的甜美女孩的回憶開始模糊,但羅莎那雙接近他的小手卻鮮明了起來。整座村莊的村民都知道怎麼一回事,只有當事人渾然不知。街坊鄰居的大嬸說:
「兩人行是一對,三人行則太擠。」
「最後,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羅莎嘆口氣。
有一晚,亞伯向她表白,她無法拒絕。不到三個月,他們就結婚了。
他們兩無法面對她的姐妹淘,放棄所有可能的彌補機會。羅莎與亞伯從未給露易莎一個解釋。婚禮當天,是他們最後一次見到她。
六十年過後,羅莎守寡時,她想起好友在婚禮當晚出現,穿著一身黑衣,佇立在教堂內盡頭。當神父說:
「你可以親吻新娘了。」
露易莎打開大門出去,從此消失無蹤。
起先,羅莎陶醉在幸福當中,不太會想到她,但過了幾個星期,她很想見露易莎一面。她去了她家,她的父母說她離開村莊,後來就再也不知道她去哪裡了。
「妳的離開,在我們的生活留下太大的空洞……」
老太太低喃著,她隨著記憶載浮載沉。兩人從未後悔當初的決定,婚後一直深愛彼此,唯一的缺憾是無法生兒育女。
「那些沒說出口的話,像是將我們拉向海底的船錨。」羅莎曾多次說。
這一晚,她發現婚禮前沒告訴露易莎的話,依舊像顆心中的大石頭。
或許,這是她唯一的人生債,但,現在要償還是否太晚了?
老太太打開床頭櫃,拿出一張亞伯在新婚那幾年耶誕節拍攝的泛黃照片,他臉上掛著大大的笑容,這是她最心愛的照片。
「亞伯,你總說事出必有因,對吧?莎拉會調派、郵局要關門,應該都有原因的。她會把這件事告訴我這個心碎又可憐的老太婆,也並非偶然。」
她拿起照片親吻,臉上露出微笑。
「就在莎拉告訴我這件事的當天夜裡,我想起露易莎,這也不會是巧合。」
她安靜了片刻。
「亞伯!有人希望我做點什麼!或許是莎拉,是你,或是露易莎……你們都瘋了,才會以為我無所不能。我這輩子總是堅定又固執……但容我提醒你一下,我已經不是二十歲了呀。」
她陷入思緒,視線回到照片上。
「雖說如此,曾經二十歲,也能再假裝是二十歲。」
她露出淘氣的笑容。
「或許,只是或許……我該找個方法幫助莎拉和這座村莊,甚至償還我的人生債。」
她將照片按在胸口,閉上雙眼。
在她熟睡之前,她夢見自己慢慢走向郵局,她踏入郵局,停在櫃檯前,將手伸入衣服下面尋找著什麼,就在那心臟的位置上。◇(節錄完)
——節錄自《高山上的小郵局》/ 悅知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