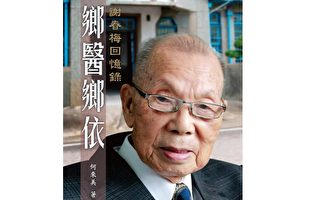7個民航史上的懸案——揭開神秘民用航空事件的真相!
【前情提要:1968年2月16日晚間,民航空運公司的波音727型客機即將由香港飛往臺北】
這架波音727的正駕駛是司徒·第歐(Stu Dew),他是民航空運公司最早的8位飛行員之一,飛行總時數高達1萬9千7百餘小時,其中包括4千8百餘小時的噴射機飛行時間。自從1966年他開始接觸波音727型飛機以來,已經累積了100餘小時的波音727飛行時間,該算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飛行員。
副駕駛是華裔的黃伯謙,他在民航空運公司已有17年的飛行經驗,飛行總時數1萬6千8百72小時,也是在1966年開始換裝波音727,該型機的飛行時間與第歐不相上下。其實以他的飛行經驗及技術來說,其實早可以升任正駕駛,但在這家外籍人士當權的華籍航空公司裡,他卻始終沒有晉升的機會。
駕駛艙裡還有一位飛航機械員,是曾在空軍官校18期受訓的張崇斌。「兩航事件」之後他沒有隨著其他人員投入共產中國的懷抱,反而加入民航空運公司繼續擔任副駕駛。公司進入噴射時代之後,他被選為噴射機的組員,擔任飛航機械員。
這架波音727在黃昏由松山飛抵香港,這時民航空運公司航務處副處長希克斯與他的太太已經在貴賓室等候了。飛機在當地只停留一個多鐘頭,等客艙清理完畢就立刻飛返臺北,於是希克斯在一般旅客登機之前,就帶著他的夫人先行登機,將他的夫人安置在頭等艙以後,就進入駕駛艙與組員們閒聊。
希克斯在二次大戰期間就以美國陸軍航空隊(US Army Air Corps)的飛行員身分,在中國戰場擔任作戰任務。大戰結束之後,他在1948年加入民航空運公司,繼續在中國大陸飛行。民航空運公司被中央情報局收購之後,他也曾擔任公司支援奠邊府之役的任務,前往越南支援法軍。他的飛行總時數超過2萬小時,並在1966年完成了波音727換裝訓練,此後的一年多期間他累計了140餘小時的波音727飛行時間。
張崇斌回憶,那天在飛機上見到希克斯走進駕駛艙,很明顯可以看出他情緒相當的亢奮。張崇斌覺得希克斯大概在貴賓室裡曾喝了些酒,才會有那樣的表現。
旅客陸續登機了,駕駛艙的組員開始做起飛前的準備。按照專業的要求,希克斯應該在此時回到客艙坐好,可是他反而繼續待在駕駛艙裡與組員聊天。當時張崇斌正按著查核表依序唸出每一個檢查項目,有好幾次必須打斷希克斯的話,來確定另外兩位組員有確實執行檢查項目。張崇斌心裡一度興起一個念頭,想建議希克斯回到客艙去坐好,但礙於希克斯是公司航務處副處長的身分,他只好將到了舌尖的話嚥了回去。
一位坐在客艙中段靠窗的旅客是家住香港的高永齡先生,那天他正要前往臺灣,擔任臺北市西門町華僑百貨公司的總經理一職。他進入客艙坐妥了之後,立刻將安全帶牢牢繫緊,並仔細觀察飛機的緊急出口是在哪個方位。他會這麼緊張,是有原因的。
就在三個多月之前,高永齡搭國泰航空公司第三十三次班機(一架康維爾八八〇式噴射客機)由香港前往西貢,飛機在起飛滾行的階段發生故障,飛行員放棄起飛之後無法將飛機即時減速,最後飛機衝出跑道,衝進維多利亞海灣,造成一人死亡,飛機全毀。落海之後,飛機在高永齡的座位前方斷裂,他才能快速地由斷裂處爬出飛機。雖然他在國泰航空的失事中僥倖生還,可是這種可怕的驚險過程一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因此這次他登機後,立刻非常警覺地查看座位四周,牢牢記住了緊急出口與他座位的相對位置。
飛機於晚上八點十八分由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在航管中心指示下向臺灣方向爬高。那時飛機是在自動駕駛的控制下飛行,黃伯謙坐在副駕駛座上注意著儀錶,張崇斌也專心盯著儀表指針顯示的三具JT-8發動機運轉狀況。至於希克斯與正駕駛第歐兩位美國飛行員,則在興高采烈地聊天。
飛機爬到3萬5千呎改平飛後,希克斯突然向第歐表示,距他上一次飛波音727,已經有兩個多月了,而且他也從來沒飛過公司的這一架飛機,因此他想坐上駕駛座,實地操縱這架飛機,過一下飛行的癮。第歐聽了之後立刻將安全帶解開,將駕駛座讓給了希克斯,自己則坐在正、副駕駛中間後方的臨時組員座椅。
張崇斌心想,希克斯實在不該提出這個很不專業的請求,第歐更不應該讓座。可是他轉念一想,希克斯是個合格的波音727飛行員,也是公司航務處副處長,雖然以前並沒有這種在航程中毫無理由隨意更換飛行員的先例,不過他也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出面干涉,於是他也就沒有作聲,繼續坐在他的位置上執行飛航機械員的勤務。
晚上8點45分,希克斯用無線電通知臺北航管中心:本機已飛進臺北飛航情報區。臺北航管中心於是指示他將高度降到2萬9千呎,希克斯隨即將飛機油門收回,讓飛機開始緩緩降低高度。5分鐘之後,希克斯又向臺北航管中心報告飛機正通過馬公多向導航臺(VOR)臺北航管中心便指示希克斯下降高度到1萬1千呎。
9點11分,希克斯通知臺北航管中心,飛機正通過新竹電臺上空。此時臺北航管中心將那架波音727的管制權交給臺北近場臺,臺北近場臺與希克斯取得聯絡之後,指示它繼續降低高度,以5千呎高度通過桃園電臺,兩千呎高度通過外信標(Outer Marker),用儀器降落系統(ILS,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對松山機場十號跑道進場落地。
9點18分,就在那架波音727接近外信標時,臺北近場臺按照航管程序,將那架飛機的管制權交給松山機場塔臺,並通知希克斯與松山塔臺聯絡。
希克斯聽到近場臺的指示後,把飛機的無線電通話波道換到松山機場塔臺向塔臺報到,並要求落地指示。塔臺管制員隨即指示他繼續以儀器降落系統進場,並告訴他當時松山機場的風向、風速及高度表設定值等。塔臺要求希克斯,等他目視機場的進場指示燈後再呼叫。希克斯當時很平靜的回應訊息收到並了解。這是希克斯最後一次與外界聯絡。
就在這個時刻,希克斯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根據進場程序,他必須以2千呎的高度通過外信標,但是他在下降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到飛機的高度,他完全不知道當飛機接近外信標時的時候,高度只剩下5百餘呎。在這樣的高度,飛機的儀器降落系統無法攔截到下滑道(Glide Path)的訊號,根本無法執行自動進場。而離譜的是,駕駛艙內的每一個人都沒有注意到飛機高度太低了,儀器進場的指示燈並沒有由黃轉綠。
飛機通過林口時,高度只剩下350呎,儀錶板上的警告燈在這時亮起,副駕駛黃伯謙看到了警告燈之後喊了聲:「高度!」想要提醒希克斯飛機的高度已經低到危險的程度。但希克斯並未理會他的警告。坐在臨時組員位置上的第歐也看到了警告燈亮起,他也提醒希克斯,飛機的高度似乎偏低。可是第歐誤認為飛機那時已經通過了外信標,正在接近松山機場跑道,所以他也沒有再進一步去干涉希克斯的操作。
在後面的客艙,空服員開始對旅客廣播,通知旅客飛機即將在松山機場落地,要求旅客們將安全帶繫妥……
這架波音727繼續降低高度,左翼先撞上了一棵大樹的樹尖,整架飛機抖動了一下,喪失了更多高度。坐在客艙中段的高永齡感覺到了那一陣很不尋常的抖動,下意識地抓緊了座椅旁邊的扶手……
很快地,那架波音727的主輪就接觸到了林口的田地,飛機在崎嶇不平的田地間顛簸著前進,此時駕駛艙裡的每一個人都突然意識到飛機已在機場以外的地方著陸了!
希克斯詛咒了一聲後大叫:「Max Power!(最大馬力)」同時將油門推桿向前推去,機械員張崇斌急著將馬力配置調好,將發動機的動力調到最大。
三具JT-8噴射發動機在經過幾秒鐘的滯性之後,開始加速,飛機再度得到昇力。希克斯緊張地將駕駛盤拉回,希望飛機能安全的重新飛上天空。然而在那片田地的盡頭有一間農舍,飛機才剛開始爬高,左邊主輪就撞上了農舍。巨大的撞擊力使得飛機左翼頓時下垂,機身向左偏去,撞進了一片相思樹林。
飛機震動的幅度持續增加,就在高永齡覺得自己在劫難逃、那致命的撞擊隨時會出現的時候,飛機卻猛然向左邊偏轉,然後一陣巨響與震動,飛機停了下來。
他睜開眼睛一看,發現機艙內已經起火,他立刻將安全帶解開,翻過旁邊的兩位旅客,對著記憶中的緊急出口處衝去。
然而還沒走幾步,他就發現機身已經斷裂,裂口正在他前面,由火光中他看到他所站的機身似乎距離下方的地面還有五、六公尺的高度,但現在根本顧不得了,毫無懸念縱身一跳,落在下方濕軟泥濘的地面。
等他由地面站起來時,發現身上的大衣已經著火,於是立刻脫掉大衣,拚了命往沒有火的地方跑。
張崇斌由他的座位上看不到飛機撞上什麼,但是由那巨大的撞擊力他知道最糟糕的事已經發生。在發動機的吼聲及機身在樹林被撞擊的雜音之間,他似乎聽到了第歐在他身後的咒罵與哭嚎,那時他已不在乎他在呼喊些什麼了,他知道飛機即將墜毀,在那生死一線的當兒,他沒忘記身為飛行組員的職責,他將發動機的油門及電門關掉,然後雙手抓住工作枱邊緣,等待飛機墜地時更大的撞擊。
幾秒鐘有一個世紀般的長久,當那似乎毫無止境的衝撞終於停止之後,張崇斌趕緊將安全帶解開,站起來要將駕駛艙的門打開。這時他聽到第歐的呻吟,他轉身看到第歐所坐的臨時組員座椅已被摔到一邊,左臂擠在座椅與機身之間,無法脫身,而希克斯似乎也被擠在機長座椅與儀錶板之間,他想藉著雙手抓住駕駛盤,將自己由駕駛座上站起來,卻無法使勁。
晚上九點二十分,松山機場的塔臺覺得民航空運公司的727客機應該已經飛抵內信標了,從塔臺上也應該可以看到那架飛機才對,但夜空中卻看不到它的航行燈,也沒有聽到那架飛機呼叫目視機場。
松山塔臺於是開始急切呼叫那架飛機,回應的是一片沉默。九點二十六分,塔臺還是無法聯絡到那架飛機,這時大家知道情況嚴重,於是立刻通知民航空運公司及臺北航空站飛航安全組:
「來自香港的波音727已經失蹤。」
塔臺也與空軍作戰司令部聯繫,詢問空軍的雷達上有沒有那架飛機的蹤跡。
高永齡跑了一陣子,才敢回過頭來看看飛機失事的現場,整架飛機都已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他看著那個有如煉獄般的火焰,實在不敢相信他在短短的一百天之中經歷了兩次飛機失事的慘劇,而他竟然都能活著出來。他就覺得這是他母親平時燒香拜佛起了作用,上蒼才會特別的眷顧他。
此時另外幾位逃出來的旅客走到高永齡身旁,彼此互相訴說著由破碎機身中逃出來的經歷。幾個人說著說著走到一條路上,遠遠竟然看到有一輛計程車亮著燈開過來,於是他們攔下計程車,要司機往臺北開。◇(節錄完)
——節錄自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