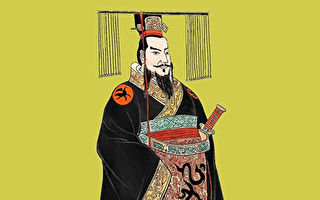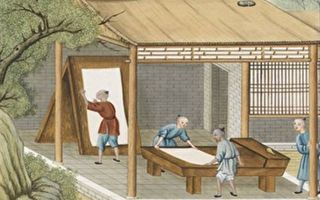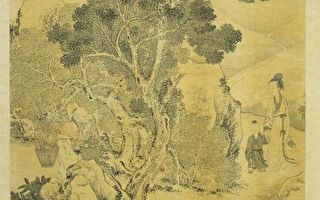前言:瘟疫,兵禍,天災相繼而至。晚清風雨飄搖,災異不斷。身逢亂世,應當隨波逐流,渾噩且過?還是砥礪猛進,慧眼警醒?曾國藩感嘆身在亂世,實為不幸。面對欺辱、毀謗、功名與誘惑,他戰戰兢兢遵循傳統,勤謹修身。經歷千百險阻,不屈不挫,終於亂世中脫穎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雖位極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終。我們擷取曾國藩家書、日記及史稿,從財富觀、修身思想、治家智慧、養生之道等不同層面,呈現曾國藩秉承的傳統價值,為讀者再現遺忘的精華傳統。
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入仕,到了咸豐十年(1860年),他以欽差大臣身分督辦江南軍務。此時的他是大清朝廷倚重的大員。家族中不僅曾國藩大權在握,他的弟弟們也相繼建功立業,為保大清立下赫赫戰功。然而他行事仍舊格外謹慎。對待諸弟和子侄,他苦口婆心地督導,要戒掉驕、奢、佚(淫逸)。
自古以來,官場是功名是非之地。曾國藩奉命在長沙辦團練。他效法明朝戚繼光,招募健勇壯丁,號稱「湘勇」,同時籌資建造戰船。經過多年屢敗屢戰,同僚的刁難和欺侮,朝臣的掣肘,曾國藩終是成就了一番事業,名震天下。他說:「人人都熱衷名望,誰會比不上我?當我有了顯赫的名望,必會有人承擔不好的名聲。」這樣一比較,他的心裡反而會過意不去,惟有自我砥礪虛懷若谷,時時反省警惕自己。他想到家鄉的弟弟們,叮囑他們教育子侄後輩要為人勤懇,行事謙謹,「我既然在外有了權勢,家中子弟最容易驕奢淫逸,這二樣都是敗家之道。」
隨著曾氏兄弟閱歷逐漸加深,兄弟們在書信中也流露出一種傲氣。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在多封家書中,提醒弟弟們戒驕、戒惰、戒佚(淫逸)。他認為:「天地之間惟有清廉和謹慎才是承載福氣的方法。驕傲使人自滿,太滿就會傾覆。」在他的眼裡,一個人無論說話還是寫文章,比如厭惡別人俗氣,嫌棄別人粗鄙,隨意議論別人的短處,或者揭露一個人的隱私,這都是驕氣。
曾氏家族名望高隆,聲勢顯赫,除了諸弟言談舉止充滿了傲慢,曾國藩還注意到,家族子弟也充滿了傲氣,而且一張嘴就議論別人長短,譏笑別人鄙陋。為此,他曾勸澄弟曾國潢:「賢弟要想戒除子侄後輩的驕氣,必須先把自己喜好議論別人短處,喜好揭露別人隱私的習氣,痛加改正,然後再讓子侄後輩在這些事上警醒改正。去除驕字,以不輕易非議、笑話別人為第一信;去掉惰字,以不晚起床為第一義。」
不過,澄弟回覆信函,說曾家子弟沒有不謙和的。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凡是喜歡譏諷批評,揭露別人短處的人,都屬於驕傲之人。他引用諺語「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規勸弟弟,「不是說,一定要錦衣玉食,動手打人,才叫驕傲。就是自己感到志得意滿,從而沒有畏懼顧忌,開口就議論別人長短,這就已經是極驕極傲了。」他希望澄弟能夠猛醒,望諸弟和家族子孫能在戒驕戒惰上多下些功夫。
軍事倥傯,政務繁忙,曾國藩仍然堅持每天讀一卷經史。他熟讀經史,為弟弟們講起歷史故事,幾乎信手拈來。史上有太多的人敗在了驕傲、懶惰上。曾國藩說起上古唐虞時代的惡人,比如帝堯長子丹朱為人傲慢,出兵討伐舜帝;舜帝的異母弟弟名叫象,本性傲狠,要置大舜於死地;夏朝末代國君桀,以及商紂王這些人因為驕恨,落得喪身亡國的下場。
曾國藩以史為鑑,自述從咸豐八年六月以後,就力戒傲字、惰字。他縱覽達官顯貴、國家戰事,家敗或戰敗,不是因為驕橫,就是因為懶惰,「驕、惰」二者中必占其一。所以告誡弟弟們要戒掉「傲」字為第一要義。
曾國藩力戒傲字,有過不少經歷。當時的官場上,彭玉麟和曾國荃均是難得一見的將才,二人分別擔任湘軍水師和湘軍陸師將領。彭玉麟(字雪琴)是曾國藩的故交知己,曾國荃是曾的親弟弟。這二位湘軍將領因行事風格不同,彼此交惡,嫌隙越來越深,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曾國荃寫信向兄長抱怨,斥責彭雪琴為人太過於聲色俱厲。說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千里之外,就是看不見自己的睫毛。無論聲音,還是容貌,表現得都是拒人千里之外,可是彭雪琴就是意識不到。曾國藩回覆沅弟:「雪琴的嚴厲,雪琴自己不知道。沅弟的聲色,恐怕也未嘗不嚴厲,僅僅是自己不知道罷了。」
為此他舉了二個例子。咸豐七年冬天,曾國藩埋怨駱文耆(駱秉章)待他實在太刻薄。溫弟曾國華說:「哥哥的臉色,也常常給人難堪。」咸豐十一年春天,馮樹堂極其怨恨張伴山,說其為人傲慢。曾國藩對沅弟說,樹堂的臉色也常拒人千里之外。曾國藩以自己和馮樹堂二個人為例,希望沅弟明白,當他責怪彭雪琴為人傲慢,或許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臉上同樣有傲慢,都是自己看不見自己罷了。
一個人心裡以傲凌物,以此自恃,就會在容貌上反映出來。曾國藩明白了這一點,從咸豐八年起,他力戒驕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人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為第一」,曾國藩勉勵自己,不要忘記當初在蔣市街頭賣菜籃子的光景,勉勵弟弟不要忘了在竹山坳裡拖碑車的情形。以前曾氏兄弟吃過很多苦,在世事無常的世間,又怎能知道以後不會再吃這樣的苦?
身處富貴,不懂謙讓,待人驕橫跋扈,無意中埋下不測禍根。在《顏氏家訓》中收錄了這個故事,北齊時期,太子高緯和琅琊王高儼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琅琊王天資聰穎,勇武過人,他的氣度和見識,在當時無人能望其項背。武成帝與胡皇后都非常寵愛他,允許他穿衣和飲食標準與太子等同,他享有的待遇,不僅超出規格,也超過其他諸王。年幼的琅琊王認不清自己的位置,即使太子哥哥即位為皇帝後,他依然驕蠻放縱,沒有任何節制。他所用器物、服飾等,都要和皇帝哥哥攀比,全然沒有君臣之別。一天,他在南宮看到了新進的冰塊,早熟的李子,便當庭罵道:「我的哥哥已有,為什麼我沒有?」琅琊王隨心所欲,有一些臣子竊竊私語,指責他像春秋時期的共叔段、州吁一樣。因宰相和士開與胡太后私通,穢亂宮闈,琅琊王便假傳聖旨殺了和士開。儘管和士開不得人心,皇帝高緯當時沒有處罰他,但後來還是殺了琅琊王。《顏氏家訓》以琅琊王為鑑,作為戒驕的例子。
曾國藩以史為鑑,恪守謹慎。雖然位高權重,身居極品,待人處世一如既往,如履薄冰。他不希望家族子弟沾染驕奢淫逸,從而招來不測之禍。
參考資料:
《曾國藩家書》
《北齊書》卷十二
《曾國藩全書》第216頁—217頁
《清史稿》卷405@*
點閱【曾國藩·亂世自警】相關文章。@*#
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