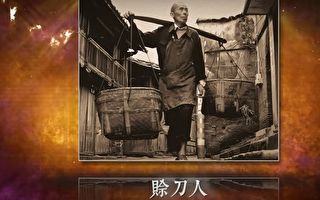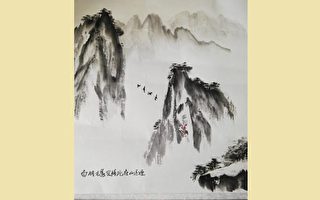這裡要講的幾個故事,大都是我本人親身經歷或者聽親歷者親自講述的,不是事後諸葛亮(就是說事情發生以後才杜撰自己的先見之明)。之所以用了「玄」,就是太奇妙,不可思議的,非常理的,不是現在的科學能夠解釋的。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將全家遣返到幾代人早就離開的老家——檔案上填寫的原籍。因為是「革命」行動,一家老小舉目無親,只好暫且住到地主分子劉先生家裡,一個破房子,他住東間,我們全家擠到西間。
地主分子劉老先生曾經是清朝末年的秀才,雖然那年已經是八十多了,但思維清晰,口齒清楚。同家族裡面他是最後健在的長輩,而且歲數也大了,農村多少還有些老觀念,村幹部不大管他。我們是另類,所以他與我們「臭味相投」,說話不很忌諱。
聽說他是清末的秀才,我很感興趣,晚上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聽他講前朝軼事。
其中一件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劉老先生是這樣說的:
我年小時去萊州府(現在的萊州市)趕考。有一天和同學上街閒逛,見到一個小媳婦到卦攤算卦,她問闖外的男人什麼時候回來。算卦先生叫她測字,小媳婦抽了一個佳人的「佳」字,算卦先生說:「人字旁兩層土,你當家的沒了,你等著料理後事吧,卦錢我也不能要你的了!」
小媳婦聽了嚎啕大哭。這臧乾兒(方言:這時候的意思)驚動了一個騎馬的旗人(劉老先生是指騎馬的清朝官員),他問了問,就拿起馬鞭抽算卦先生兩馬鞭,罵他道:「人命關天的事你怎麼能糊弄人!」他朝哭哭啼啼的小媳婦說:「你不要聽他胡咧咧,我看你的籤和你坐的方位、時辰,你當家的明天某某時辰肯定就回來了!」
年歲多了,那天什麼時辰我記不準了,好像是傍下晚(傍晚)。小媳婦半信半疑道謝了當官的旗人,就回家了。我那時年少也好事,就嘎活同學續著(方言:跟著)小媳婦,看看她住在哪個巷口,想看看那個旗人說的對不對。
第二天我和同學到了小媳婦家的巷口,聽鄰居說小媳婦正在家歡天喜地給男人包穀扎(方言:餃子)。
劉老先生說:「我到於今這麼大年紀,也弄不明白這個旗人是怎麼算出來的,他怎麼就能看著小媳婦坐的方位和時辰就能看得這麼準!」
在昏暗的油燈下,從劉老先生牙齒殘缺的口裡吐出這樣奇怪的軼事,冬季寒風吹得同樣殘缺不齊的窗紙簌簌作響…….
我緊裹棉襖,只能驚歎天下竟有這樣的高人。@◇
點閱【玄——我親歷的故事】相關文章。
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