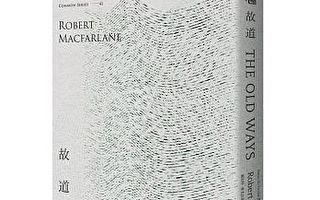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續前文)
開學後不久,我收到巴桑大哥的來信。其中提到了那位我還沒有見過面的回族大哥馬健行,在甘南老家因急性闌尾炎不幸喪命。信中約我於三月十四日下午至昆明湖某玉帶橋頭碰面,參加他們的詩社聚會。
三月十四日下午,天氣極佳,明晴萬里。我準時走向約定的聚會地點。遠遠望見巴桑大哥與一群男女青年聊天。我想:他們一定在指點江山,尋找詩興。又一會,連他們的笑聲也聽得清楚。
我悄自一數,發現有十三人,當我走近時,巴桑也發現了我,立刻上來拉著我的手,對大家說:「這是天民老弟,蘇北漢人,我們的特約佳賓。」
我有些不好意思,只是嘻嘻一笑,向在場的人表示友善。
然後,巴桑向我介紹其他各位同學,說:「劉朗,醉仙,李承德,李夫子,你早已認識。」
另外一一指點他人說:「他叫『馬剛』,回族,武威人;她叫『步木真』,蒙古人,滕格爾老鄉;她叫『王雯麗』,與費雯麗只差個姓,川南人;她叫『唐英』,苗族,苗好仁老鄉,貴州人;她叫『楊雪貞』,白族,大理人;她叫『金喜』,又叫『金芙蓉』,滿族,吉林人;她叫『徐文』,侗族,湘西人,名字像個男子;她叫『古麗』,新疆維人。
除了你早先認識的,新朋友與你都同級。將來我們畢業了,你們仍有許多機會相聚,真是個好緣分。」
巴桑說話時,我隨他手勢打量幾位新友,那馬剛,矮壯,神情持重;那步木真,中等個,短髮,四方臉,單眼皮,看上去,沉靜而敦厚;那唐英不到一米五,清瘦,雙目黑而亮;那楊雪貞大約一米六五,圓臉微胖,明眸皓齒,與電影《五朵金花》中的角色一樣漂亮;那金喜,身材高大,面黑而發亮,精神飽滿;那王雯麗,細高挑,雙目大而明亮,似秋水沉靜,若寒潭深邃;那維族姑娘古麗簡直像個西方的小影星;那徐文一臉活潑,猶如春花迎露,身材嬌小。
幾個人除了步木真與王雯麗看上去約三十歲外,其餘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
巴桑介紹完畢,領大家朝南邊漫步一段行程之後,我才知道巴桑的室友有幾人不願參加詩社,便介紹一些老鄉進來。滕格爾介紹了步木真,苗好仁介紹了唐英,這兩個人又將她們的同學馬剛、楊雪貞、金芙蓉、王雯麗、徐文介紹進來。
他們都是少數民族,年齡不大,竟喜歡漢文古典詩詞,我感到好奇,就問身邊的楊雪貞:「你們白族人也講漢語?」
她說:「講!」
「也懂漢文古典文學麼?」
她說:「有些人是會的,我們白族的祖先中,很多人愛寫漢文格律詩,他們很有學問哩。有的大學者寫的書可多了。」
「舉幾個例子,可以麼?」
她說:「當然可以,比如南詔時有個叫段義宗的官員,就寫得好詩,他有首《思鄉》,還載在《全唐詩》裡面哩。」
她美麗的面龐上顯出快樂而自豪的神情。我剛想說點什麼,她便輕聲地唸唸有詞了:
「瀘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
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
坐久消長燭,愁多減玉顏。
懸心秋月亮,萬里照關山。」
又說:「當時的白族詩人,大都會用漢文寫詩。比如楊奇鯤的『風裡浪花吹又白,雨中山色洗還清』,何等的清新!」
若有所思的她,凝視著湖水。
我問:「想不到古代南疆僻地,有過那麼多的文化精英!」
她說:「可惜的是楊、段作為南詔官員,出使成都,朝拜唐僖宗,都被奸臣高駢陷害致死。是漢人中敗類害死了我們南詔的詩傑。」
我心中頓生悵恨,彷彿段、楊諸人久滯成都,常生鄉思,庭花秋月不能寬慰其懷的羈旅困頓,是我自己的遭遇。
楊雪貞又說:「明朝時,我們白族中的楊甫、李元明、高桂英、楊南金、楊土元,都用漢文寫詩。」
我說:「看來我們楊家是詩人家庭呀。」
楊雪貞嫣然一笑,接著說:「清朝時,我們白族人師範,不但是大詩人,而且也是大學者。」
她停了一下,問我:「你到過成都的武侯祠麼?」
「沒有。」
她說:「那幅著名的楹聯也是白族人寫的。」
「哪一幅?」
她說:「『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人治蜀要深思。』寫這幅聯的人叫趙藩,可是個大詩人,現存的就有一萬多首哩!」
我聽得入迷,覺得身邊的這位白族女生不可小視,心中頗有些肅然起敬。
我們隨人群走至划船處,夷族大哥楊少山租了兩只小船。我們一行十四人,七人一船,向湖心蕩去。我們這船上七人是巴桑、馬剛、醉仙、步木真、金芙蓉、古麗和我,另一船上自然是李承德、楊少山、劉朗、唐英、楊雪貞、王雯麗和徐文七人。
二隻船相隔不遠,並向而行。湖水湛碧,天清氣爽,北面萬壽山雖小而巍峨,樹木叢中,雕樑畫棟,飛彩流輝,玉帶橋玲瓏精緻,遠望如白玉雕成。許久,無人言語,大家都只自默賞風光。@#(未完,待續)
(點閱【小說:海棠詩社】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