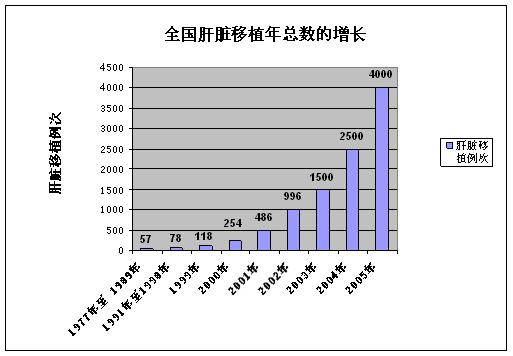王本湘直到下午二點鐘才露面。他一推開房門就連聲道歉,說自己因為臨時有事給耽誤了,覺得實在對不起張恒直。他在道歉的同時,又暗示對方:他已經入了黨,現在是全年級的團總支書記。
「你有什麼事,咱們以後有機會再談吧。」王本湘眼睛望著手錶,皮笑肉不笑地說。「要不,你寫信告訴我也行。今天是禮拜六,我馬上就要去黨總支開會,還差五分鐘。」
張恒直站起來告辭走了。他心裏沉甸甸的。一陣陣的西風撲面而來。楊樹在風中瑟瑟顫抖,發出了沙沙的歎息聲。黃葉、紅葉、棕葉紛紛脫離了枝條,在半空旋卷。張恒直的心也隨著秋風一陣陣地抽縮,無限淒涼、悲戚。他低著頭,眼睛不敢正視前面和左右,一心只希望趕快離開他曾經在這兒生活、學習過的大學。可是兩隻腳好像綁著幾十斤重的大石頭,步伐沉重而緩慢,每向前邁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力氣似的。那條熟悉的洋灰道也彷彿比以前長多了,好不容易走到校門口,猛一抬頭,忽然看見劉玉蘭正好迎面過來,還是穿著那件打補丁的藍布褂子。他嚇了一跳,想趕緊躲起來。但是太晚了,劉玉蘭已經看見他了。
在人類情感的領域裏,女人大概永遠要比男人敏銳些。儘管張恒直一向態度很呆板,劉玉蘭還是微妙地覺察出來了:這個人對待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的眼睛裏似乎還多了點什麼。所以,她此刻碰見他就主動向他點點頭,還抿著大嘴巴微微一笑。這一笑不要緊,可把張恒直羞得滿臉通紅,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鑽進去藏起來。想不到張恒直愈是驚慌失措,劉玉蘭倒愈加受感動,立時悲哀像一陣潮水湧上了她的心頭……
劉玉蘭年紀確實不輕了,比她小一歲的妹妹早在二年前就已經當上了幸福的母親。她因為是個大學生,方圓幾十個村子找不出第二個,家裏左鄰右舍沒有一個敢問津她的的終身。她長得並不漂亮,缺少女性的嫵媚,功課又不好,每學期總得補考一兩門。在大學裏,沒有一個異性注意過她,除了面前這個呆頭呆腦的張恒直……但不幸他是一個右派!
張恒直昏頭昏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農場的。三弟早已等得望眼欲穿,一看見他就遠遠地嚷開了:
「噯!錢帶來了嗎?」
這聲叫喊把張恒直從虛無縹緲的世界帶回到了煩惱的現實。他到大學白走了一趟,不但沒有借到錢,反而將自己身上僅有的一元錢當作車錢花掉了。他又懊惱又著急,心亂如麻,沒了主意,於是就把面前的三弟當作出氣筒臭駡一頓。這回三弟不敢回嘴了,垂著兩手服服帖帖地聽著,內心裏卻恨得發痛發癢。張恒直罵夠了,這才皺著眉頭問道:
「你到這兒來,誰給的盤纏?」
三弟低著頭,心裏盤算著該如何回答。他想起了自己臨走時,郭先生親自趕來送行,給了他一元錢和三個豆餡包子。郭先生還握著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叮囑他:
「請你務必代我向恒直兄問好,祝他鵬程萬里。」
「來的盤纏是郭先生借的。」三弟說,眼睛看著地上的一塊小石子。「他還要我向你烏鱉問好。祝你磅秤萬里。」
「什麼磅秤萬里,你這小王八蛋!為什麼不叫郭先生先寫封信來打個招呼?你以為我錢多得麻袋都盛不下?現在你就去找郭先生吧,讓他給你盤纏回去!我不管!」
「郭先生只借給我來的盤纏呀!是娘叫我來的。娘半年多沒有收到過你的信,你也沒有給娘寄過錢,娘在家不放心,還以為你病了呢!再說,爹死了,娘哭得死去活來,等著你的錢買棺材。」
三弟說得很有道理。大哥閉住了嘴,再也罵不出來了。弟兄兩人你瞅著我,我看著你,心裏都在發愁。幸好有一個「小上海」,上星期剛收到家裏寄來的三十元錢,還來不及花掉,就主動分出一半給張恒直,把他悄悄地叫到一邊,說是借給他的弟弟做盤纏。張恒直紅著臉接受了。他心裏很感激「小上海」:這人又慷慨又善於照顧自己的面子。
「你把這錢拿去買火車票,立刻給我滾回去!」
三弟接過大哥手裏的錢,把三張五元票額的鈔票數了三遍,然後抬起一雙老鼠眼,怯生生地說:
「就這麼點?」
「你要多少!」大哥怒不可遏地咆哮道,兩隻眼睛佈滿了一條條的血絲。「要我把人民銀行給你整個搬來不成?你這王八羔子!在家成天貪吃懶做,不好好幹活,看我揍你不揍你!」
三弟不再說話了。他明白大哥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便回到馬號去取行李。他的行李很簡單,只有一隻布口袋子,裏面除了半袋山芋乾和蘿蔔乾之外,還裝著今天上午剛撿到的一把破鍁頭和半截木梳子。
江濤自始至終都在觀察著這幕悲劇。他從這裏聯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想到了他們在生活裏的艱難困苦和常常遭到的白眼。他的心裏很難受,因此對張恒直弟兄倆個今天的處境感到由衷的同情,掏出了六角錢塞到三弟的手裏:
「小弟弟!別嫌少,帶著路上買幾個燒餅吃吃。」
按照江濤本人現在的收入,六角錢不算少了,他在農場一天幹十多個小時的重活,累折了腰還掙不到這麼多哩!可是張恒直偏偏不領情,將錢從三弟手裏奪過來,一把扔在地上,還向上面啐了一口唾沫。三弟待大哥一回頭,立刻就彎下身子撿起這六角錢,把那幾張毛票團成一團,緊緊地捏在手心裏,幾乎都快要捏出汗來了。
三弟的記性特別好。從火車站到農場的道路,他是一路上求爺爺告奶奶地打聽得來的,現在他用不著再問一句,就能沿著原來的路徑摸回到了火車站。他一邊走,一邊細細地盤算著:買了火車票,大哥給的錢就剩不下幾個了,等於來回白走了兩千多裏。他決心冒點風險,把挨駡得來的錢全部留下來帶回家去。他照抄老文章,花五分錢買了一張月臺票混上了火車。
他有意坐在門廊的邊上,離廁所很近,一旦發現有人查票,可以馬上躲進廁所裏避一避。火車在前進。車輪發出了哢嚓哢嚓的聲音。三弟的思潮也跟著車輪的響聲連綿起伏。他弄不明白大哥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哥以前在離老家六百里的城裏當幹部,掙的錢很多,把家裏安頓得舒舒服服,村裏的人誰見了都羡慕。後來他卻忽然心血來潮,放著幹部不當,跑到北方去上大學,也不和家裏人商量一下。他不知道大學是什麼,但聽郭先生說過,上了大學,他大哥的官就可以做得更大了。既然如此,為什麼上了大學以後,每月給家裏寄的錢卻遠不如從前多呢?而且,幹麼又要到農場去呢?一去農場,乾脆一個錢也不往家裏寄了。郭先生說他大哥當了場長,這話不對。他親眼看見那幫大學生,一個個穿得很破爛,天不亮就扛著農具下地幹累活,一點也不神氣,根本不像幹部的樣子。他也沒有見到漂亮的嫂子。看來郭先生的話是不可信的。大哥倒了楣了。他在農場聽到了一個新名詞:右派。他不懂右派是什麼意思,但知道這斷然不是一個好字眼。他要告訴娘和弟妹們:大哥是右派。不管怎麼說,他現在恨上了大哥:多麼自私啊!他心裏憤憤地罵著:
「沒良心的!娘白養了你!」
在這憎恨的同時,他的心裏又洋溢著愛的感情。娘的棉襖太舊了,今年冬天穿不得了。他要用大哥給的盤纏錢替娘添置一件新棉襖,剩下的錢再扯布給阿香做一身單衣。
阿香是一個老寡婦的女兒,今年二十六歲了,比他還大五歲。因為長一臉麻子,家裏又特別窮,所以總是嫁不出去。他倒不覺得她醜。小時侯,有一次父親嫌他幹活不出數,當場就把他揍了一頓,而且還不許他回家吃午飯。烈日當頭,他一個人坐在地頭邊上哭泣。恰巧阿香路過發現了,安慰了他幾句,還在他手上塞了一個玉米餑餑。他啃著這餑餑,心裏充滿了感激。從這一天起,他便偷偷地愛上了阿香。現在老骨頭死了,他在家裏是最大的,沒有人敢反對他,他要把阿香娶過來當老婆,和娘一起過日子。他得想法子把妹妹們一個一個地嫁出去,好讓娘和阿香的日子過得寬裕些。
三弟坐在火車裏不敢睡覺。他開始在心裏盤算著如何向娘回話。他知道,如果說了實話,把錢全數拿出來,娘有了這些錢作底,一定要東拼西湊,借債買棺材。不如撒個謊,絕了娘的心,他趁機拿一領席子裹上老骨頭的屍體趕快把他埋上算了。他扳著手指頭算了一遍又一遍:做一件棉襖,棉花、裏子和布面要多少錢;做一身單衣又要多少錢。大哥給了他十五元的盤纏;那個姓江的又白送他六角;來的時候娘給了他一元,還有郭先生的一元,再加上自己原有的三元多錢,統共有二十多元呢!足夠實現他的計畫了。
他一邊盤算,一邊啃著山芋乾和蘿蔔乾,還吃了五個雞蛋。這五個雞蛋是娘叫他帶給大哥的。但大哥沒有向他問起過,想必郭先生的信裏沒有提到雞蛋的事,所以他把它們留下來供自己享用了。他感到口渴得很厲害。他堅持著不喝水。喝水得花錢啊!在火車裏,一杯水就要二分錢哩!他來的時候喝過一杯,現在再也不上當了。要是在家裏就好了,水有的是,渴了就一大碗公一大碗公的喝,用不著花半分錢。
火車載著他向南賓士,經過了一站又一站,距他的家鄉愈來愈近了。謝天謝地,一路上還沒有遇到過查票的。他向列車員打聽,知道列車再過半個鐘頭就要到達宿縣了。他把布袋子擰緊(裏面的山芋乾和蘿蔔乾剩下不多了,那把撿的破鍁頭現在凸出了起來),拴上一個活結繫在肩上,開始做下車的準備。他必須在火車進入宿縣車站之前下去,再走三十多裏路,就到家了。車廂裏的光線漸漸地昏暗了下來。他先審慎地環視四周,再走進廁所,立刻鎖上了門。他把錢掏出來再數一遍:一張也沒有少。他身上從來沒有帶過這麼多的錢。有了這些錢,他就可以給娘和阿香添做新衣服了。他懷著狂喜的激情,把廁所裏的窗子開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他做跳車的準備了。他先把頭探到窗外,接著上半身也出去了。他的兩隻手緊緊地死抓住窗框的邊,支撐著全身的重量,右腳首先跨出了窗子,左腳也已經踏到窗邊上了。他該向下跳了。就在這最緊要的關頭,他忽然想起了懷裏的錢,怕它們掉出來丟了。他潛意識地鬆開一隻手,伸到懷裏去摸錢。他的手剛接觸到錢,身子已經滑跌下來了。他只覺得頭部猛烈一震,在茫蒼蒼的暮色中,突然閃過娘和阿香的臉,她們好像兩道火炬照亮了他的眼睛,但立刻就消失在永久的黑暗裏了……
三弟,這個自私而又樸實的小夥子,就這樣離開了人間——懷抱著對娘的摯愛和對阿香的一片柔情蜜意……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