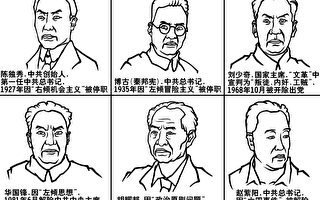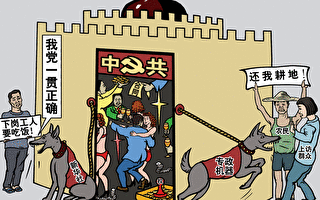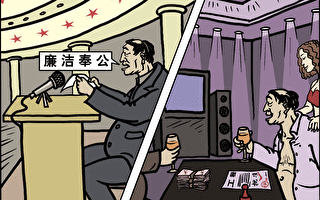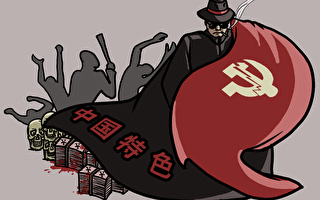《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75)
毛需要知識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會科學的如作家、藝術家、歷史學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學家、技術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別發了一個《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鬥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對在日內瓦會議後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一般要『不劃不鬥』。」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備受優待。
毛著重打擊的是為農民仗義執言的人。《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駁斥『農民生活苦』的無恥讕言」。龍雲的罪名之一是「強調這裡餓死人,那裡餓死人。」孫中山大本營軍需總局局長羅翼群曾說農民「接近餓死的邊緣」。他所在的廣東省組織了一場二十多天的農村「視察」,讓他吃夠了苦頭,由《人民日報》跟蹤報導。「每天,他只要一出門,就有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圍上來」。一天,他的去路「被幾萬憤怒的群眾擠得水洩不通,連汽車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繼續和羅翼群辯理,有人恨得想用傘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戶的商人、店員、小販也都圍上來,痛罵羅翼群。」車身上貼滿了詛咒他的標語。
毛的手段既有鬧劇,也有殺人。毛後來對中共高層說他如何「開捉戒,開殺戒,湖南鬥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
殺人是為了殺一儆百。湖北省漢陽縣的三名教師、圖書管理員為此倒在刑場上。他們的罪名是煽動漢陽一中的學生鬧事。這個縣城的初中生罷課並上街遊行,抗議教育經費又要縮減,嚴重影響農村,「二十個初中畢業生中,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他們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這一事件被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全國報紙都刊登了對他們的死刑判決。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澤東一錘定音,他在宣佈死刑的頭一天(九月五日)到達武漢。他來之前,當地法院對是否判死刑意見不一。
毛政權把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集中在城市裡,特別是「重點學校」,主要培養一小部分從事科學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廣大農民的孩子能認幾個字就行。給縣城學校,國家好歹還投一點錢,村子裡的小學幾乎分文沒有。農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裡,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經費也受到一次大削減。五百萬高小畢業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學。而一百萬初中生中的八十萬畢業後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鎮壓就是為了防備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運動中槍斃的不少,自殺的更多。住在頤和園裡的人早上起來散步,經常會看到樹上吊著一兩個人,還有跳湖自殺的,身體插入湖底淤泥裡,兩隻腳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經歷了鬥爭大會,儘管沒有拳打腳踢,橫眉瞪眼的辱罵也難以忍受。他們的家庭從此成了賤民。為了保護孩子,也為了保護自己,許多人跟右派離了婚。無數家庭就這麼拆散了。
多數右派被遣送到邊遠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勞動力去開墾處女地。新華社記者戴煌後來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攝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凍,他們一百多人睡在一間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裡,麥稈兒苫頂,「窩棚內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零下十幾度,許多人只得穿著鞋和衣而臥。」「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雖管夠,但菜極少,有時只有幾粒黃豆鹹菜,甚至連鹽都缺少。」
「我們每天早晨四點多鐘就起來,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這十五、六個小時內,除了吃三頓飯和洗臉洗腳的時間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頓地勞動,要抽空兒寫封信或洗件衣服,簡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難的『任務』。很多人不得不帶著一些硬紙頭,工間一有小歇就把硬紙頭放在膝蓋上寫起來,一封信往往要寫好幾次才草草寫完。髒衣服和泥襪子只好堆在屋外牆腳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內容,像在原始森林裡伐木,是右派們從來沒幹過的,鋸樹中被砸死、砍傷的不計其數。一邊幹,一邊還要聽「奴隸主對待奴隸般的訓斥」:「你們不要忘記你們是來勞動改造、認罪服法的!你們可不要調皮搗蛋、偷奸要滑!」
戴煌,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給後世的記者,是在知道毛澤東搞「引蛇出洞」後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鯁在喉,非吐不可」,給毛寫了一封長信,說:中共特權階級正在全國各地形成和發展中。在這個新特權階級舉行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會和酒會時,「數以萬千計的災民在啃著草根樹皮呢!」戴煌反對對毛的神化:「在我們國家裡,做了一件什麼好事,或完成了什麼工程,都要向人民說這是『黨的英明』、『毛主席的領導』;甚至連炊事員做好了飯,也要說這是由於『毛主席的領導』。」這個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負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離了婚,全家部受到牽連,「我的一個正在小學執教的年方二十歲的侄兒,患了心尖瓣狹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給他動了手術,就可以挽救這條年輕的生命,但有人說他是我這個大右派的侄兒,他本人又尚未被轉正,就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從北大荒活著回來了。他還算幸運,無數中華民族的精英永遠地長眠在那遙遠的流放之地。
封殺了知識分子反對的聲音,毛澤東集中精力對付中共領導中他認為拖了他軍事工業化後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劉少奇和周恩來。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劉」。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員唱配角的會議。會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週一九五六年縮減重工業建設規模的「反冒進」,跟「匈牙利事件」相提並論,說:「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檢討。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長的職務,當即傳出周行將垮臺的風聲,外交部的高級幹部受到鼓勵公開批周。
毛也激烈指責周手下管經濟的人,使這些人緊張得睡不著覺。南寧會議期間,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徹夜不眠在房間裡不停地來回走,受不了壓力發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見他「語無倫次,精神恍惚。不斷地說:『饒命啊!饒命啊!』」在送他去廣州住院的飛機上,黃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頭說:「饒了我吧。」不到三個星期,他就死在醫院裡,死時才四十六歲。★
(★黃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們結婚時,他是個二十歲的激進學生,江是個十八歲的圖書管理員。在黃的影響下,江青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毛結婚後,江青曾數次約他「談談」,但都被黃敬斷然回絕。這些私事同毛給黃敬施加的壓力並無關係,毛似乎從來沒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慶,毛還特地邀請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納出席招待會,會上介紹見面時,毛握著唐納的手含笑說:「和為貴!」唐納為江青曾兩度自殺,毛或許對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權後,唐納定居巴黎,在那裡終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將召開的加速軍事工業化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面對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當眾作檢討,主要談他如何犯了反冒進的錯誤,被右派分子利用來向黨猖狂進攻,反右運動才使他「開始覺醒」。
寫這樣一份檢討使周恩來痛苦萬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時間,天天關在屋子裡,鬍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風度蕩然無存。寫檢討的方式是周說一句,秘書記錄一句,秘書看到他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建議自己走開,讓他安靜地構思。「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已經深夜十二時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隨叫隨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說:『恩來獨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麼你卻睡覺去了?』」鄧穎超同秘書到了周的辦公室,和周爭論了很久,要他寫。周繼續口授時,「幾乎流出了眼淚」。周選擇鄧穎超做夫人,本來就不是出自愛情,而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鄧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檢討終於叫毛滿意了。這次大會氣勢洶洶,用《人民日報》的話說,是「反對混入黨內的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的會議」。後兩項罪名針對的是各省領導中為本地老百姓說話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他說過這樣一些話: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災害不斷出現,但上繳的糧食太多,以至於「農民家無隔夜之糧」,「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調些糧出省。會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於發表「誰說災區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婦能為無米炊」等妙語的吳芝圃。
劉少奇在會上作的工作報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點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說的「寧可慢一點好」這一類話。小組會上,地方大員對劉進行圍攻,說他批評得不夠,語氣太輕。像周恩來一樣,劉選擇了跟毛走。其他管經濟的人也紛紛作檢討。
毛事先已準備好,誰不聽話,就打成搞陰謀的反黨分子:「不經合法手續」,「進行反對活動」。但到閉幕會上講話時,他提綱上寫的這類話都沒有講。不必講了,人人都已俯首聽命。
劉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來感到威信掃地,他問毛「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毛叫他繼續幹,連外交也還讓他管,儘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長。毛很清楚,論到在外國人面前給他的政權臉上貼金,沒人趕得上周恩來。接替周當外交部長的陳毅後來不無自嘲地說,中國外交都是毛決策,周直接管,他這個外交部長無非是個「大招待員」。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作了一項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檔林彪提拔為黨的副主席。這使得毛在核心領導中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
毛開始強化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毛的個人崇拜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稍有收斂,現在毛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無邏輯地說不贊成個人崇拜的人「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員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主要靠報紙,不僅識字的人看得到,不識字的也知道,因為中國那時有集中起來聽讀報的規矩,不想聽也得聽。毛搞了一連串基層視察,使報紙有機會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個合作社聊了聊天,報上馬上告訴全國人民:「社員們都說:能夠看到毛主席,是一輩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裡的莊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庫鏟了幾鏟土,這幾鏟土大概是毛執政以來的唯一一次勞動,《人民日報》頭版跟著就是一篇妙文:「當毛主庫鏟土的時候,在周圍聚集上萬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細看著毛主席怎樣把一掀一掀的土送進柳條筐裡。毛主席剛一放下鐵掀,一個叫余秉森的解放軍戰士,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這張鐵掀包起來。他激動地說:『看到這張掀,我們就想起了毛主席,這樣,我們的幹勁就會更大。』」所有這一切都在報上詳細報導,使全國人民明白這是他們對毛應有的態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進了家餐館:天津「正陽春」。他理所當然地被認出來了——怎麼可能認不出來呢?他不僅在餐館門口下車,還在樓上餐廳裡打開紗窗,探出頭去。「毛主席!毛主席!」人們開始驚呼,很快數萬人擠在樓前街上歡呼跳躍,喊著「毛主席萬歲」。秘書擔心他的安全,建議毛離開,用身材相仿的警衛戰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絕了。他來餐館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會有任何危險:來前沒人知道,餐樓離人群很遠。環繞餐館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參觀的別處一樣。毛幾次在樓上窗前亮相揮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後對中共高層不無得意地說:「我在天津參觀時,幾萬人圍著我,我把手一擺,人們都散開了。」毛儼然已是上帝。(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