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種無可言喻的思緒裡。他整整祈禱了一夜。第二天,幾個膽大好奇的人,想方設法,要引他談論那個G.代表,他卻只指指天。從此,他對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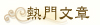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國民公會代表好像沒有注意到「總算」那兩個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開始回答,臉上的笑容全消滅了:「不要祝賀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決過暴君的末日。」
《空山詩選》是一個手抄孤本且內容多為當局所不容,故首先在成都的朋友間傳觀時,就嚴格限制外傳;若需轉抄一律使用作者認可的化名。朋友中間轉抄得最多的是吳鴻、楊楓、羅鶴、熊焰等人。當時,陳墨尚在鹽源,白水已返甘孜,張基仍滯喜德,阿寧、巒鳴、長虹長困滎經。這些友人飛鴻傳書得知《空山詩選》已經搞出卻不得一見,恨得牙癢癢的。阿寧來信說:「行行好,明年新年探親,請務必將《空山詩選》帶來讓滎經諸友一睹為快。」我顧慮太多,不敢遵命。
 2004年8月20日 5:38 AM
2004年8月20日 5:38 AM “全國山河一遍紅”后,成千上万的“紅衛兵爺爺”被赶下了鄉,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网”也越收越緊。我已是成家之人,不得不四處找臨時工做,只要有活干,臟累都不怕,能掙錢養家糊口就行。陳墨屬無業閑雜、東飄西蕩、總感覺被“网”住了,決意邀九九一起到西昌鹽源縣插隊落戶。1970年3月1日晚,是一個“多情自古傷离別”的日子。我和徐坯、羅鶴、馮里、楊楓、云朗、祖祥、伯勞、黎明等10多人,聚在漿洗街辦事處所安排的武侯祠大街一家旅館里,為即將上山下鄉的陳墨、九九送行。大家擠在一個房間內,分坐在兩間床上,亮燈夜敘,或慷慨高談,或激昂闊論,或輕聲叮囑,或掩面暗泣,坐待天明。3月2日晨,一群人浩浩蕩蕩從旅館出來,步行到漿洗街辦事處大門外,送陳墨、九九登上一輛帶篷的解放牌貨車。汽車開始啟動,陳墨忽然從車內人叢中擠到車后擋板前,大聲地向諸友揮手說:“再見了!”一聲未了,他已是淚流滿面。送行諸友受其感染,竟哭聲大起,響成一片:“哭聲直上干云霄”,塵埃不見万里橋。我于當天一气吟成一首《送友人赴山中》,又于第2天寫了1首《似水离愁》。
 2004年8月14日 9:03 AM
2004年8月14日 9:03 AM 1966年7月,“文革”運動已由初期當權派掌控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展到由“紅衛兵爺爺”肆無忌憚大搞打、砸、搶、燒“破四舊”的階段。我在雅安,被單位列為第四類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難保,“天兵天將”們又几次上門查書收書,隨身帶來的一箱書籍也已被收繳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陳墨卻偏在此時突然從成都給我寄來一包書,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藝書籍。其中有一本殘破的民國時期出版的《北極風情話》,顯然是一本禁書。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陳墨一生喜書,無奈家貧,藏書寥寥,忽地將其全部“家當”給我寄來,肯定處境比我更糟,但這樣做于他是損,于我可是禍呀!我無計可施,只得將這包書付諸一炬。
 2004年7月28日 8:29 AM
2004年7月28日 8:29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