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秋,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引人矚目的大事:一件是美國為主英國為輔的美英聯軍打打著『自由‧解放』的旗幟,攻打伊拉克推翻胡森政權之後,仍然受到意外的恐怖襲擊,引起反戰人士的責難,使美國不得不提出一項新的『決議案』,要求聯合國給予必要的支持﹔另一件是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二十三條立法』,引發了五十萬居民『七一』大游行示威抗議,迫使特區政府首長不得不宣佈﹕無限期延後該項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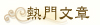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8 人和地的悲哀五十多年來,失敗的『社會主義』實踐,最慘重的兩大失敗是:一、與人鬥;二、與地鬥。兩鬥俱傷的結果可以歸納為一個字:窮。與人鬥和與地鬥,都以『階級鬥爭為綱』,它的遺禍,如同近來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瘟疫,不知道甚麼時候發作,一旦發作就很難收拾。因此,要想消彌『積重』過多的禍害,決非易事。
 2005年2月25日 10:15 PM
2005年2月25日 10:15 PM 7 餓罪難挨一九五九年二月,鋼鐵師『班師』回營。不計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好歹也還是煉出了鋼鐵,至於煉出多少,領導人語焉不詳,大眾又無法過問,好在有毛主席『成積九個指頭,缺點一個指頭』的最終定論,就不必計較了。一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電稱:一九五八年全國鋼產量『躍升』為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不管如何,這個數字起碼符合『大躍進』精神,皆大歡喜。我私下想,這一千多萬噸鋼,不知包不包括鋼鐵師三團小平爐煉出的那塊低炭鋼﹖那是技術員小祁鑑定的,鍛成一把斧頭一把鐮刀之後,由我親自送到省政府大院『鋼鐵師成果展覽會』上。
 2005年2月24日 9:44 PM
2005年2月24日 9:44 PM 6鋼鐵師記實今年的國慶節慶祝大會及大遊行,特別熱鬧,花樣也特別多。因為是『大躍進』年,各行各業都要 以『大躍進的姿態』,『放衛星的成積』,向毛主席和黨中央獻禮。
 2005年2月23日 11:27 PM
2005年2月23日 11:27 PM 5 自留地之爭兩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國北方平原上,演出過一幕驚心動魄的活劇。一群亡命的貴族重冑,在黃土平原上仆仆奔馳。他們雖然仗劍駕車,但看得出來,一個個衣冠不整,疲憊不堪,饑腸轆轆,難以繼續趕路。他們餓狼一般的眼睛,四處搜索,只見荒涼的田壟間,麥苗稀疏,顆粒難覓,哪裡去找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這時,他們發現一個衣衫襤縷的農夫,在田間正低頭彎腰除草,動作遲緩無力。流亡者中一個衣著華麗的年輕人,走下車來,用盡可能客氣的口吻向農夫請求:『請你給我們弄些吃的東西吧!我們幾天沒吃過飯,都快走不動了,你無論如何得幫幫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來的農夫,看了看這一群路過的客人,嘆了一口氣,又彎腰從腳下捧起一大塊泥土,送到年輕人面前,無可奈何的說:『沒有別的了,只有這個給你吧!』
 2005年2月22日 7:22 PM
2005年2月22日 7:22 PM 4 八月,多事之秋 歷史會記住這個時刻。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國現代史上、也許還是世界現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國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在黃帝的故里河南誕生了。在嶺南,第一個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選擇在紫氣橫來、水稻衛星升空的連縣。說來湊巧,我的女兒也在連縣一家醫院裡呱呱墜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國的萬門火炮,對準自己的國土家園金門,輪番轟擊。同時向世界宣稱﹕萬炮轟擊美帝頭子艾森豪威爾!
 2005年2月21日 10:10 PM
2005年2月21日 10:10 PM 3 瘋狂的夏天夏收夏種,是農村最繁忙的季節。繁忙,意味著甚麼,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夠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於上草村,每一個勞動力平均要負擔十二畝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將近一半的田間勞動,要靠每個勞動力的肩膀(挑擔運輸)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時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預料的。
 2005年2月20日 9:36 PM
2005年2月20日 9:36 PM 2 桃花源裡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農業社的一個生產隊。我們在這個生產隊落戶,有點像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我們帶著自己的戶口和糧食定額到這裡來,和社員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參加評工記分,一樣領取工分票。不同的一點是我們的身份是國家幹部,工資關係轉到縣委組織部,按當地的級別工資標準,每人比原來的工資額都少了一級。
 2005年2月19日 4:49 PM
2005年2月19日 4:49 PM 小 引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嶺蔥蘢。 我在深山裡跋涉了七個小時,還不見有一戶人家。這時,西山日落,彤雲滿天,回首來時山路,蒼茫無際。正進退兩難,忽見樹林深處閃出一條人影。等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樣。只見他一身粗布黑頭巾,黑短褂,黑褲衩,頭插一根野雞翎,腰插一把開山刀,腳踏一雙十耳草鞋。他肩上扛著一株枯乾的大松樹,走起路來虎虎生風。我讓在路邊,向他打聽我要去的那個瑤排。他兩道目光閃電一般在我臉上一掃,揚手朝前方一指,腳步如飛,轉眼間消失在濃重的暮靄裡。
 2005年2月13日 4:50 PM
2005年2月13日 4:50 PM 特務長楊標真冤 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我眼前出現一幅如此不可思議的情景﹕兩條細麻繩﹐死死拴住特務長楊標兩個大拇指﹐通過小滑輪用力一拉﹐楊標本能地踮起腳跟﹐就在腳尖離地的一刻﹐他滿臉通紅﹐大汗淋漓﹐殺豬一般地嘶叫起來……。
 2005年2月12日 4:31 PM
2005年2月12日 4:31 PM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2005年2月11日 11:33 AM
2005年2月11日 11:33 AM 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2005年2月8日 11:06 AM
2005年2月8日 11:06 AM 鯉 湖 鎮 一 役一陣激烈的槍聲,震得寒星搖搖欲墜。 鯉湖鎮周圍十幾里數十個村寨、近二十萬民眾,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膽子大一點的人,輕輕開門走出來,黑夜裡互相輕聲打聽,又都茫無頭緒。小北風颳得很緊,不明來歷的槍戰,一陣緊似一陣,似乎還夾雜著一兩聲沉悶的手榴彈爆炸聲,更平添幾多不安和恐懼。有的縮頭躡足,返身入屋,閉門不出。有的披上一件舊棉襖,摸索著走出村口,試圖辨別槍聲的方位,希望得到一點甚麼消息。
 2005年2月7日 2:01 PM
2005年2月7日 2:01 PM 我上小學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歌。老師把簡譜和歌詞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字體端正美觀,便有一種引吭高歌的慾望;老師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學們跟著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裡一高興,課堂上高聲唱,下課獨自哼唱,放學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紀念週會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較清亮圓潤,贏得老師同學讚許的目光,心裡未免有些翹翹然。凡上音樂課,我特別起勁,特別投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