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豬急迫的尖叫聲把他從朦朧的意識中驚醒了。他立刻縱身一跳,還沒等到意識完全清醒過來,就已經奔到母豬旁邊。母豬大概剛挪動過身子,它的後肢右肘下面壓著一頭小豬。那小豬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命,一面聲嘶力竭地呼叫,一面用盡全力掙扎著往外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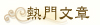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王博生找到一個機會,在人面前敞開嗓子把吳樹文罵了一頓,心裏的氣已消了一大半,現在見宋祖康掏出一包紅棗請客,唾液立時大量地向外分泌,肚子也感到餓了。他是這些人中飯量最大的一個,每月剛過20號,飯票就不夠了,因此晚飯從來沒敢吃飽過一頓。所以,他對食物特別感興趣。
他忽然聽到有人叫他,嚇了一跳,陡地站起來,一邊把血詩藏到衣袋裏,一邊本能地向圈門走去。說話的不是別人,而是王博生:他正站在豬圈外面向裏面張望。宋祖康的緊張情緒稍微緩和了些,這才感覺到心臟的跳動比平時加劇了許多。他機械地過去給王博生開圈門,好讓他進來。
這是一個遭受過流放、並且至死都在受著迫害的詩人:他在沙皇的刺刀下面勇敢地歌頌自由,熱烈地號召人們同情那些為權力的輪子碾碎了的千千萬萬善良的普通人。也許正是普希金,這顆明亮的北極星,激發了萬里迢迢的珠江邊上一個少年美好的天性,教會他去熱愛真理,鄙棄一切醜惡和不義。
念信人顯然頗為得意,不但聲音響亮、清晰,而且還帶著做作的感情,彷彿在向觀眾朗讀一篇臺詞。不管愛聽不愛聽,這聲音直往每個人的耳朵裏鑽,攪亂了宋祖康的沉思默想。他心裏很煩躁,霍地坐起來,將信一把奪過來,隨手往鋪上一扔,一面厲聲地說:「你這瘋子!快要變成《白夜》裏的主人公了!」
打去年冬天以來,他一直對天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這是一個秘密,誰也不知道。他常常在晚上就寢的時候,一邊脫衣服,一邊心裏擔心著明天會不會下雪。啊,上蒼!但願你發點慈悲,可千萬,千萬不能下雪!
「姆媽此刻大概正在廚房裏熱牛奶。再過半個鐘頭爹爹就要上班了。他得吃完早點再上班。姆媽給他倒好牛奶(裏面打了兩個雞蛋),便開始給他切麵包。姆媽切麵包的本事真大,一片片切得很薄很薄,再塗上一層黃油,香噴噴的,可好吃哩!不過我更愛吃果子醬。
冬天來到了。這是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遼闊的國土上升起了舉世聞名的「三面紅旗」,在她們璀璨奪目的光輝照耀下,全國男女老幼幾乎都動員起來了:挑燈夜戰,砸鐵煉鋼,挖渠開河。各行各業都在爭著放「衛星」。「衛星」一個更比一個大。一時間,只見中國的天空「衛星」滿天飛。
王本湘直到下午二點鐘才露面。他一推開房門就連聲道歉,說自己因為臨時有事給耽誤了,覺得實在對不起張恒直。他在道歉的同時,又暗示對方:他已經入了黨,現在是全年級的團總支書記。
俗話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鬥爭會剛剛結束不久,張恒直好不容易地寫出了一封詳盡的長信,正在幻想著市委來給他甄別、平反,生活裏又發生了一椿事。
陳雲甫是星期四中午走的,直到星期一下午才回到農場。湯達淩客套地問過了病情,便拿出自己親筆謄寫的報告交給他審閱。陳雲甫粗粗地看了一下,取出鋼筆準備簽名:反正事情只能是這麼一個結局。
月亮慷慨地灑下了大量銀白色的光耀。湖水是白茫茫的一片。沒有風。湖面上時不時颼颼地閃跳起一兩尾亮晶晶的魚兒,攪動了寧靜的死水。在他後面不遠,有一隻青蛙發出咯咯的哀鳴:它不幸被蛇盤纏住了,正在奮力掙扎著。
江濤介紹完了內容,稍微停頓了一下,潤潤喉嚨,用教師啟發學生的一種語氣總結道:「請大家想一想:除了右派,誰還會寫出這麼惡毒的語言來攻擊我們偉大的黨?你說!你是不是右派?你有沒有蓄意向黨進攻?」
在陳雲甫桌子的對面,坐著一位新來的年輕人,「恒大」捲煙一支接著一支不離嘴。半個月前,湯達淩剛踏進黨委辦公室門檻的當兒,心情是沉重的:他在生活小節上一向不夠檢點,最近在男女關係方面出了點亂子,聽說有人借著這個問題想在他身上做文章。可是當他從同一個門檻邁出來的時候,那兩條短腿變得罕見的輕鬆敏捷。
張恒直看見旗子降落了,就無可奈何地拿起了鐮刀。他打了不一會兒的草,又開始向「小上海」傾吐衷腸,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和痛苦全部倒出來讓「小上海」知道。他多麼強烈地渴望著能有一個人瞭解他呀!這個人就是「小上海」。如果「小上海」能安慰他幾句,他的痛苦就可以減輕些,生活也就有了樂趣。
單調的生活有它自己獨特的節奏。每天天還沒有大亮就下地幹活,肌肉不斷地重複著有限幾個固定的動作,一直重複到太陽落山,重複到黑夜來臨才收工。腦子裏空蕩蕩的,時間過得非常非常的慢。如果不是有一頓中飯調劑,白天的時間將會變得更長更難熬過。
陳雲甫的兩道眉毛緊緊地絞鎖著,那對烏黑的眼睛顯得十分深邃,深邃裏面又似乎包含著疲倦。煙斗在吱吱地響。從鼻子裏噴出了一團團的白煙。房間裏飄蕩著一股氤氳的香氣。他的桌子上放著一堆材料。這幾天他都在研究南區隊的情況,重點是張恒直。他調閱了張恒直的檔案。
在一個寒冷的初春的傍晚,太陽剛剛沉入地平線,它的餘輝正把西邊的天際塗染得如血一般紅。在一間骯髒邋遢的大屋子裏,六個人圍著一個火星全滅了的爐子,你一言我一語地談笑著。這時從另一個屋子裏匆匆走進來一個濃眉方臉的小夥子,這位小夥子,我們在上一章裏已經見過兩面,知道他叫馬偉章。
小王帶來了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師院罷課一說不實。今天是禮拜天,本來就不上課。倒是北大那幫人在那裏碰了一個硬釘子,被師院學生給轟出去了,聽說馬上就要回北京去討救兵。「他們如果再來,」老張興奮地從床上坐起來說道。「不管來多少人,我們也要組織同學把他們轟出去。」
- 1
- 2
共有約 50 條記錄




 2007年9月23日 3:39 PM
2007年9月23日 3:3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