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門的時候,圖書室顯得很安靜,那女巫——如果她確實是的話,舒適地坐在煙囪角落的安樂椅上。她身披紅色斗篷,頭戴一頂黑色女帽,或者不如說寬邊吉卜賽帽,用一塊條子手帕繫到了下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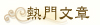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此刻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火爐邊的一群人上了。我很快就明白來人叫梅森先生。接著我知道他剛到英國,來自某個氣候炎熱的國家,無疑那就是為什麼他臉色那麼灰黃,坐得那麼靠近火爐,在室內穿著緊身長外衣的原因了。
 2008年10月18日 3:01 PM
2008年10月18日 3:01 PM 我看到他要娶她是出於門第觀念,也許還有政治上的原因,因為她的地位與家庭關係同他很相配。我覺得他並沒有把自己的愛給她,她也沒有資格從他那兒得到這個寶物。這就是問題的癥結——就是觸及痛處的地方——就是我熱情有增無減的原因:因為她不可能把他迷住。
 2008年10月17日 3:50 PM
2008年10月17日 3:50 PM 那些是桑菲爾德府歡樂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同最初三個月我在這兒度過的平靜、單調和孤寂的日子相比,真是天差地別!如今一切哀傷情調已經煙消雲散,一切陰鬱的聯想已忘得一乾二淨,到處熱熱鬧鬧,整天人來客往。
 2008年10月16日 1:29 PM
2008年10月16日 1:29 PM 據說天才總有很強的自我意識。我無法判斷英格拉姆小姐是不是位天才,但是她有自我意識——說實在相當強。她同溫文而雅的登特太太談起了植物。而登特太太似乎沒有研究過那門學問,儘管她說喜愛花卉,「尤其是野花」。
 2008年10月14日 3:35 PM
2008年10月14日 3:35 PM 我小心翼翼地從自己的避難所出來,揀了一條直通廚房的後樓梯下去。那裡火光熊熊,一片混亂,湯和魚都已到了最後製作階段,廚子彎腰曲背對著鍋爐,彷彿全身心都要自動燃燒起來。
 2008年10月13日 3:51 PM
2008年10月13日 3:51 PM 一個星期過去了,卻不見羅切斯特先生的消息,十天過去了,他仍舊沒有來。費爾法克斯太太說,要是他直接從裡斯去倫敦,並從那兒轉道去歐洲大陸,一年內不再在桑菲爾德露面,她也不會感到驚奇,因為他常常出乎意料地說走就走。
 2008年10月12日 3:26 PM
2008年10月12日 3:26 PM 樓梯上終於響起了吱格的腳步聲,莉婭來了,但她不過是來通知茶點已在費爾法克斯太太房間裡擺好,我朝那走去,心裡很是高興,至少可以到樓下去了。我想這麼一來離羅切斯特先生更近了。
 2008年10月11日 3:49 PM
2008年10月11日 3:49 PM 那個不眠之夜後的第二天,我既希望見到羅切斯特先生,而又害怕見到他。我很想再次傾聽他的聲音,而又害怕與他的目光相遇。上午的前半晌,我時刻盼他來。他不常進讀書室,但有時卻進來待幾分鐘。我有這樣的預感,那天他一定會來。
 2008年10月10日 4:11 PM
2008年10月10日 4:11 PM 什麼東西吱咯一聲。那是一扇半掩的門,羅切斯特先生的房門,團團煙霧從裡面冒出來。我不再去想費爾法克斯太太,也不再去想格雷斯.普爾,或者那笑聲。一瞬間,我到了他房間裡。火舌從床和四周竄出,帳幔已經起火。在火光與煙霧的包圍中,羅切斯特先生伸長了身子,一動不動地躺著,睡得很熟。
 2008年10月9日 3:57 PM
2008年10月9日 3:57 PM 我們進屋以後,我脫下了她的帽子和外衣,把她放在自己的膝頭上,坐了一個小時,允許她隨心所欲地嘮叨個不停,即使有點放肆和輕浮,也不加指責。別人一多去注意她,她就容易犯這個毛病,暴露出她性格上的淺薄。這種淺薄同普通英國頭腦幾乎格格不入,很可能是從她母親那兒遺傳來的。
 2008年10月8日 4:00 PM
2008年10月8日 4:00 PM 在日後某個場合,羅切斯特先生的確對這件事情作了解釋。一天下午,他在庭院裡碰到了我和阿黛勒。趁阿黛勒正逗著派洛特,玩著板羽球的時候,他請我去一條長長的佈滿山毛櫸的小路上散步,從那兒看得見阿黛勒。
 2008年10月7日 3:25 PM
2008年10月7日 3:25 PM 我自己也有很多過失,我知道。我向你擔保,我不想掩飾,上帝知道,我不必對別人太苛刻。我要反省往昔的經歷、一連串行為和一種生活方式,因此會招來鄰居的譏諷和責備。
 2008年10月6日 3:34 PM
2008年10月6日 3:34 PM 他的胸部出奇地寬闊,同他四肢的長度不成比例。我敢肯定,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是個醜陋的男人,但是他舉止中卻無意識地流露出那麼明顯的傲慢,在行為方面又那麼從容自如,對自己的外表顯得那麼毫不在乎,又是那麼高傲地依賴其他內在或外來的特質的力量,來彌補自身魅力的缺乏。
 2008年10月5日 3:39 PM
2008年10月5日 3:39 PM 後來的幾天我很少見到羅切斯特先生。早上他似乎忙於事務,下午接待從米爾科特或附近來造訪的紳士,有時他們留下來與他共進晚餐。他的傷勢好轉到可以騎馬時,便經常騎馬外出,也許是回訪,往往到深夜才回來。
 2008年10月4日 3:32 PM
2008年10月4日 3:32 PM 遵照醫囑,羅切斯特先生那晚上床很早,第二天早晨也沒有馬上起身。他就是下樓來也是處理事務的,他的代理人和一些佃戶到了,等著要跟他說話。阿黛勒和我現在得騰出書房,用作每日來訪者的接待室。
 2008年10月2日 4:07 PM
2008年10月2日 4:07 PM 這匹馬已經很近了,但還看不見。除了得得的蹄聲,我還聽見了樹籬下一陣騷動,緊靠地面的榛子樹枝下,悄悄地溜出一條大狗,黑白相間的毛色襯著樹木,使它成了一個清晰的目標。這正是貝茜故事中,「蓋特拉西」的面孔,一個獅子一般的怪物,有著長長的頭髮和碩大無比的頭顱,它從我身旁經過,卻同我相安無事。
 2008年10月1日 4:05 PM
2008年10月1日 4:05 PM 我初到桑菲爾德府的時候,一切都顯得平平靜靜,似乎預示著我未來的經歷會一帆風順。我進一步熟悉了這個地方及其居住者以後,發現這預期沒有落空。費爾法克斯太太果然與她當初給人的印象相符,性格溫和,心地善良,受過足夠的教育,具有中等的智力。
 2008年9月30日 4:06 PM
2008年9月30日 4:06 PM 給一位兒童歌手選擇這樣的題材,似乎有些離奇。不過我猜想,要她表演目的在於聽聽用童聲唱出來的愛情和嫉妒的曲調。但那目的本身就是低級趣味的,至少我這樣想。阿黛勒把這支歌唱得悅耳動聽,而且還帶著她那種年紀會有的天真爛漫的情調。唱完以後,她從我膝頭跳下說:「小姐,現在我來給你朗誦些詩吧。」
 2008年9月29日 4:04 PM
2008年9月29日 4:04 PM 費爾法克斯太太客氣地跟我道了晚安。我閂上了門,目光從容四顧,不覺感到那寬闊的大廳、漆黑寬暢的樓梯和陰冷的長廊所造成的恐怖怪異的印象,已被這小房間的蓬勃生氣抹去了幾分。這時我忽然想到,經歷了身心交瘁的一天之後,此刻我終於到達了一個安全避風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2008年9月28日 3:27 PM
2008年9月28日 3:27 PM 一部小說中新的一章,有些像一齣戲中的新的一場。這回我拉開幕布的時候,讀者,你一定會想像,你看到的是米爾科特喬治旅店中的一個房間。這裡同其他旅店的陳設相同,一樣的大圖案牆紙,一樣的地毯,一樣的傢具,一樣的壁爐擺設,一樣的圖片,其中一幅是喬治三世的肖像,另一幅是威爾士親王的肖像還有一幅畫的是沃爾夫之死。
 2008年9月27日 3:25 PM
2008年9月27日 3:25 PM 一到家便有種種事務等著我去做。姑娘們做功課時我得陪坐著,隨後是輪到我讀禱告,照應她們上床。在此之後,我與其他教師吃了晚飯。甚至最後到了夜間安寢時,那位始終少不了的格麗絲小姐仍與我作伴。燭台上只剩下一短截蠟燭了,我擔心她會喋喋不休,直至燭滅。
 2008年9月26日 4:11 PM
2008年9月26日 4:11 PM 到目前為止,我已細述了自己微不足道的身世。我一生的最初十年,差不多花了十章來描寫。但這不是一部正正規規的自傳。我不過是要勾起自知會使讀者感興趣的記憶,因此我現在要幾乎隻字不提跳過八年的生活,只需用幾行筆墨來保持連貫性。
 2008年9月25日 3:20 PM
2008年9月25日 3:20 PM 六月初的一個晚上,我與瑪麗.安在林子裡逗留得很晚。像往常一樣,我們又與別人分道揚鑣,閒逛到了很遠的地方,遠得終於使我們迷了路,而不得不去一間孤零零的茅舍回路。那裡住著一男一女,養了一群以林間山毛櫸為食的半野的豬。回校時,已經是明月高掛。
 2008年9月24日 3:21 PM
2008年9月24日 3:21 PM 然而,羅沃德的貧困,或者不如說艱辛,有所好轉。春天即將來臨,實際上已經到來,冬季的嚴寒過去了。積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風不再那般肆虐,在四月和風的吹拂下,我那雙曾被一月的寒氣剝去了一層皮,紅腫得一拐一拐的可憐的腳,已開始消腫和痊癒。
 2008年9月23日 3:46 PM
2008年9月23日 3:46 PM 我講完了。坦普爾小姐默默地看了我幾分鐘,隨後說:「勞埃德先生我有些認識,我會寫信給他的。要是他的答覆同你說的相符,我們會公開澄清對你的詆毀。對我來說,簡,現在你說的相符,我們會公開澄清對你的詆毀。對我來說,簡,現在你已經清白了。
 2008年9月22日 3:45 PM
2008年9月22日 3:45 PM 半個小時不到,鐘就敲響了五點。散課了,大家都進飯廳去喫茶點,我這才大著膽走下凳子。這時暮色正濃,我躲進一個角落,在地板上坐了下來。一直支撐著我的魔力消失了,被不良反應所取代。我傷心不已,臉朝下撲倒在地,嚎啕大哭起來。海倫.彭斯不在,沒有東西支撐我。
 2008年9月21日 4:26 PM
2008年9月21日 4:2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