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弟子麗菊有一次和我同車去醫院,她的腿也被酷刑折磨成一瘸一瘸的。麗菊三十剛出頭,進勞教所前是廣州一所高校的英語老師。她一見我,對我一笑。麗菊總是在最艱難、危險的時候都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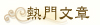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去了幾次醫院後,我的腳只是消了一些腫,醫生們對我傷殘的腿毫無辦法。其實,每次去醫院的路途勞頓對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的我來說,只是一種折磨。
 2009年10月4日 6:16 PM
2009年10月4日 6:16 PM 一回到牢房,「挾控」遞給我一個鐵飯盒,裡面是我的晚飯。我吃了一口發現那飯還有一點溫熱。這是我兩年多來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吃到熱飯。
 2009年10月3日 2:44 PM
2009年10月3日 2:44 PM 廣州市區建起了不少新的高樓大廈,但我對這些毫無感覺。因為這片土地仍然和兩年前一樣,沒有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信仰的自由。
 2009年10月2日 2:41 PM
2009年10月2日 2:41 PM 我的腿被折磨致殘後,他們從未帶我去過醫院,也不在乎我的腿怎麼樣。現在他們大概知道沒希望逼我妥協了,轉而希望盡快抹掉他們施酷刑的罪證。
 2009年10月1日 2:37 PM
2009年10月1日 2:37 PM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七點,三大隊教導員來到牢房,要我站到牢房的一個角落直到願意放棄法輪功為止。她命令倆個「挾控」在我耳邊大聲讀中共的宣傳材料,不許我坐、不許我睡。
 2009年9月28日 3:50 PM
2009年9月28日 3:50 PM 那時天氣非常寒冷,看守們穿著厚厚的軍大衣還冷的瑟瑟發抖。她們總是到晚上九點左右才允許我去沖涼。冰冷的水一澆到身上,身體凍的冒煙,傷腿馬上凍的僵硬、更加紅腫疼痛。
 2009年9月26日 2:48 PM
2009年9月26日 2:48 PM 在這次酷刑前我一直善意、真誠的和看守溝通,盡力使她們明白大法的真相。酷刑後我變的非常沉默。我意識到這個時候語言已經沒有用,唯有依靠對大法的堅定去震懾邪惡。
 2009年9月25日 2:42 PM
2009年9月25日 2:42 PM 剛開始我是看的。看中共怎麼造謠。放完「天安門自焚」的錄像後看守問我:「看完這個,你該放棄法輪功了吧?」我說那是假的。然後我一一給她們指出來其中的造假之處,聽的她們無話可說。
 2009年9月24日 2:17 PM
2009年9月24日 2:17 PM 看守強迫我終日坐在牢房的小塑料凳上看中共誹謗法輪功的宣傳材料。她們時不時透過牢房鐵門上的一個小洞監視我和阿玉在裡面的情況。
 2009年9月23日 2:14 PM
2009年9月23日 2:14 PM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從大會召開的前五個月開始,槎頭女子勞教所對所有堅定的大法弟子開始了新一輪的酷刑迫害。
 2009年9月20日 4:42 PM
2009年9月20日 4:42 PM 三小時後車開到一所監獄大門口。這所監獄位於一大片光禿禿的荒蕪之地上,四周什麼都沒有,讓人感覺沒有任何逃出去的希望。在監獄大門前,車子停下接受檢查。
 2009年9月19日 2:51 PM
2009年9月19日 2:51 PM 槎頭女子勞教所不允許大法弟子閱讀任何東西,除了中共誹謗法輪功的宣傳材料;也不准大法弟子寫任何東西,除了每月一封的家信和看守佈置的「作業」。
 2009年9月18日 2:43 PM
2009年9月18日 2:43 PM 我被關在三大隊時,脾氣暴躁的監工總在工廠用惡毒的語言罵我、侮辱我,說我幹活笨手笨腳之類。我默默忍受、從不回嘴,同時不斷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2009年9月15日 2:53 PM
2009年9月15日 2:53 PM 七點,長長一天的苦役開始。在污染的工廠裡,被關押者被迫製造和加工各種各樣的產品:假花、衣服、牛仔褲、毛衣、袋子、耳環、項鏈、聖誕卡、玩具、徽章……
 2009年9月11日 1:28 PM
2009年9月11日 1:28 PM 儘管丈夫的話傷人,我沒和他爭吵,我從未把聲音提高哪怕一點點。說再見時他冷若冰霜的轉身就走,我過去溫柔的擁抱他、謝謝他來探視我。
 2009年9月9日 9:15 PM
2009年9月9日 9:15 PM 別的被關押人員家屬可以一周來勞教所探視一次。而大法弟子不被允許給家人打電話;一月准許寫一次的家信其實也全被看守沒收;家人也不許來勞教所探視,除非勞教所想通過家人給大法弟子施壓時,才會允許他們短暫的探視。
 2009年9月6日 2:33 PM
2009年9月6日 2:33 PM 有一次,關在槎頭女子勞教所的所有大法弟子被集中到一個大房間,大群看守緊張的圍住我們戒備,說是請來了中共黨校的一個教授給我們上「思想教育課」。
 2009年9月4日 2:25 PM
2009年9月4日 2:25 PM 看守為此用各種方法迫害我們,包括把我們關進禁閉室折磨、延長我們在勞教所的期限,但我們都堅持不妥協。從那以後,大法弟子和他們平等的站著說話。
 2009年8月29日 2:00 PM
2009年8月29日 2:00 PM 那時正值熱帶盛夏,小島上更炎熱,氣溫常達攝氏三十度以上。看守們強迫我在正午最毒辣的太陽底下連續跑步、操練幾個小時,使紅瘡更加又癢又疼。
 2009年8月23日 2:37 PM
2009年8月23日 2:37 PM 我丈夫在我被綁架的翌日回到家,見一地狼藉、電話線被扯斷、妻子失蹤,以為竊賊進了屋,馬上報警。警察卻叫他問610。他問了610後才知道:我被抓進了看守所。
 2009年8月21日 2:30 PM
2009年8月21日 2:3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