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彷彿覺得他剛從一場莫名其妙的夢裡醒過來,又看見自己正在黑夜之中,從一個斜坡滑向一道絕壁的最邊上;他站著發抖,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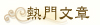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經過了多年的懺悔和忍辱,他修身自贖,也有了值得樂觀的開端,到現在,他在面臨那咄咄逼人的逆境時,如果仍能立即下定決心,直赴天國所在的深淵,毫不反顧,那又是多麼豪放的一件事
我們已向那顆良心的深處探望過,現在是再探望的時刻了。我們這樣做,不能不受感動,也不能沒有恐懼,因為這種探望比任何事情都更加觸目驚心。
快到半夜時,他忽然醒過來;他在睡夢中聽見在他頭上有響聲。他注意聽。好像有人在他上面屋子裡走路,是來回走動的步履聲。他再仔細聽,便聽出了那是馬德蘭先生的腳步。
斯戈弗萊爾回答,一面又用他大拇指的指甲刮著桌面上的一個跡印,一面用佛蘭德人最善於混在他們狡猾裡的那種漠不關心的神氣說:「我現在才想到一件事。市長先生沒有告訴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市長先生到什麼地方去呢?」
誰也看不出散普麗斯姆姆的年紀,她從不曾有過青春,似乎也永遠不會老。那是個安靜、嚴肅、友好、冷淡,從來不曾說過謊的人,我們不敢說她是個婦人。
沙威望著馬德蘭先生,在他那對天真的眸子裡,我們彷彿可以看見那種剛強、純潔、卻又不甚了了的神情。他用一種平靜的聲音說:「市長先生,我不能同意。」
沙威擺著他那副堅定而憂鬱的面孔答道:「市長先生,真理總是真理。我很失望。叫冉阿讓的確是那人。我也認出了他。」馬德蘭先生用一種很低的聲音接著說:「您以為可靠嗎?」
馬德蘭先生正在他辦公室裡提前處理市府的幾件緊急公事,以備隨時去孟費郿。那時有人來傳達,說偵察員沙威請見。馬德蘭先生聽到那名字,不能不起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德納第不肯「放走那孩子」,並且找了各種不成理由的借口。珂賽特有點不舒服,冬季不宜上路,並且在那地方還有一些零用債務急待了清,他正在收取發票等等。
沙威在當天晚上寫了一封信。第二天早晨,他親自把那封信送到濱海蒙特勒伊郵局。那封信是寄到巴黎去的,上面寫著這樣的字:「呈警署署長先生的秘書夏布耶先生」。
她剛才見到她自己成了兩種對立力量的爭奪對象。她見到兩個掌握她的自由、生命、靈魂、孩子的人在她眼前鬥爭,那兩個人中的一個把她拖向黑暗,一個把她拖向光明
當馬德蘭先生說了剛才大家聽到的那個「我」字以後,偵察員沙威便轉身向著市長先生,面色發青,嘴唇發紫,形容冷峻,目光凶頑,渾身有著一種不可察覺的戰慄
沙威一直立著沒有動,眼睛望著地,他在這一場合處於一種極不適合的地位,好像一座曾被人移動、正待安置的塑像。門閂的聲音驚醒了他。他抬起頭,露出一副儼然不可侵犯的表情
幾分鐘以前,已有一個人在眾人不知不覺之間進來了,他關好門,靠在門上,聽到了芳汀的哀求。正當兵士們把手放在那不肯起立的倒霉婦人身上,他上前一步,從黑影裡鑽出來說:「請你們等一會!」
聽見了那種威嚴的句子「永生的天父親自到來也沒有辦法」時,她知道這次的判決是無可挽回的了。她垂頭喪氣、聲嘶喉哽地說:「開恩呀!」
沙威分開觀眾,突出人牆,拖著他後面的那個苦命人,大踏步走向廣場那邊的警署。她機械地任人處置。他和她都沒說一句話。一大群觀眾,樂到發狂,嘴裡胡言亂語,都跟著走。
她那種反應一定刺激了這位吃閒飯的人,他乘她轉過背去時,躡著足,跟在她後面,忍住笑,彎下腰,在地上捏了一把雪,一下塞到她的背裡,兩個赤裸裸的肩膀中間。那妓女狂叫一聲,回轉身來,豹子似的跳上去
他們更有錢一些,人家會說「這些都是佳公子」;假使他們更窮一些,人家也會說「這些都是二流子」。這種人乾脆就是些遊民。在這些遊民中,有惱人的,也有被人惱的,有神志昏沉的,也有醜態百出的。
芳汀的故事說明什麼呢?說明社會收買了一個奴隸。向誰收買?向貧苦收買。向饑寒、孤獨、遺棄、貧困收買。令人痛心的買賣。一個人的靈魂交換一塊麵包。貧苦賣出,社會買進。
芳汀把她的鏡子丟到窗子外面。她早已放棄了二樓上的那間小屋子,搬到房頂下的一間用木閂拴著的破樓裡去了;有許多房頂下的屋子,頂和地板相交成斜角,並且時時會撞你的頭
那拔牙的走方郎中見了這個美麗的姑娘張著嘴笑,突然叫起來:「喂,那位笑嘻嘻的姑娘,您的牙齒真漂亮呀!假使您肯把您的瓷牌賣給我,我每一個出價一個金拿破侖。」
維克杜尼昂夫人有時看見她從她窗子下面走過,看出了「那傢伙」的苦難,又想到幸而有她,「那傢伙」才回到「她應有的地位」,她心裡一陣高興。黑心人自有黑幸福。
一天早晨,車間女管理員交給她五十法郎,說是市長先生交來的,還向她說,她已不是那車間裡的人了,並且奉市長先生之命,要她離開孟費郿。
馬德蘭抬起頭來,正遇到沙威那雙鷹眼始終盯在他的臉上,馬德蘭望著那些不動的農民,苦笑了一下。隨後,他一言不發,雙膝跪下,觀眾還沒來得及叫,他已到了車子下面了。




 2010年6月21日 1:11 PM
2010年6月21日 1:11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