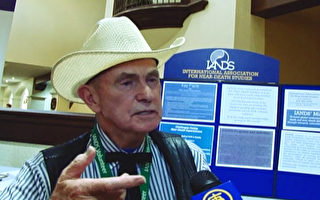上无片瓦下无锥地 同甘共苦结连理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上海这座饱受战乱祸害的城市也渐渐苏醒。“三层楼”附近沿恒丰路、裕通路马路旁,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又重新建起了新的住宅,父亲的木匠活儿多了起来。找母亲的除了缝补旧衣衫之外,要裁缝新衣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父母手头有了积蓄,便合计着也要在小木棚原址上重建一个新屋。于是,父亲白天外出给人家盖房造屋打工挣钱,晚上就在家给自己干活。又是夯土打基础,又是和泥砌砖墙,集木匠、泥瓦匠、小工于一身,足足花了三个多月,1946年初秋,一个砖木结构的新房建成了,还是座带阁楼的小屋。
由于父亲的精湛技术和独到匠心,小楼盖得小巧玲珑,逗人喜爱。落成不久,便被一个在警察局当文书的小吏看中,央求曾宝元说合,死活纠缠着父亲,让立即卖给他,说是因为他妻小马上就要从乡下回来了。为了便于让父亲尽快搬家,还给父亲在广肇路梅园路口买了一间茅草屋。碍于曾先生的情面,父亲答应了。于是父母亲又搬到仅隔一箭之遥的茅屋里。茅屋虽简陋,还透风漏雨,但地皮却比原来的大。父亲便再度集泥水、木工于一身,没日没夜的干了起来。不同的是,这次有了帮手,他们的几个同事互相换工,帮衬着一家一家地盖新房。人多力量大,不到两个月,又一座新房落成了。而此时,母亲36岁,父亲也已进入不惑之年了。不惑之年的父亲,却在人生道路上迷惑了。
自从县大队解散,他带着母亲潜身于大上海之后,曾背着母亲数次偷偷打探家乡的消息,想寻找原来的组织,伺机返回故里。但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信息阻隔,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直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造反派审查、迫害,被逼写“交代”时,我才知道,早在1942年,当他得知姚俅在他之前已经潜入上海,并和他见面以后,曾萌生过寻找组织的想法。尽管他知道姚俅的身份非同一般,但出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任何人不得擅自去联系非同一组织机构的人,更何况要在这茫茫人海的大上海中。于是,他也只能放弃了主动寻找,而被动地等待上面派人和他联系。奇怪的是,他们从未派出任何人寻找过父亲。就这样,父亲与组织脱离了关系。此时他已经和母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年。
四年里两个人相依为命,互相帮衬,从上无片瓦之盖,下无立锥之地,到拥有了自己的蜗居。在漫长的同甘苦共患难之中,他们理所当然成了一家人,尽管父亲在故乡还有一个拥有五个子女的家。这种现象当时在中共中、高层的干部中相当普遍。不同的是那些干部们后来通过种种方式解除了旧婚约,但与中共组织失联的父亲却成了一个普通工人,自然也就没有管道解除旧婚约并让这第二次的婚姻合法化了。
生不逢时体多病 茹苦含辛慈母恩
1947年,在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和平,再度同室操戈之际,我来到了人世间。3月4日凌晨,也许是冥冥之中得到“这世界并非那么完整迷人”的暗示,也许是幼小的心灵已经预见到未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不幸。反正,我脱离母胎后,有一瞬间,是既不啼哭,也无声息,以顽强的沉默抵抗着尘世的污浊。
这可吓坏了接生的婆娘——我们的邻居戴大妈,也急坏了分娩体虚的母亲。母亲让戴大妈再次把我倒提起来,拍打我的小屁股,我仍是坚不吭声。父母亲几乎绝望了,以为没救了。忽然奇迹出现,我们家房屋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水塘,不知是谁家养的鸭子,那天早早的出了窝,来到池边戏水觅食,高声地叫呱着。这鸭子的尖声呱叫居然惊醒了我,旋即大声啼哭了起来。
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为自己中年得子而庆幸,以为后半生可以有了依靠,从此,她的生活便有了新的希望。殊不知,我的出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艰难和困苦。
母亲是高龄生育,加上生活艰辛、营养不良,所以根本没有奶水,于是便把我托给邻居戴大妈哺育。不到一岁,还没断奶时,我患了百日咳,白天咳得没法吃奶,到夜晚是又饿又咳,彻夜啼哭不已。母亲一筹莫展,只好整夜把我抱在怀里,慢慢的摇晃,轻轻地哄拍。整整熬了将近两个月,我才渐渐好转。将近一周岁的我,又病又饿,瘦得只剩皮包骨,看上去还不及人家六、七个月的婴儿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时常是含着泪水喂我吃药,哄我入眠的。母亲的心血都快熬干了。
1949年春,上海“解放”。是年底,家中又添一丁,弟弟问世了。1953年朝鲜战场停战。此后社会相对的稳定了一段时期,百姓得以养生安息,市场也渐渐繁荣。父亲由姚俅(此时他已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并担任了闸北区的副区长)介绍,进入了国营单位“华东建筑工程公司”,当上技术工人,等级为木工六级,收入颇丰,家境摆脱了窘促,日见富裕起来。
我五岁不到,便被送进我们家后弄堂里的私塾馆。这是一个稍宽敞的民宅,客堂里摆上了二排共六张长桌,12个孩童在这里念着不同程度的课程。教书先生一会儿教右边一溜大一点的孩子念唐诗,一会儿教左边小一点的孩子学识字。少不更事的我,只是坐在长木桌旁边,傻傻地看着学长们读书写字,时而顺手撕下一页课本纸,塞进嘴里,咀嚼半天再吐出来。别人是看书识字,而我也就只有吃书的分儿了。
当时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这么早把我送进私塾,这不是糟蹋学杂费么?后来才知道,父亲进了建筑公司以后工作日见繁忙,母亲一人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弟弟已是十分辛劳。再加上此时邻居已大多知道我母亲是个缝纫好手,纷纷上门求艺,为孩子们添置新衣。活计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母亲情面难却,便一一接了下来。为了便于照料弟弟,也为了有时间完成手中针活,便将我送进了私塾学堂。那时,母亲虽然十分辛劳,但内心却充溢着甘甜。看着长子每天拿着残缺不全的课本,跳跳蹦蹦地走进后弄堂的私塾馆,她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父巧手平地起楼 悲欢离合三代同堂
1953年广肇路拓宽马路,由原来的不足三丈,拓宽到六丈。沿街面北侧拆除了两排房屋,我们原本地处弄堂内第三排的房屋便成了临街面的门面房。母亲由此产生了新的忧虑,马路拓宽,车来人往,顽童的安全成了问题。父母亲商议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卖掉临街面的房屋,另择弄堂房居住。
成年以后,我每每想到此事,不知怎的,总会不由想起“孟母三迁”的典故。恰巧,有人找到米行老板曾宝元(曾先生早年伙同父亲贩卖布料,亏本后改行贩米,数年后,竟开了家米行。)要买新居,看到我们那座马上要变成临街的房屋,立马下订,并约定半年之内我们必须搬迁。
又是姚俅帮了大忙,替父亲在单位请了长假,介绍认识了来自盐城的同行邵玉麒和其他二个师傅。几个人买下了位于民立路、共和路口的一个旧煤场,计划建造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屋80余间。消息一传出,许多人入股参与了进来。在这众多的参股者之中,父亲惊奇地发现失散多年的亲侄女也在其中。此时的她已是上海申新九厂(后为国棉二十二厂)的团委副书记了。当她得知我父亲——她的叔叔准备集资盖一个新式里弄住宅区的消息后,立即找到了父亲,希望能参与进来。父亲喜不自禁,马上答应并同邵玉麒师傅等人约定,她的住房建筑工本费全免了,由父亲亲自出工建造。考虑到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安全,所以将她的住房安排在社区中间(民立路200弄36号)。
由此,父亲干脆就同大家商定,工匠们出力为大家盖房,工钱打折,折扣的部分抵充自家房屋的建筑材料。就这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工程开工了。父亲白天为别人架屋上梁,晚上在自家砌墙盖瓦,累得几乎散了骨架。半年之后,新房落成了。
1954年夏,我们从广肇路搬到了民立路190号新居。在这个屋子里,我度过了青少年的黄金时段,也和父母一起熬过了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又一起度过动乱的“文革”十年。也是在这个屋子里,我自己娶妻生子,成为人父,最终,在这个屋子里,我先后送走了年迈的双亲。
新居楼上楼下建筑面积近80平米,顶高达7米,在50年代初期,算是很大的住房。父母为此花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上一身债。为还债,不得不将住房的大部分出租,自己一家四口则蜗居在约14平方米的中厢房和不到10平米的灶间内。中厢房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卧室,灶间则是日常起居做饭、接待来客的地方。同样为了还债,母亲再一次操起了女红。而父亲则在工作之余,为左邻右舍打起了零工。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中厢房靠墙的一张大床上的情景。为了能让四个人卧睡得下,父亲在靠墙边的床内档加上一块一尺余宽的木板,把它变成六尺半的大床。我和弟弟合盖一床被,分开两头睡在床里档,父母睡在外沿。
每每半夜醒来,总能看见母亲坐在床沿,在微弱的灯光下飞针走线。为了省电,家里用的灯泡是15瓦的,光线很暗,母亲经常要下床站着,踮起小脚,迎着灯光穿针引线。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多么不懂事啊!深更半夜看见母亲还在灯下操劳,有时总不免咕噜一声:“还不睡啊!”尽管话里有着关心和体贴,但母亲肯定也能从中听出了一些“灯光影响睡眠”的不满。于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睡眠,昏暗的灯泡上又罩上了一个黑布罩!
父亲则是自己取消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自1955年至1957年将近三年里,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邻居或亲戚朋友家打零工。有时修理一下门窗、家具,有时做点新的桌椅板凳什么的。偶尔也有人请他做全新的家具,诸如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什么的。除非是陌生的客户,一般的邻居、亲朋好友他从不收任何费用,有时还倒贴一些原木材料。亲朋好友们甚是过意不去,常常是除了提供午餐便饭之外,还经常留他晚上小酌一番。回到家,他朝我们笑笑说:“省了家里一顿。”近三年时间里,他走遍了里弄里每一户人家,也几乎尝遍了每一家的菜肴。(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