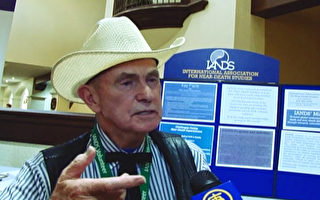文革无情毁家园 双亲无辜受摧残
1966年,我高中毕业,父母亲期盼我能考上大学,为他们增光。可是“文化大革命”无情地破灭了我进大学的梦想,也击碎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期盼。那年深秋,我和高中同学一起“大串联”,走遍了小半个中国。归途中患上了急性大叶性肺炎,回到上海就住进了市肺科医院。父母亲惊恐万分,日夜担忧。短短的半年多里,他们竟来院探望了二十多次,当时从闸北的民立路要到复旦大学后面的肺科医院,得转四部公车,整整坐两个小时,还要步行一大段路。母亲那双小脚得多难哪!我曾多次劝过她,让她别来,甚至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她默默地笑笑,点点头说声:“知道了!”可是没多久,她又和爸爸一起来了。唉,我可怜的妈妈,可敬的爸爸!
出院后,他们像看守犯人一样守着我,除了去医院复查,几乎不让我出门半步。在家养病的半年多里,父亲以耳疾为由提前退休,让弟弟顶替他在房地产公司上了班。而他自己则和另外的几个师傅结伴专门给人家做新婚家具,以补贴家用。那时候,家具也是凭票供应的。票证由单位统一发放。有些人等了许多年才能分到一张大橱票。新婚的夫妇要想配齐所有的家具就必定得雇人打造,所以找父亲打造家具的活计还真不少。他把挣得的钱全给了妈妈,让她给我买药物和营养品了。母亲则除了帮人做针线,又到里弄生产组去讨来了拆纱的工作,为挣多一点钱,能让我吃上牛奶,增加营养,好尽早恢复。
1968年底,我被分配进了上海第一石油机械厂,当上了学徒工。在我拿着第一个月的津贴交给他们时,母亲流泪了。18块钱的津贴,她数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里弄街道,“人人过关,个个洗澡”。已经退了休的父亲迫不得已还要为自己早年莫名其妙被“脱离组织”的谬事一遍遍写检查,而母亲则为她曾是“富农”的女儿、“地主乡绅”的媳妇,被街道“造反派”勒令“劳动改造”。勒令她每天早晚两次打扫弄堂的走道!
于是晨风里、暮色中,一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婆(此时母亲已60岁了)抡着比她个子高的大竹扫帚,艰难地挪着步子,一点一点地向后退着,一点一点地扫着肮脏的人类垃圾!一个深秋的傍晚,天空飘着濛濛细雨,雨中,母亲抡着扫把艰难地挪着步子,一双小脚浸泡在路边的积水里……目睹这让人心头流血的一幕,我忍不住满腔愤怒,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扫帚扔在一边,并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那些毫无人性的“畜生”。没料到,母亲猛地抽了我一个耳光;看到我仍然不肯甘休的样子,她竟然哀求起我来。望着她那张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脸和饱含泪水的双眼,我的头发涨、脸发烫、手脚冰凉、心在流血,扭头奔回家里。我想哭,但无泪;我想喊,但发不出声。我一头扑倒在床上,默然地流泪了。
大姐姚根娣和许多敢仗义执言的人,找到街道“革命委员会”为母亲和父亲说情,竟然得到“研究研究,请示一下”的答复。三个月后,母亲解除了“劳动改造”,不久,父亲也终于通过了“检查”。我知道,这和他们平时处事待人平和善良是分不开的,里弄里许多人都在为他们向街道说情,街道方面也只能顺水推舟了。
更何况父亲也曾为革委会副主任家打过好几件家具呢。父母亲得到了“解放”,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他们似乎又能和平常人一样了。但我知道,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已经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们衰老了许多。母亲的两鬓斑白了,父亲的腰背也弯了下来,他们很少再有爽朗的笑声了。
养儿方知父母恩 仁慈博爱是楷模
1976年10月,“文革”灾难终于结束,1978年我考进了大学。这在我们弄堂里算是头一遭。高中毕业十多年后,还能跨进大学的校门!看着大红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乐了,当天晚上还开戒喝了点酒。母亲笑了,母亲也急了,31岁的我刚刚进大学,照老规矩大学生是不能结婚的,等我毕业后再结婚,那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抱孙子啊?
1980年,高教部发文允许高龄大学生结婚。我终于也成家了。大礼前夕,妈妈悄悄地走到已经布置停当的新房里,把一个小布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整整1200元钱!天哪,进厂三年满师以后我每月才30多元钱工资,还要吃饭、穿衣、零花,这些钱她是怎么攒起来的!望着她那充满笑意的脸,我强忍着泪水,叫了声:“妈!”她只是轻声说了句:“小点声,你爸不知道。”婚后第三天,我陪新娘回娘家。从她娘家回来已经很晚了,打开家门,看见父亲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个小红纸袋。他见我们进门连忙站起身,走到我新婚妻子身边,把红纸袋交给她。一声不响地走回自己房间去了。我们进了房间打开红纸袋,里面是崭新的10元纸币,一数整整50张。妻望着我,我望着她,久久说不出话来。
婚后数年,我也成为父亲了,孩子诞生在仲秋的凌晨,故而父亲为其取名“晟儿”。此后,我们也为自己的孩子操劳忙碌,为孩子的病痛担忧,为孩子的学习操心,为孩子的成长高兴,为孩子的成就自豪。每当身为父母的我们为孩子做了些什么,或者担心些什么时,总情不自禁会想起我们的父母当年为我们操心劳累的情景。
“养儿方知报娘恩”,当我们开始理解,开始醒悟,想要报答他们时,他们却都已老了,很多东西已经享受不了了。1988年,我借调到上海对外服务公司并应聘进入了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餐桌上鸡鸭鱼肉不算稀罕了,但他们牙松齿老,嚼不动了。戏院里又开始演传统大戏了,我托人好不容易买了票,可他们走不动,去不了了,偶尔去附近的闸北区工人俱乐部看上一场电影,小半里路,要走上近半个小时。回来就说:“不看了,不看了!”1989年,我去日本工作研修,回国时在免税商店买了部23吋的彩电,想让他们在家里看戏看电影,可他们看了一会儿就让关上,说是:“让孩子早点休息!”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因为日本公司工作繁忙,很少照顾到家里,就和爸爸商量,想雇个保姆照顾母亲,可她坚决不要,父亲也不同意。我猜想,在母亲,恐怕是出于节约的考虑;在父亲,恐怕则是想自己亲手照料一下陪伴自己走过四十多年风雨历程的老伴。直至母亲弥留阶段,父亲几乎一直守在她的身边。我们多想守住她、挽留住她的生命,让她多享几年晚年的幸福啊,但她已经心疲力竭了,三年“天灾人祸”的大饥荒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病患,十年“文化革命”在她心灵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如今已是身心俱乏,病入膏肓,回天乏力。
1991年10月25日,母亲走完了她艰辛漫长的一生,离我们而去。享年82岁。
但我总觉得她没走远,她还在关注着我们。
她那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她的善良、仁慈、博爱,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将无时无刻惕励着我,这是我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哲人懿德满邻里 双亲天国同安息
母亲走后,父亲一直忧郁寡欢,日常话语减少了许多,时常胃痛,影响到饮食,饭量减了,酒也不喝了,甚至连最喜好的烟也停了。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他却冲我们一笑,查什么,不就是多年的老胃寒吗?岂料,他已是胃癌晚期了。当我们发觉他越来越瘦,不太对劲,逼着他去了区中心医院检查时才发现是不治之症,我和弟弟决定马上给他办理住院治疗。起初他死活不同意,但禁不住我和弟弟又哄、又骗、又逼,他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在家等待住院通知的那几天里,他还坚持着每天下午去小晟晟的学校接他回家。四天后,1992年7月31日,在他坐上计程车去医院之前还叮咛我们,要照顾好小晟晟!
父亲住院,医生随即就发出病危通知,并明确告知这胃癌晚期是不治之症,动不动手术几乎都一样。我和弟弟去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要手术治疗,他却是淡淡一笑:“八十多岁了,还开什么劳什子刀啊,再说,我也该去你妈妈那里陪她了。这辈子我亏欠她太多了!”他还极其认真地关照我们,他死后要和妈妈埋葬在一起,坚决不要把遗骨葬回故乡。从他毫无商量的口气里,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对自己家乡人的一种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当时,无法捉摸得透。直至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在他写的向造反派的交代材料里,有一段他被组织遗忘的隐密。原来当时县大队的指导员(他的一个远亲)一直阻挠有关人员设法与我父亲取得联系,后来此人兼了大队长的职务,就更不愿意让父亲归队了。
父亲要我们在苏州选一块墓地,因为那里离大姐姚根娣的墓地近些(大姐姚根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扭秧歌的走资派”,受迫害于1974年不幸逝世。遗骨葬于苏州吴山头)。我们雇了看护工日夜分班照料他的起居饮食。白日里我和弟弟上班工作,晚上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他的床前,和他唠唠家长里短。有一次我问他:“爸,你抛弃了县大队长的职务和妈妈来到上海,过了大半辈子清贫的生活,后悔吗?你的战友、下级,可是做到某某市公安局长,并差一点升到市长啊。”他用力地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后悔的,生活本身贵在平淡,别看老陆当了几年公安局长,但最后不是跳楼自杀了吗?我要是没有‘被组织脱离’,说不定也能弄个一官半职,但结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半晌,他又把脸朝向我,语重心长地说:“大鸭子(我的小名,因诞生时鸭子的叫声惊醒我而得名)你千万别走仕途!答应我!答应我!”望着他瘦削而坚毅的脸庞,我含泪点了点头。他才放心地闭眼睡着了…….
1992年8月25日在送走妈妈整整十个月之后,我们又送走了为我们操劳大半辈子的爸爸。
他和妈妈一样勤劳、诚恳、老实本分、善良仁慈。我们从1954年搬进民立路190号,直到父母亲相继去世,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父母亲竟然从来没有和里弄里任何一个人吵过一次嘴,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他们的身心备受摧残的年月里!我在他的悼词里说道:“父亲的善良、仁厚是有口皆碑的,80年来他从没和任何人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父亲是勤劳慈爱的。居住在民立路200弄的居民几乎每家都有我父亲给他们留下的手艺活儿。小到门窗、桌椅板凳,大到衣柜、阁楼晒台。父亲用他长满老茧的双手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忆,他也因此活在了我们心中。”记得我在念这几句话时,大厅里近300人几乎全哭了。
爸爸,亲爱的爸爸,你那颗勤劳、善良的心将永远跳动在我们的身体里,直到永远。
愿你在天国和母亲一起安息吧!(全文完)◇#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