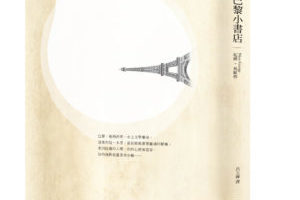苏东坡的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这座人潮似海的巍巍大城,真能藏住所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还是就像笼罩城顶的雾霾一样,人们只能避它防它,束手无策?
该做好人还是坏人?雾霾深罩的北京城,上演着不见天的罪与罚。
──《王城如海》
幽咽如诉的胡琴曲〈二泉映月〉响起,表情狂乱砸家什的余松坡逐渐平静,缓慢步入卧室安睡。北京做为中国的首善之都,既是历史古城,也是政经巨邑,千千万万的乡下青年进京后,委身于逼仄的陋室内,成为蚁族,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只为在首都中占得一席之地,力图他日的功成名就。余松坡也曾是千万人中的一员,为求前程费尽心机,如今做为海外归国成功人士,原本是票房毒药的舞台剧导演,此次的《城市启示录》却空前叫座,但也因为演员对“蚁族”青年流露出鄙夷的神色,引来舆论的挞伐。锋头正健的余松坡,因遇见在天桥贩卖新鲜空气的痴傻流浪汉后,勾起昔日乡下往事,引得他梦游症又犯了,只有〈二泉映月〉能安抚噩梦,这首曲子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罗冬雨身为余松坡因霾害为气喘所苦的儿子的保母,她让同是乡下进京的男友与弟弟绕着余松坡的生活打转,他们的朋友因为雾霾视线不佳车祸丧命,女友为当舞台剧演员宁愿脱衣接受潜规则。然而北京正是靠着这群乡下人,维持京城的气派,他们的苦处被这座妆点得繁华明艳的城市隐没。一个偶然,压抑的青年抓住了机会,准备揭开华丽面具下的黑历史。“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座人潮似海的巍巍大城,真能藏住所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还是就像笼罩城顶的雾霾一样,人们只能避它防它,束手无策?
继《耶路撒冷》后,最受期待的青年小说家徐则臣,将视角从“走向世界”的京漂族移到北京海归派。透过主角导演的舞台剧探讨北京城的本质,巧妙地将城市个性、雾霾联结谋求功名的真实人性。全书故事仅短短数日,却罗织了层层相叠的往日云烟,不堪的秘密,不安的灵魂,上演了一则罪与罚的现世寓言。
【作者简介】
徐则臣
一九七八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居北京。
著有《午夜之门》、《夜火车》、《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到世界去》等。
【主文】
合租客甲 从前有个人,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想栽出一棵参天大树。
合租客乙 结果呢?
合租客甲 死了。
合租客丙 该。
合租客甲 他又栽,死了。他还栽,继续死。他继续栽,还死。再栽,再死。
合租客乙 上帝就没感动一下?
合租客丙 你看,想到上帝了。为什么一定得想到上帝呢?
合租客甲 上帝没感动,上帝看烦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种点草呢?
合租客乙 跑森林里种草?头脑被上帝踢了?
合租客丙 他种了没?
合租客甲 他弯下腰,贴着地面种出了草原。
——《城市启示录》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坡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先是脖颈处薄薄地一凛,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余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雾霾里。
能见度一百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
余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词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五十?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一串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儿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
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PM二点五爆表,预约的访谈照常?他回:当然。只能照常。霾了不是一天两天,一爆表就不干活儿,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
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
那人先砸碎的是厨房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地遥远,余松坡没当回事,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他撅起下巴,让吉列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
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余松坡正在比画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崭崭地留在那里,茬口切割一般的整齐。
罗冬雨打了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她醒来是因为余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
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余果还是空荡荡地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她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了。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待会儿就收拾。”她说的是地上的碎玻璃。
“保留现场”,余松坡说话的时候能感到喉结在手底下艰难地蠕动,“出现了恐怖分子。”他想把这个清早弄得轻松一点。他很清楚,这幽默不是为了宽慰罗冬雨,而是缓解自己的焦虑。
惹事了。但他搞不清惹下的事对正在演的戏和自己的艺术生涯有多大影响。他确信自己是个优秀的戏剧导演,他也确信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戏剧演员,他的表情已经跟刚才的幽默貌合神离,所以他如实地补了一句,“有人砸了咱们的窗户,我马上报警。”
他把纸巾从伤口上拿下来,血还在往外渗。
“我去拿创可贴。”
罗冬雨转身去找药箱。睡袍摆动,余松坡看见她光裸圆润的脚后跟。他把厨房的百叶窗也拉下,雾霾锁城,两个好看的脚后跟是多么奢侈。
从房间里出来,罗冬雨已经换上了家居服。她在穿衣镜前给余松坡贴创可贴。先用酒精棉球消毒,余松坡痛得暗暗抽冷气。他仰着脖子,目光向下只能看见罗冬雨头发缝中白净的头皮。沙宣洗发水的味道。
不管他和祁好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罗冬雨都坚持用沙宣,她自己买。散发着好闻味道的黑发中间那道笔直的头缝,让余松坡发现了别样的性感。他突然想抱一抱这个在他们家做了四年保姆的女孩子,或者被她抱一抱。跟欲望无关,是脆弱。
好女人总能让男人感觉自己是个孩子。他有点觉得自己不容易了,媒体和舆论对他的新戏似乎已经不是感不感冒的问题了。
“该嫁了,小罗。”他说。
“等一下。”罗冬雨说。她是让他别说话,喉结上下蹿动影响她操作。
余果在咳嗽。她把创可贴的两端按了一下,去冰箱里取出昨天调制的萝卜蜂蜜水。霍大夫说,别没事就给孩子吃药。
两周前她和祁好带余果去看传说中的中医霍大夫。余果咳嗽一个半月,北京能跑的医院都跑遍了,能吃的药也都吃遍了,还是咳。祁好朋友的朋友介绍了霍大夫。
霍大夫很神,他的神不在只有三十二岁就成了传说,也不在他七岁成了盲人,也不在他极少开常规的药方,只以食疗和推拿手法祛病;他的神在,听完罗冬雨详尽地罗列了余果一个半月来的病情与反复,以及余果的日常细节之后,慢悠悠地转向只能偶尔插上几句话的祁好,慢悠悠地说:“你这当妈的得上点心啊。”
他一个年纪轻轻的瞎子怎么就断定我不称职?回家的车上祁好一路都在流眼泪。
他们在霍大夫跟前没有透露出半点私密的信息,三个人自始至终都没给对方任何称谓。霍大夫把过脉,说当如此如此。开出的唯一方子是,咳嗽时喝萝卜蜂蜜水。管用。这几天余果几乎不咳了,但从昨天下午开始,雾霾卷土重来。玻璃一碎,余果在睡梦中也有了反应。
照祁好出门前拟定的食谱,罗冬雨做好早餐。跟一个多月来的每一天一样,余松坡在早饭桌上都要解决很多问题,家里的,剧组的,媒体的,好像是余果咳嗽以后他才开始忙的。今天他没法送孩子去幼儿园了。
当然他也没送过几回,余果现在中班,一年半里送接都算上,他进幼儿园也不超过十次。祁好稍微要多一些,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这事也让保姆来办,有点不合适。在饭桌上余松坡拨打一一○报了案,砸了厨房又砸卫生间,肯定有预谋,姑息只能养奸。
作为在美国待了二十年的“海归”,这点法律意识还是有的。有话法庭上说,谁都别在背后耍小动作;砸玻璃,简直可笑到下流,不能忍。
不过他一会儿就出门,录口供只能罗冬雨代劳了。还有,警察来过之后,赶紧给物业打电话报修,冷风受得了,雾霾受不了。看过那个新闻吗?科学家做了实验,小白鼠吸了一礼拜的霾,红润润的小肺都变黑了。黑了就黑了,回不去了。不可逆。
罗冬雨记下了。饭后,余松坡在玄关前换鞋时问:
“你祁姊啥时候回来?”
罗冬雨摇摇头,机票不是她订的。◇(未完,待续)
——节录自《王城如海》/ 九歌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