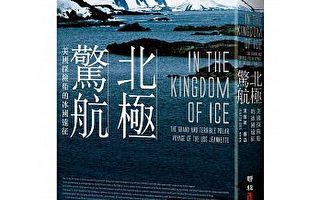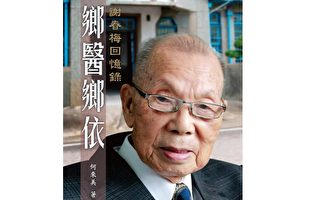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续前文)
*3
薇安对战争并不陌生。她知道的不是隆隆的枪炮、烟硝的战火和鲜血,而是战争的后遗症。虽然在承平时期出生,她最早的记忆却攸关战事。
她记得一边跟爸爸说再见,一边看着妈妈啜泣。她记得饿肚子,而且总觉得好冷。但最重要的是,她记得爸爸返家后走路一跛一跛、唉声叹气、沉默不语,变了一个人。
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酗酒,什么话都埋在心里,对家人不理不睬。之后,她记得房门劈啪关上、争执声轰然四起,而后缓缓转为难堪的沉默、她爸妈搬进不同的卧室。
离家参战的爸爸和战后返家的爸爸是两个不同的人。她试着赢得他的爱;更重要的是,她试着持续爱他,但最终,两者皆是不可能的任务。
自从他把她送到卡利弗,这些年来,她营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每年寄圣诞卡和生日卡给他,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卡片。他们父女很少交谈,还有什么好说的?
伊莎贝尔似乎始终放不下,但薇安不一样,她了解——也接受——妈妈一过世,他们的家就无可挽回,支离破碎。他是个再怎么样都不愿为孩子承担父职的男人。
“我知道你多害怕战争。”
安托万说。
“马其诺防线挺得住,”她试图让自己听起来令人信服:“你圣诞节之前就会回家。”
马其诺防线是道长达数百英里的水泥墙,一次大战后,法国沿着德、法边境筑起这道防线,沿墙架设武器与障碍物,防止德国入侵。德军不可能突破这道防线。
安托万揽她入怀。茉莉花香令人心醉,顷刻间,她确知从今以后,她一闻到茉莉花香就会想起这次道别。
“我爱你,安托万·莫里亚克,我等你回家,回到我身边。”
日后,她不记得他们走进屋里,爬上楼梯,躺到床上,脱下彼此的衣服。她只记得自己赤裸裸地窝在他的怀里,躺在他的身下,他一反往常,狂热、急切……他的吻带着探索的意味,双手似乎想要撕裂她,即使是紧紧搂住。
“你比自己以为的坚强,小薇。”
完事后,他们静静躺在彼此的臂弯里,他对她说。
“我不是。”
她悄悄说,声音轻到他听不见。
***
隔天早上,薇安想整天把安托万留在床上,甚至劝他收拾行囊,一家人像小偷那样摸黑逃跑。
但他们能逃到哪里?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欧洲。
等她吃完早餐,洗好碗盘,她的头已经隐隐抽痛。
“妈,你好像不开心。”
苏菲说。
“夏天天气这么好,而且我们正要去好朋友家里坐坐,我怎么会不开心?”
薇安笑笑说,但是笑容有点牵强。
她走出家门,站到前院的一棵苹果树下,这才意识到自己没穿鞋。
“妈!”
苏菲不耐烦地叫了她一声。
“我来啰。”
她边说边跟着苏菲穿过前院,走过以前用来养鸽、现在用来摆放园艺工具的木棚和空荡的谷仓。苏菲推开闸门,跑进邻家精心修整的院子,冲向一栋装了蓝色百叶窗的小石屋。
苏菲敲敲大门,无人回应;她直接推门进去。
“苏菲!”
薇安厉声说,但她的斥责有如耳边风。在好友家不必拘礼,而蕾秋·德·尚普兰和薇安是十五年的知交。爸爸忝不知耻把她们两姐妹丢到乡园后的一个月,薇安就结识蕾秋。
两人自此就是一对好搭档。薇安瘦小、苍白、紧张兮兮,蕾秋个头跟男孩一样高大,眉毛的生长速度比谣言的散布更加惊人,声音跟雾号一样粗嘎。她们都打不进小圈圈,直到遇见彼此。
她们很快就形影不离,中学毕业后依然是好友,直至今日。她们一起上大学,两人都成为小学老师,甚至在同一时间怀了孕。如今她们在当地的小学任教,在相邻的教室里教书。
蕾秋从敞开的门口露面,怀里抱着她刚出生的小儿子艾瑞尔。
她们互看一眼,眼神中道尽两人担心害怕的一切。
薇安跟着她朋友走进明亮、整洁雅致的小房间,一张粗拙的木头长桌摆着一个插满野花的花瓶,两侧各有一张椅子,椅子式样并不搭调。
角落有个真皮手提箱,箱上搁着蕾秋的先生马克喜爱的羊毛毡帽。蕾秋走进厨房,端出摆满可丽露蛋糕的小陶盘,两人走向屋外。
小小的后院里,玫瑰花沿着自家的树篱生长,一张桌子和四张椅子散置在砖石平台上,几盏古旧的煤油灯悬挂在栗树的树枝上。
薇安拿起可丽露蛋糕咬了一口,细细品尝浓郁的香草奶油内馅和香脆微焦外皮。她坐下。
蕾秋在她对面坐下,怀里的小宝宝好梦方酣。静默在两人间延展,满载彼此的忧虑和不安。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机会认识他爸爸。”
蕾秋低头看着小宝宝说。
“战争会改变他们。”
薇安想起往事,说了一句。她爸爸曾参与索姆河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超过七十五万人丧命,种种关于德军暴行的传言也随少数幸存的法军传回乡里。
蕾秋把小宝宝抱到肩上,稳稳地轻拍他的背。
“马克不太会换尿布。小艾瑞尔喜欢睡在我们的床上,我猜现在不是问题了。”
薇安感觉自己浮现笑意。这个玩笑不算什么,但多少有点帮助。
“安托万的鼾声很烦人,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
“而且我们可以吃水波蛋当晚餐。”
“脏衣服少了一半,”她说,但声音逐渐哽咽:“蕾秋,我不够坚强,应付不来。”
“你当然应付得来,我们会一起熬过来。”
“我认识安托万之前……”
蕾秋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我知道、我知道,你瘦得跟树枝一样,一紧张就结结巴巴,对每样东西都过敏。我都知道,我也在,不是吗?但这些都过去了。你得坚强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蕾秋的笑容渐渐隐去。
“我知道我人高马大——轮廓优美,他们跟我推销胸衣和丝袜时总是这么说——但是,小薇,这件事让我濒临崩溃,有时我也需要你让我靠一靠。但我当然不会整个人靠在你身上。”
“所以我们两人不能同时崩溃?”
“没错!”蕾秋说:“就这么说定啰。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开瓶干邑白兰地或琴酒?”
“现在是早上十点。”
“没错,你说的对极了。那就来杯法式75鸡尾酒吧。”
星期二早上薇安醒来时,日光自窗外流泄而入,粗拙的原木蒙上一层闪亮的光影。
安托万坐在窗边的椅子上,那张胡桃木的摇椅是薇安第二次怀孕时、安托万亲手所制。多年来,空空荡荡的摇椅似乎是个嘲讽。日后想起,她把那段日子称为“流产岁月”。大地丰饶富足,她的心田却一片荒芜。
她四年内三度流产,失去三个气若游丝、心跳微弱、双手泛蓝的胎儿。而后奇迹似的,一个小宝宝活了下来:苏菲。那张摇椅的木头纹理间收纳着几个瘦小、哀伤的鬼魅,但也承载着美好的回忆。
“说不定你应该把苏菲带到巴黎,”
她坐起时,他开口说:“你爸爸会照顾你们。”
“我爸爸已经表明他不想跟女儿住,我怎能指望他欣然接纳我们。”
薇安把菱格被毯推到一旁,起身下床,光脚踏上陈旧的地毯。
“你们没问题吧?”
“苏菲和我会没事的,反正你很快就会回来。马其诺防线挺得住,况且,天晓得德国人才不是我们的对手呢!”
“可惜他们的武器比我们精良。我把银行存款全都领了出来,床垫下藏了六万五千法郎,薇安,请你善加花用。你还有教书的薪水,应该可以让你们支撑好一阵子。”
她一阵惶恐,心中狂跳。她对他们的财务状况所知甚少,向来是安托万管账。他慢慢站起来,把她搂到怀里。她好想把此刻的安全感装入瓶中,日后当她的心因孤寂恐惧而干涸时,才能啜饮一口。
记住这一刻,她心想。他的乱发捕捉了日光,褐色的双眼盈满了情意,一小时前,他龟裂的双唇在黑暗中亲吻着她。
他们身后的窗户敞开,她听到窗外的声响,一匹马儿拖着四轮推车沿着小路缓缓前进,马蹄踢踢踏踏,车轮啪哒啪哒,声声平缓。
那八成是奎利安先生载着鲜花前往市场。如果她在院子里,他会停下来送她一朵花,称赞她人比花娇,她也会微微一笑,说声谢谢,请他喝杯饮料。
薇安不情不愿地抽身。她走向木制梳妆台,把蓝色陶罐里的温水倒进浅盆,洗了脸。在那个充当更衣间的凹室,她隐匿在金黄和乳白的亚麻布帘后方,穿上胸衣,套上蕾丝花边的底裤和袜带,沿着大腿顺顺丝袜,系在袜带上,然后穿上一件方领束腰洋装。
等她拉上布帘、转过身来,安托万已经不在房里。
她拿起皮包,走到走廊另一头的苏菲卧房。女儿的房间跟他们的一样狭小,天花板斜向一侧,地上铺着宽长的木板,还有一扇俯瞰果园的窗户。房里一张铸铁床铺,床边的小桌上搁着一盏二手台灯。漆成蓝色的大衣橱占据了剩余的空间,苏菲的绘画妆点了墙面。
薇安拉开百叶窗,让阳光流泄到房里。
夏夜炎热,苏菲跟往常一样半夜就把被单踢到床下,她那只名叫“贝贝”的粉红绒毛玩具熊贴着她的脸颊。
薇安拾起玩具熊,低头凝视它那微微褪色、备受宠爱的脸庞。苏菲去年迷上了新玩具,贝贝受到冷落,被丢置在窗边的架子上。
这会儿贝贝再度受宠。
薇安倾身亲吻女儿的小脸。
苏菲翻身,眨眨眼睛,醒了过来。
“妈,我不要让爸爸走。”
她轻声说。伸手拿玩具熊,几乎从薇安的手中抢走贝贝。
“我了解,”薇安叹气:“我了解。”
薇安走向大衣橱,从橱里挑出那件苏菲最喜欢的水手洋装。
“我可以戴爸爸帮我编的雏菊花冠吗?”
所谓的“花冠”皱皱地搁在床边小桌上,小小的花朵已枯萎。薇安小心拿起,戴在苏菲的头上。
薇安以为自己应付得不错,直到她走进客厅,看到安托万。
“爸?”苏菲摸摸枯萎的雏菊花冠,犹豫地说:“别走。”
安托万蹲下来,抱住苏菲。
“为了确保你和妈妈的安全,我必须上战场,但我很快就会回来。”
薇安听出他话语中的哽咽。
苏菲抽身,雏菊花冠斜斜地从头上滑落。
“你保证你会很快回来?”
安托万掠过女儿神情急切的脸庞,迎上薇安忧心重重的凝视。
“我保证。”他终于说。
苏菲点点头。
他们一家三口沉默地走出家门,手牵着手走上山丘,朝灰黑的谷仓前进。及膝的金黄野草覆满浑圆的山丘,一丛丛跟干草车一样巨大的丁香花沿着地产的边界蔓生。
三个小小的白色十字架立在山丘上,世间只剩下这三个十字架缅怀薇安失去的胎儿。今天她不许自己看十字架。心情已经够沉重了,她不能再想那些往事,添增心中的负担。
那部绿色的雷诺老爷车停放在谷仓里。他们都坐进车里后,安托万发动引擎,倒车驶出谷仓,辗过渐渐枯黄的草,开到小路上。
薇安凝视灰尘仆仆的小窗,看着窗外青绿的河谷,铺了红砖瓦的屋顶、牧草田园、葡萄园、细长高耸的林木,种种熟悉的影像迷濛地闪过。
车子开抵图尔附近的火车站。唉,太快了。
月台上挤满提着皮箱的年轻男子、与他们吻别的女人、哭哭啼啼的孩童。
一个世代的男人又将远赴战场。
别多想,薇安跟自己说。不要回想上次男人们返家时走路一跛一跛,颜面灼伤,缺手缺脚……
安托万买车票,带着他们上车时,薇安紧紧抓住丈夫的手。三等车厢非常闷热,几乎令人窒息,乘客们有如沼地芦苇般挤成一列,她直挺挺地坐着,皮包搁在膝上,依然抓着丈夫的手。
火车到站,十几个人下车,薇安、苏菲和安托万跟着其他人沿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前进,走入一个迷人的村庄,这个小村跟都兰地区的其他村庄一样典雅幽静,繁花怒放,处处可见崩坍的古老城墙。
战争怎么可能要来?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怎么可能集结士兵、把他们送往战场?
安托万拉拉她的手,示意她再往前走。她什么时候停下了脚步?
前方有一排最近架设、固定在石墙上的铁制闸门,门后是一排排临时房舍。
铁门一开,一名骑马的士兵出来欢迎来报到的人们,他的皮制马鞍随着马儿的步伐嘎吱作响,脸上都是灰尘,热得满脸通红。他拉扯缰绳,马儿停步,一边甩甩头,一边嘶嘶喷气。
一架飞机在上空嗡嗡飞过。
“各位,”士兵说:“请把你们的文件带到铁门旁的中尉那里。来,赶快行动。”
安托万亲吻薇安,这一吻是如此柔情,让薇安好想哭。
“我爱你。”
他贴着她的唇说。
“我也爱你。”
她说,但此时此刻,这几个意义深重的字眼感觉却无足轻重。与战争抗衡,爱情算什么?
“我也是,爸爸,我也爱你!”
苏菲哭着说,整个人投入他的怀抱。他们一家三口最后一次紧紧拥抱,直到安托万抽身。
“再见。”他说。
薇安无法道别。她看着他走开,见他渐渐融入一群谈笑的年轻人中,再也难辨身影。
巨大的铁门“啪”地关上,钢铁在炽热、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发出铿铿锵锵的回音,薇安和苏菲站在街上,形影孤单。◇(节录完)
【作者简介】
克莉丝汀·汉娜(Kristin Hannah)
《纽约时报》畅销作家,已出版二十二本小说。她曾是律师,而后转行写作。育有一子,与先生定居美国西北部与夏威夷。
——节录自《夜莺》/ 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
(点阅【夜莺】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