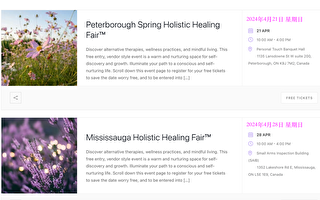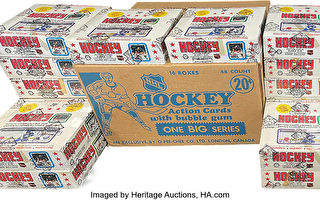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纪元2018年02月07日讯】这两天,朋友圈里,一片雪景,包括我地处长江南岸的湖北老家。
自离开家乡,忽忽二十余年,所居之地,珠三角,长三角,闽南,都是不见落雪的地方,每逢新年,不过敷衍一下应个景罢了。潜意识里,总觉得没有雪花伴舞的新年是不正式的。
在广东人和闽南人眼里,上海理所当然属于北方。可我在上海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场像模像样的雪,偶尔稀稀拉拉落几片,或孤单影只,或三五结伴,在沉沉暗空中孤独地飞舞,落到地上,瞬间融化。
我喜欢雪,因为它的明朗,也因为它的安静。雪不像雨那般点滴凄清,愁损离人,更不会借着风的阵势,斜吹横打,敲着窗棂,打着芭蕉。雪安静,内敛,悄悄的,于天地沉睡间,铺满整个的大地。
无雪的冬天让人烦躁不安。四季也变得混沌模糊。
记忆中有一个片段:正月,在外婆家拜年,吃过早饭开始下雪,没有风,雪落的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待到午后,天地间已经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
雪就像安定剂。外婆家的老黄猫平时在家呆不住,那天,也不到处乱跑了,头尾相接,蜷缩成一团,偎在猫窝里酣睡,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长辈们围坐在一起烤火聊天。那时还不流行火炉,是那种类似野外篝火的火坑,火塘三边用数寸厚的麻条石或是木头规整地圈着。火坑的优点是烤火得劲;缺点是灰尘大,终日饱受烟熏之苦。偶尔,燃烧的木柴爆炸,溅起的火花难免会落到头上和身上。
我们表兄妹则聚在厢房里打扑克牌,桌子底下放着木托架的炭盆火。突然,不远处一声枪响,四野一个重重的惊悚,屋檐下的冰凌子震掉了好几个,哗啦啦一阵碎响。有人在狩猎。下雪天是狩猎的好天气,动物经过的地方,会留下清晰的脚迹。
那天,好像是有人打到了一只獐子,大人们都说谁要发大财了。外公告诉我,雄性獐子体内的麝香是名贵药材,很值钱。
带烟囱的大火炉,八十年代末期才慢慢流行开来,起初比较简陋,长方形,炉身炉面都是铁皮,长长的烟囱穿墙而过,笔直伸向屋外。到了九十年代,随着铸炉技艺越来越精湛,款式也越来越新颖,圆形炉面的材质,分铝合金和陶瓷等好几种。
窗外,北风呼号,雪花飞舞。屋内,炉火正旺,壶水正沸。来了客人或是邻居,一进门,先拍打身上的雪花,大家自觉把椅子挪一挪。落座。给客人沏上一杯绿茶。
热茶。瓜子。以八卦闲扯居多的闲散话题。咝咝作响的水壶。
偶尔,炉膛里砰砰几声爆响———那是没干透的枫香树在作怪。以我对木柴有限的认知,我只知道栎树少烟且易燃,火舌高。生火时,我的经验是在炉桥上搁几张废纸,然后在上面蓬松架一些枯枝,枯枝上面放几块易燃的干柴。点燃纸张,关上炉门,火苗自下而上,慢慢燃起。待炉膛里有了滚烫的带火星的柴灰,往里面埋几个红薯或是土豆。有着焦黄锅巴的烤土豆蘸辣椒酱吃,实在是人间少有的美味。
记忆里很多个寒假,我都是在炉火旁安静地翻杂志,读小说。大哥订的有《大众电影》,杂志上明星们的穿着打扮,引导着我对外界对时尚的领悟和感知。那时,母亲四十多岁,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常常利用雪天做针线活。我和母亲对坐着,中间隔着温暖的火炉。滚烫的炉面上,要么坐着一壶水,要么炖着一锅汤,咕嘟咕嘟,直冒热气。偶尔,炉面上搁着几颗花生几粒板栗几个核桃。我性格随母亲多些,安静,不爱东家西家地串门。
如今,在乡间,在闹市,已经很难见到烧柴火的火炉了,人们都把它当成过时的风尚和陈迹,取而代之的是暖气和各种地热板。可我总觉得,比之火炉,干净的暖气似乎少了性格和活力,也缺少光。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猛烈燃烧中,给人的不仅仅是温暖,还给人一种启示与希望的闪光。
所幸我的亲人还保存着这一取暖习俗。姐姐家四房两厅,专门腾出一间屋子,用来放置圆盘铝合金的火炉。前天,她电话里跟我说买了一车木柴,够烧一个冬天了。
往事一去不复返。和我一样,浪迹到各地的五峰同乡,真不知有多少,在我们对故土的共同记忆里,冬日的雪景,雪天的火炉,炉膛里的土豆,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抹去的乡土情结。
责任编辑: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