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一年:我的快乐调查报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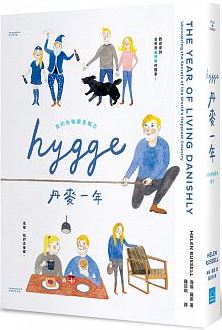
《HYGGE! 丹麦一年》( 地平线文化提供)
一切其实开始得很简单。休了几天假,假日即将结束时,我和老公的心情都很低落,十分不愿回去面对那些例行公事。伦敦降下了一场灰濛濛的细雨,使整座城市看起来脏兮兮的,让人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正如当时的我。
“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些而已……”
每天搭地铁上班时,我的脑海中总会闪过这么一句讪笑的话语,挑衅着自己。十二个小时后,走过随处可见鸡骨头的街道,回到家里,晚上还得继续工作数小时,或是为了工作出席某个活动。
我是一名记者,替一家表面看来十分光鲜亮丽的杂志社工作。但,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因为我每天所撰写的文章都在告诉读者如何“兼顾一切”: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获得成功、身心健全、向酒精说“不”等等。可是,我自己的学贷都还没还清、需要依赖大量咖啡因才能撑过一天的工作,睡前还得靠葡萄酒助眠。
每个星期天晚上,想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胸口就会一阵闷。每天早上,我都会按下好几次闹钟的贪睡按钮才爬得起来。这份工作是我努力很久才得到的,而我在这个产业也奋斗了十年以上。可是,达到目标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变得比较快乐,只是更加忙碌罢了。我想要达成的目标一直在变,达成一个目标,又会觉得“少了”别样东西。我以为我想要、需要的东西,或我“应该”做的事情,总是永无止尽。而我,总是疲惫不堪,人生变得凌乱、破碎。我总想一次做很多事,但总觉得自己落后他人。
那时,我三十三岁。耶稣也活到这个岁数,但祂在这把年纪时,照理说已经做出在水上行走、治愈痳疯病、让死者复活的事迹。祂也启发了好几个追随者、诅咒无花果树、在婚礼上神奇地变出大量的葡萄酒。我呢?我有一份工作、一间公寓、一个老公、一些好友,还有一条新养的狗。它是一只品种不明的混种犬,养它,是希望能带给我们一点乡村情调,平衡一下繁忙的都市生活。
所以,我的人生还算可以!?
好吧,我确实经常头痛、失眠,使用数个月的抗生素,扁桃腺炎仍未好转,而且每隔一个星期似乎就会感冒一次。但,这些都很正常,不是吗?
过去,都市生活带来的刺激曾让我成长茁壮,和优秀、活力充沛的团队一起共事,我也从不会无聊。我的社交行程满档,有一群支持我以及我所深爱的朋友,而且还住在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其中一座城市。然而,在英国首都全力冲刺十二年后,同时我所居住的北伦敦社区又在十二个月之内,发生第二起砍人事件,使我突然感到情绪极度低迷。
不仅如此。两年来,我天天注射荷尔蒙,被针筒又戳又捅的,每个月却总是换来一场心碎。我们一直努力要有孩子,但我就是没办法怀孕。每当办公室传卡片、募礼金,要送给那些喜获麟儿、请育婴假的同事时,我就好不开心。这么多年来,我每星期上三次门诊,目标就是一件婴儿装,却只能买来送人,实在是受够了。
后来,大家开始开我玩笑,叫我“加快脚步”、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不会希望“错失良机”。听到这些话,我总是一边露出大到下巴会痛的笑容,一边克制自己,不要朝向他们的脸上挥拳并大吼一声:“滚开!”我早已经认命,打算未来在工作时间穿插人工受孕的疗程,然后再用仅有的空闲时间做更多工作,以赶上进度。我不能停;我不能让自己有时间想太多,才能够继续维持我自以为想要与需要的那种生活。
我另一半的压力也很大,几乎每晚回到家后,都对这个世界感到愤怒不已。他会气呼呼地抱怨那一小时半的通勤时间所遇到的糟糕驾驶,或是尖峰时段的交通状况,接着倒在沙发、沉迷于电视节目的垃圾内容,直到该上床睡觉的时候。
我的老公是个表情严肃的金发男子,身上散发着物理老师的气质。他小时候曾参加星河巧克力棒(Milky Bar)广告童星的试镜,但小时候没电视可看的他,其实不太晓得星河巧克力棒是什么,只因为他的父母在《卫报》(Guardian)看见广告,觉得这产品听起来蛮健康就报名参加了。后来,是另一个仿佛得了白化症的小孩获得那个角色,但他仍记得那美好的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玩掌上型的任天堂游戏机,是另一个有望获得童星角色的小孩带来的。此外,他还尽情吃了很多巧克力——若在平常,这可是被禁止的。
他的父母禁止他接触许多这类新奇的玩具和食品,反倒常常让他听古典乐、带他上博物馆,或是到户外进行长距离的清新徒步之旅。因此,不难想像在他八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听到他说最喜欢的书是阿尔戈斯(Argos)的商品目录时,内心有多么失望;他可以开心地读好几个小时的商品目录,在这本厚重的“巨著”里,圈选各种想要的家电产品和乐高组合。
从这个童年喜好,就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出现在我的生命时,我已经差不多放弃希望了。那年是二○○八年,前一任男友在一场婚礼上把我甩了;上次约会的对象邀我到他家共进晚餐,却被我发现在看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忘记买任何吃的,后来他说要帮我订达美乐披萨,我跟他说不用麻烦了。
所以,当我认识未来的老公,他说要煮饭给我吃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那顿晚餐进行得出奇顺利。他很聪明、幽默,人也很好,而且还拿出了“白瓷焗烤杯”!我跟我妈讲到最后这一点时,她十分赞赏地说:
“有一组白瓷焗烤杯,表示他是个教养很好的年轻人,而且他还知道怎么使用,那就更不得了了!”
三年后,我嫁给了他。因为他会逗我笑、愿意吃我的实验料理、不会抱怨我把家里的甜食一扫而空。有时,他确实让人很受不了——每天都会弄丢钥匙、皮夹、手机,甚至全部一起弄丢;到哪儿都会迟到;上个厕所总是要上老半天,叫人气得要命(“你是在翻修厕所吗?”)。但我们的婚姻没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建构人生。此外,撇开医院的疗程以及轻度的忧郁、疲劳、感冒病毒、因为月初花太多钱导致月底出现的经济问题,我们依然相爱。
我想像我们两个几年之后会搬离伦敦,过着工作、拜访朋友、度假的生活,接着退休。我幻想自己的人生就像英国版的《女作家与谋杀案》(Murder She Wrote),过着和主角洁西卡‧佛莱契(Jessica Fletcher)一样的生活:撰写犯罪小说、解开除却血腥内容的犯罪事件、喝一杯好茶,最后来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幻想中的退休生活一定会超酷的。可是,当我和老公分享这个愿景时,他似乎不怎么热情。我得到的反应是:
“就这样?大家都这样啊!”
我试着再跟他解释一遍:
“你没听清楚洁西卡‧佛莱契的那个部分吗?”
他说,《女作家与谋杀案》是虚构的。我对他的言论嗤之以鼻,说他接下来该不会要告诉我,“独角兽可不是真的唷!”然后,他打断我的话,跟我说他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旅居海外。
“‘海外’?”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你是说,‘不在这个国家’?不在我们的海洋?”
“对。”他回答。
“噢。”
我这个人对冒险没什么兴趣,因为成长的过程和年轻时期就已经历了很多。现在,我比较向往安定。如果前方出现必须放胆冒险的事情,我倾向在自己的舒适圈内乖乖躲好。点菜时,我甚至不敢点平常不会吃的东西,但我老公似乎想要追求更多。这让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无法满足他。
疑虑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接着,在某个下雨的星期三晚上,他告诉我,有人要给他一份新工作,工作地点在另一个国家。◇(未完,待续)
——节录自《HYGGE! 丹麦一年》(前言)/地平线文化出版社
【作者简介】
海伦‧罗素(Helen Russell)
专为全球媒体和报刊撰稿。本书叙述作者和丈夫搬到丹麦后,找到幸福的北欧风格生活。本书出版后,激起人们对北欧丹麦生活的新概念“Hygge”的关注,并跻身英国、欧洲畅销书榜。
责任编辑:李昀
点阅【HYGGE! 丹麦一年】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