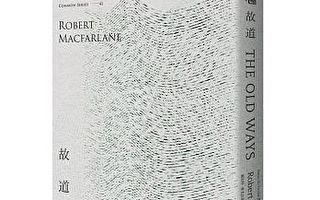过去几个月,我听过太多故事,恐怖的、悲伤的都有。尸袋拉链被拉开时我就站在旁边,我很清楚事实里大量掺杂着虚构的想像。可是那些故事、说故事的人,以及我们祝福过的遗骸,全部都出自“我方”的观点。听见“另一方”的事从个人嘴里说出,这还是头一遭。当然劫机者的遗骸会跟受害者的混杂在一起,只是我没想到罢了,因为我只顾着抚慰“我方”。
我问鲁迪他们怎么知道那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说他也不清楚,不过他猜可能跟那具遗体被发现的位置,还有它和飞机的局部构造非常接近有关。我想像这具遗体,或者残骸,被一群或许有朋友罹难的纽约消防员和警察、港务警局官员和建筑工人团团围住的画面。
“你也在场?”我问。
“是啊。”
“发现那是劫机者之一时,大伙儿做了什么呢?朝遗体吐口水或是用什么方式侮辱它吗?”不管传言是真是假,我想像它应该会引爆不小的激烈情绪。
想也没想,鲁迪摇了摇头。
“不⋯⋯没这回事。我们怀着敬意处理这具遗骸,和处理其他遗骸没两样。”
我很吃惊,完全没料到他会这么说。他的反应之率真、语气之诚恳,在在令人惊叹。我对他说,我非常吃惊,而且真心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在内,感到骄傲。
他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理所当然地回说:“我们只是互相提醒:喂,记住,这是某人的儿子,现在也还是某人的儿子。”
我知道我听见了神圣的话语。
将近凌晨两点,我结束和鲁迪的对话,走出活动拖车去透透气。还没有遗骸送进来,不过我还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留在墙上,以备不时之需。这种情况很正常。
如果整晚没事,停尸间的牧师可以在现场到处走动,为其他人打气。我决定前往人称第十消防站(Ten House)——或10─10,也就是第十帮浦车队、第十云梯车队——的消防大队。
这个消防站就位在灾变现场周边,也是最接近世贸中心的消防站。一听见飞机撞击北塔的声音,几个值班的人员冲向窗口,发现大楼起火燃烧。几小时不到,他们当中有五个人丧生。之后这个消防站严重受损,如今作为储存装备和其它物品之用。
轮班时,我经常到那里借用浴室,或者站在屋顶眺望整片灾变现场。站内气氛有点阴森。即便只是我胡乱想像那些人的幽魂在其中流连,我仍能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共鸣。
一边走着,我猛然想到,这晚的灾变现场好像不太一样。什么东西不见了,但又想不起到底是什么。就在到达第十消防站之前,我想起是狗儿们。我好想念以前在这儿出现过的搜救犬和医疗犬。也许因为冷天加上搜索不到残骸,更别提我是轮值夜班,因此很难看见它们。
对这里的每个人——包括我——来说,它们的存在可说是一大安慰。摇晃的尾巴可以如此地振奋人心,实在神奇。
当找到存活者的期盼转换为找到残骸的期待,就连几只搜救犬都受到了影响。日复一日,以及漫长的夜里,狗儿们不断搜寻着生命迹象。搜索落空的持续挫败使得它们精神不振,你可以从它们的疲倦眼神和姿态中看出来。
有时候,为了激励它们,建筑工人或消防员会把某个同事藏在碎石里,然后让训犬员过来。闻出气味的狗会开始兴奋地挖掘被浅埋起来的人。当“救援”完成,所有人一起欢呼,狗儿的精神就又来了,尾巴猛摇,眼睛发亮,你可以看出某种内在的火焰重新点燃。
这份对狗儿的怜悯也让在场的人重振起精神,提醒他们自己的任务并未失败。有勇气每天到这儿来,竭尽所能付出,而仍然能够关怀别人,光这点就是一种成功。我们可以继续盼望——不是期待找到生还者,而是希望自己能活下去。
我登上通往第十消防站屋顶的阶梯,一边沉思着狗儿和鲁迪告诉我的那些事。我一踏出去,惊讶地发现外头站着一个女人,一个看来大约四十七、八岁的救护技术员。她靠在围墙边缘,金色直发飘在脑后,让我想起船头的人头雕像:神秘、坚毅,有一张看不出喜怒的脸庞。
我正想离开,因为我不想打扰她独处;可是她正好回头看见我。当我们目光相遇,她用一种亲切但又戒慎的表情向我招呼。我在世贸现场见多了类似的表情,因此并不以为意。我知道这是疲惫、忧伤,加上极力想压制自己情绪的结果。
我们并肩站在那里,凝视着下方不曾停歇的工作状况。从我们的有利位置,卡车的铿隆铿隆声变得微弱了些,被夜空的消音板吸收了。能够抽离忙碌和噪音真是一大快慰。我们就像两只找到一处高高的窗台歇脚的鸟儿。
这位救护技术员告诉我,她正好在第二栋楼倒塌前到达这里。
“简直像身在地狱,”她说。
“眼前一片黑,根本不能呼吸。我和我同事在混乱和黑暗中走失了,你可以听见脚底下有人尖叫,可是什么都看不见,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断想着我的五个孩子,而且正打算离开双塔。起初我有点犹豫,心想我应该先找到我的工作伙伴,可是我继续往前走。直到当天深夜我才听说他顺利逃出去了。要是当时我回去找他,现在或许不在这里了。要是他回去找我,他的下场也一样。他吓得一直不敢回到这儿来⋯⋯可是我每个月总要来两、三次。”
“你都如何面对那些影像、那些记忆?”我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想我只能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在这里尽点力帮忙。”
“我愿意把生命交到这个女人手中。”我心想。
她生养了五个孩子,曾经和死亡打过照面,如今又回来卖命。有好一阵子,我们静静站着,两个联合起来抵抗悲惨处境的母亲。没有交谈半句,只是让寒风吹袭我们的头发。她的脸轮廓鲜明而美丽,在我眼中犹如一个站在岗位上守护着这片灾变现场的天使。
“我们还是回去干活吧!”她说:“有缘再见了。”
“但愿如此。”我说着和她握手。
“好好照料孩子们。他们很幸运有一个这么勇敢的妈妈。”
“你也一样。”
她笑笑,然而眼里的光迅速黯淡下来,像是关上了帘子。我不知道她是退缩回去以便能继续撑下去,还是试图把那些可怕影像隔绝在外。关于她这部分的故事,我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
下了阶梯,我们分头走开。我回停尸间,她隐入夜色中。
我发现自己在每次与人互动之后总是习惯性地小声祷告。我喃喃默念着无语的祈愿——为了什么?为这些男男女女的平安,为他们的亲人,为所有那些再也不能迎接亲人回家的家庭。
我祷告,为了让自己能继续走下去。
我祈求能拥有智慧,能说出贴切的话语,以便面对下一个需要安慰的人。
我祈求自己不会忘了这些人的面孔。我将它们一一编织,像祷告披肩那样围在肩头。
我迈开大步迅速走回拖车,仿佛这样便能逃离寒风似地。一进到里头,我立刻和一位紧急医疗服务(EMS)技术士(lieutenant)四目交接。他是个灰发、有张娃娃脸的矮壮男子。一双蓝眼睛尽管充满哀伤,却十分亲切。
我在他身上发现我在这里见过无数次的东西:想要诉说自身故事的一种羞涩的渴望。除非他们开口说出来,别人往往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找我或其他牧师聊聊,有时未尝不是一种探究自己情感的方式。单靠自己这么做或许会有点可怕。有时候这也是一种自白的方式。我不确定这位技术士脑子里想些什么,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谈谈。
我们走到一个较隐密的角落,虽说事实上并不需要这么做。目前拖车内只有另外两个困倦的人,而且似乎正在打盹。
我们先闲聊了一下彼此的家和亲人。事情通常都是这么进行的。我们必须先透过一些合情合理、平凡稳当的事物搭起关系,然后才会冒险涉入这阵子的各种惊骇和恐怖话题。
他告诉我有关他的两个孩子的事,一男一女。描述他的儿子时,他开始眼泛泪光,喉咙哽咽起来。
“他实在是贴心得不得了。”技术士说:“我也说不清楚,总之他是可爱又仁慈的孩子。我女儿也很棒,不过是个麻烦精。”
他大笑,摇了摇头。
我感觉他在他儿子身上感受到某种脆弱性,激发了他的保护欲。也许他渴望能保护儿子免于遭受许多人子面临的危险,让人子葬身在这停尸间外面、葬身在古今所有战场上的那种危险。如果他保护得了他儿子,或许也就能找到,并且保护九一一那天遭到摧残的,存在他内心的那个孩子。
技术士低头抹着泪水,接着开始谈起当天他也在这里。
“你绝对无法想像那种状况,人面临的艰难抉择,那种惊恐。有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和他的工作伙伴刚抬着一个女人走下好几层楼梯。她已经陷入昏迷,看来早就断气了。他们才刚走出大楼,它就开始倒下来了。你可知道他们怎么做?”
他问,来回搜索着我的眼睛。
“他们把她放下,开始没命地跑。他们非把她留下不可,因为他们只有几秒钟时间。要是继续抬着她,他们肯定全部没命。可怜的女人。到现在我朋友还难过得要命,他老是想起她。可是,要知道,他有四个孩子,他不得不做个抉择。但他良心上过不去。为什么老天要逼人做这种决定呢?”
“没人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会怎么做,”我轻声说:“除非自己遇上了,而且谁都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在那种生死关头可能会做的事。”
“你知道让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粉尘。从铺天盖地的粉尘中走过,我们很清楚我们也从人的骨灰中走过。我身上盖满了,盖满了别人的骨灰。”
技术士哭了起来。他垂下头,一手捂着脸,将泪水哗啦哗啦倒入看来像是汇集了集体伤痛的无底巨杯的掌心。
“对不起。”
他说,揉着眼睛。
“这是我事发到现在第一次哭。我没事的。”
忧伤压在他壮硕的肩上。他会忍住…….可是他真的会没事吗?我们当中有谁会真的没事?尽管机会不大,但他的某些特质让我仍然对他抱有希望——他的勇气,他的正直,他那温柔的忧伤。我为他的小儿子和女儿默念了一段感恩词,然后为他内心的赤子——他暂时遗失了的那个部分——祈祷。
当然,我们决定到这儿来都是因为热切地想要尽点力。但要是有恐怖的影像萦绕不去呢?要是必须做出没有回头路的抉择呢?站在技术士身边,我将手放在他肩头。我感觉得到天使翅膀在他夹克底下翩然鼓动。他可知道它们的存在?他可曾想到,他穿着行走的鞋子是上帝的鞋?
“继续说吧!”我心想:“继续诉说你的故事,一直说到你的负荷消失,一直说到那些骨灰成了雪花落下,有如宽恕,一片片,在独一无二的完美里,消融于无形。”
等我转进我家那条街、把车开进车道时,冬阳已渐渐上升。成排的房舍看来已经不再像婴儿床,它们是将我们紧紧托住、让我们不至于散落到冰冻草地上的骨架。我需要再度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我自己的人生。我好想,但不知怎地有些犹豫。我知道自己既疲倦又亢奋,不断想着我似乎遗忘了什么。也许是我的一部分,而我必须把它召唤回来。也许我想太多了。
我打开门,屋内一片寂静。我们的斗牛犬赛奇正肚子朝上,呼噜呼噜睡得香甜。我走进来时,它连动都没动一下。好个尽责的看门犬。拆开的圣诞礼物散置在地板上,感觉似乎也正沉沉睡着。只有那棵树——张开绿色臂膀,浑身松香——仍然醒着向我道早安。
我轻手轻脚走上楼梯,进了女儿的房间。我在她身边躺下,将鼻子凑近她的脸颊。她身上有种热面包的味道。
“妈咪,你回来了!”
她睡眼矇眬地说,身体偎了过来。
“是啊,亲爱的,我回家了。”我悄声说:“我回家了。”
我闭上眼睛,将这晚的种种一切用帘子隔开。在帘子的那侧,市中心的机具仍然隆隆运转,精神抖擞的工人来接手疲惫同事的班。我无法答应女儿这是我最后一次轮值。新年快到了,还有太多工作要做。我不必再去,我随时可以说不。可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碎片留在了世贸灾变现场,这会儿带着别人的碎片。
除非整个工作完成,我怎么也无法把自己完整拼凑起来,而且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别人的残片。我选择了一幅图案细致繁复、部件纤弱的马赛克拼图。纵使最终的构图还不明晰,我知道所有的碎片都在那里。同样的光从蓝色、白色的碎片折射出来,无论是光滑或粗糙。它照亮空白的部分,填补了空隙,直到下一个碎片被发现为止。
目前,我正站在大片深达膝盖的彩色玻璃碎片中。也许,总有一天我可以退后一步欣赏。而我期待看见的是一股更加深化、而非裂解的信心,不管是对于人性、上帝,或者我所做的抉择。◇(节录完)
——节录自《让光照亮你的心》/联经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昀
点阅【书摘:让光照亮你的心】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