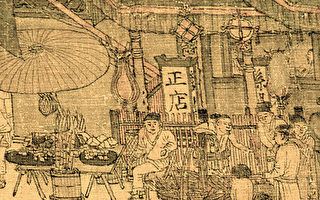回到无所有之处,能看见多少自己,才能看到多少世界。
城市各有不同的孤独。
上海是你在街上走过,闻得到弄堂人家晚饭的味道,看得见灯光,听得见炒菜锅的声响,但你感到那些和你并没有关连,你只是从他们窗外走过。
北京是闻不到,每条街都那么阔,住宅群集在小区里,与街道还隔着遥远的庭院造景。一个小区或许是个有上万人聚集、向上堆叠起来生活的空间,但你有可能从外部感觉不到它的一丝人间烟火气。这也会使你感到孤独。
那年我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季,飞机降落在漆黑的停机坪上,机舱播音说外头气温零下十五度。那些年是我很愿意远走高飞,很愿意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那时我不太害怕孤单。
当你觉得自己还在往前走,孤独就不可怕。你想看前面的风景,你想被一种没有体验过的温湿度包围。那些陌生感击落在心脏上的刺痛,代替有人陪伴而成为一种期待。
我在北京生活了四年,住在一个租来的,二十层楼高的公寓里。窗外是天空,只有天空。因为没有哪棵树能长到二十层楼高,而其他的建物距离都有些远,都在街的另一头。
这个小公寓每到下午阳光西晒。因为是冬天找的房子,当时不怕它太暖。我还记得那个冬日下午,我已经在户外走得又冷又累,看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子,直到走进这一户。一开门日照敞亮,迎面就是一窗户的天空。空气干燥,白色沙发布表面漂浮着很淡很淡的灰尘味道。
我想,就是这里了。我就把自己寄存在这个被阳光漂白了的空间里吧!
这本集子里,有一半的文章写在北京,在那个窗外只看得到天空的公寓里。另一半,写在去年我回到台北之后。
在北京第一年的冬天,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真的看到历史小说里常描写的那种:一轮鸭蛋黄般的太阳。
在台湾、和世界上我曾去过的大部分地方,太阳光都是金色,或是白色的。但北京真的有橘红色的太阳。经常是在薄雾的日子,可能是雾中悬浮的物质折射了光线,使太阳有了颜色。
如果你停下来远望,它就在那里,因雾气而轮廓模糊,在常见的灰墙上方,在掉光了树叶的白杨树稍,远远地挂着。有一点疏离,静寂而古老。或许其他人都看惯了这样的风景,并不会为它停下来。而我总是会。
另一个我始终记得的风景,是北京夜里的雾与光。那时我上班的公司在东长安大街。加班后搭电扶梯下楼,穿过一整座地下商场后,从街的对面冒出地表。
夜里的东长安大街通常清冷,人车渐少。路两旁装饰着繁复的巴洛克式街灯。在雾中,那些灯光就被晕散了,每隔一段距离有一盏昏黄,越远越隐约,直到被雾气全面抹平,再也分不清是这盏或是那盏。
站在街边等公车,这雾与灯的夜景有时让我想起巴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桥上也有这样形制复杂的灯。一张有名的照片是沙特站在笼着薄雾的桥上,穿着厚重的呢大衣,叼着烟斗,背后白气茫茫。远处有灯光靠近,我等的公车来了。
当我重读这本书辑一一“月夜”里的文字时,北京的雾、天空、寒冷、它的日与夜的感觉,又回来了。它的遥远也回来了。孤独感,并且是只有北京这座城市才会给予我的那种孤独,都回来了。
在北京的那几年,我读的书有点两极。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读了许多关于科技、与科技对人的影响、未来趋势的书。我很关注那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新的人类情境,例如人工智能与棋手的对弈,城市大数据与自动驾驶。
另外我重读了一些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封神演义》、《左传》里的文选等等。
当我在书店没有找到想看的新书、不知道该读什么的时候,我就走到古典的书架前,它们是安全而不易位移的选择。
因为很孤独,所以经常不自觉地在这些书籍里寻找可以同理的角色和情境。因为很孤独,似乎也就特别清晰,总是看到年少时没看出来的涵义。
比如有一天我读〈郑伯克段于鄢〉,它是有关三千年前一个统治家庭的内争,演变为一个小国的血流成河。是个关于仇恨引发更大的仇恨、轻蔑引发更大的轻蔑的故事。
然则它又是关于一个善良的小人物,一个微不足道的他者、比郑伯家族位阶低很多的颖考叔,这个小人物以同为人子的同理心,救赎了一个深陷于悔恨循环中的权势之家。
这故事非常超越时空,我想,它就算出现在《魔戒》或是《权力的游戏》里,也毫无违和感。或许,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智能和算法逐渐变成为我们自身存在看不见的邻接面时,人类唯一可能的视角是颖考叔的视角。
你追问不了在远方进行的战争与权力的游戏,你活在一个被给予的位置,你的生活受到更巨大层次布局的导向,但你也还能从自己出发,有一种同理心去理解,从而洞悉了在眼前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像颖考叔那样。
有时,它正是整体数据库之所缺少,但应该被运算进去的一件事。
当我想起读这些书,写这些文章的日子,想起像〈郑伯克段于鄢〉这样的古老文学是如何来到我生活里而我又如何藉由它们思想,我也会想起北京的雾。那时的霾还没有后来的严重,而雾赋予了北京的太阳和夜里的街灯,一种属于那座城市特殊的朦胧和色温。它像是蒙在我的感官与孤独之上的一层遮罩,将我引向了这些阅读与这些感觉。
年轻时候看世界,总想看得分明,觉得它应该分明。中年看世界,就明白有些事物确实是笼罩在雾里的,这世上也有只在雾里才会出现的风景,像是鸭蛋黄般红色的太阳,和东长安大街按距离排列的晕黄。你要把雾连同世界一起看进去。看作是此刻的一笔数据。
比起明亮的日光朗照,阅读文学或是古典典籍,更像是在这如雾笼罩般的世界里,寻找月色的照明。文学与艺术,或许不是直接应答现实世界的问题,给不出口号主张和表面的是非对错,但它们挑动的是某些更细微的神经——是这个阅读者、感受者,这个想要理解世界的人的神经,然后,他可以自己去回答世界。
有时我感到其中有答案,那答案经常是来自有什么折射了我自己。一种既指涉又共振,既朝外又向内的辩证关系,你既是问问题的人,也是问题的本身。
有时你是感动于在文学与艺术里看到的探求,而不只是那作品的好坏。
有时你在极古老的书籍里,发现有一则记述,穿越时空来标示此刻的你。然而在得到这些启示之前,多少要有一种勇气去放弃。放弃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披挂穿戴的那些短促、有所凭依的立场,放弃那些张口就来、标签化的是非与功利。而自愿走进比雾更深的地方,去获得对世界另一维的理解。
……如果看得够清楚,就会知道那样的深入雾中不是作为什么崇高的牺牲。而是时至今日作为人类活在世上之所必需。
若非如此,那些人云亦云的成见,或出口咄咄,或嘻笑讨巧,那些十分便于在社群网络上引来赞声的话语,其话语的跟风、再跟风只会将我们绕进没有出路的迷宫。
有时我感到我们是一个雾中的世代,被标举在亮处的价值太多,话语太多,义正词严太多,但集体却失去方向感,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里。
如果不可解的世界是雾,我们还是能尝试去到比雾更深的地方,从那里回头看自己(首先是自己),在雾中的形状。这个经验是重要的。放下了鲜衣怒马的幻术,回到无所有之处,能看见多少自己,才能看到多少世界。◇
——节录自《比雾更深的地方》(作者序)/ 木马文化出版公司
<文苑>选登
责任编辑: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