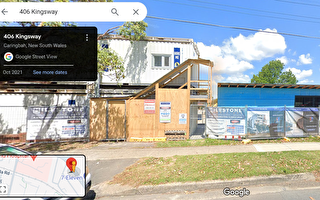【大纪元2019年05月31日讯】编者按:六四三十周年前夕,现居澳洲的艺术家郭健作为一名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了那件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往事。
(大纪元记者安平雅悉尼报导)三十年的时光,能否抹去一段血色的历史?海外宁静与自由的生活,能否疗愈一个人心底的伤痛?
1992年,历经波折,死里逃生的郭健终于踏上了澳洲的土地。
郭健说自己曾经两次出现“真切”的幻觉,“96年的一天,我在悉尼歌剧院门口看见了一辆坦克。大约十年后,我第二次看到这个景象,旁边站着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
“在澳洲经常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多年后,我听到这个声音仍觉得自己置身天安门广场,还在长安街上,一听到烟花的声音,就觉得是枪声”。他说。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人在自由社会生活多年仍无法摆脱恐惧的阴影?
1987年,正在中央民族大学国画专业读书的郭健,一天在宿舍里听到隐隐约约的口号声, “我以为哪里在放电影,奇怪的是,口号声越来越近” ,觉得肯定有事发生的郭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学校门口,但学校大门锁了,学校领导、保卫科的人站在大门前。
“谁出去就开除谁”保卫科的一个人喊道。
过了一段时间,再得知有学生游行时,郭健往操场边的围墙那跑,跑到时,已经有很多学生在墙头上往外看了,大概看了半个小时后,郭健一纵身跳了下去,“我站在游行队伍边上看着,突然间心里觉得很害怕,自己怎么会在这里,看着周围所有人都像是警察、便衣,比游行的学生还多。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一种从心底升上来的恐惧感。”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郭健和一个同学悄悄写了一个标语,类似 “打倒贪官” 之类的,俩人半夜时战战兢兢地贴到了校园的告示栏上,第二天去看时没了,以为自己要被抓的恐惧再次袭来,让他俩吃惊的是“居然没事”。
不久,郭健和同学跑到北大清华,一看校园里到处是标语,像是受到了鼓励。但看到站在那里看标语的人就觉得他们是警察和便衣,郭健说,“危险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带给他的感觉是“大学像监狱,好像所有人都在监视你。”
郭健在北大看到学生的游行通知时,当晚就在学校操场的围墙边等着。“我从墙上跳下去了,走到了游行的队伍中。”
和游行队伍走到天亮的郭健,来到积水潭时看到绿绿的一堵人墙,全是精壮的小伙子。
“那时已经不是恐惧,已经是恐惧的极度版本,感觉他们快开枪了。”郭健说,“学生开始去冲人墙,随着那堵人墙被冲开,我内心的恐惧在此刻好像得到了释放。”
5月,得知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那天晚上,郭健骑上自行车直奔广场,加入了最初的一两百人之中。在那里坚持了七天半的郭健被强行送往医院。
6月2日晚上,听说军队已经到广场的消息后,郭健赶去时看到人数众多的军人穿着白衬衫,背着背包,身上没有携带武器。 “你别以为他们没有武器,他们的武器都在大巴里,被学生和市民劫下来了”。
6月3日,学生将大巴开到中南海,准备归还给军队,归还前,学生将车上的武器拿出来展示, 郭健说军队开始向人群仍催泪瓦斯, “一颗就在我身边爆开”, 他们将大巴抢走了。
郭健想起来,其实早在5月份他们绝食那会儿,一次去上厕所时看到很多军人在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里。“当时大家都已为军队还在城外面时,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在那了。绿压压的一片,钢盔闪着锃亮的光”。他说。
当天吃晚饭的时间,郭健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天安门,发现没什么事,一些人在那里庆祝胜利。大约10点左右,郭健听到了远处传来像鞭炮的声音,他看到有人从西边向天安门广场跑了过来,边跑边喊 “他们开枪了,他们开枪了”。
那一刻郭健都觉得不可能,应该是谣言。不一会,他看到三轮车拉着人过来了,血糊糊的,郭健心想可能是被打的吧,不会是开枪了。
想要弄清事实的他和同学一起向木樨地骑去。
郭健看到很多人拉着不知是受伤还是死掉的人就过来了。其中遇到一个被人扶着的人,他说刚从医院出来,腿上中枪,子弹取出来了,拿给我们看,我还在想是假子弹吧,他扔到我手上,我一看是真的。直到那时,我还是不能完全相信。
继续往前走,看到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一辆巴士横在了路中间,有人要点巴士,郭健和同学去阻拦,认为不要给当局制造口实,巴士上的人愤怒喊道:“你们没看到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吗?”郭健这时才注意到已经有很多人在他身边倒下。
“子弹打在地上溅起的火星,我都不觉得那是真的,那些人就在我身边倒下,完全和战争一样,但当时就好像没有意识。“郭健讲述到。
郭健看到一面北大化学系的旗子在烟雾中若隐若现。透过烟雾散开的一瞬,郭健看到一群当兵的正在冲,学生迎着他们冲,一边冲一边倒下,不一会那面旗子就看不到了。
“有几枪打在我旁边,有人倒下了,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真的”。和郭健一起的同学无意识的仍往前冲,“我一把抓住他说,‘别跑了,跟我走’。我们俩开始掉头跑,往路边的胡同里跑。进去才发现,胡同的地上全部是鲜血,那里是复兴医院, 医院里面的过道上、走廊上全部是人,死的、伤的,墙上、地上到处是血,我当时完全傻了。”
医院的医生找人帮忙,郭健和一些人跟着到了一个房间,医生让把这些尸体抬出来,郭健一进去就被吓坏了,全都是摞起来的尸体。“奇形怪状的,地上的血这么厚,我同学一进去就差点摔倒了,我们都要吐了,干不下去,医生还在分配任务的时候,我和同学就走了。”
有人提议我们去街上救那些没死的人,我和同学就跟着去了。一个人拿着一块白手巾绑在一根棍子上,当白旗,我们就这样出去了。看到路边有个人躺在地上,血流如注,我们抬着他就往医院跑。交给医生后,我们又出去,我们四个人抬,拿白旗的人断后,突然这个人被打中后脑倒下了。“我和同学哭都哭不出了”。
医院门口的停车棚临时改成停尸体的地方,好多死掉的人就堆在那。
“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哪个学院的,赶快去认认你们的同学,我坐在那里,根本不敢去认,那时才发现那个血腥比想像中要残酷得多,是人根本承受不了的”。郭健说,“我和我的同学当时不要说勇气,人已经崩溃了、瘫掉了,我们坐在路边一句话都说不出,坐了很久很久。”
回到学校的郭健已经失去了语言的组织能力,在学校副院长的询问下他努力表达,“不要让学生再出去了,出去就是送死”。精疲力尽的他回到宿舍倒头睡下。
“坦克已经开到了学校”,郭健被这样的噩梦惊醒后,发现现实中虽然不是坦克,“但真的有装甲车正在学校周围巡逻”。
“6月5、6号时,有车开进学校来抓人,到8、9号时,学校没人了,街上也没人了,只剩岗哨,呼啸而过的军车,零星的枪声伴随高音喇叭的呼号”。郭健说,“ 整个城市像座死城”。
枪声后的觉醒
三十年后,再讲起那段往事,郭健声色平静,但能感受到那结了疤但已烙进他生命的伤痛再次被碰触。
在郭健看来,“中共的体制注定了这场屠杀的发生,没有六四,还会有‘七四’、‘八四’,中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三反、五反、文革,这些都是屠杀行为,只是被冠以了革命的名义。只要老百姓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中共就会认为失控了,就会下手,这是中共的本质注定的,中共的性质不变,中国就注定不会有改变。”
六四的枪声惊醒了他。
“(六四前)我当过兵,我认为当兵的人只能向敌人、坏人开枪,而现在我被他们(军人)看成了坏人,我作为学生的角色被看成了敌人。我当时很震惊,才明白了以前那些被我看成是坏人的、被中共镇压的人原来和现在的我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场景变了”。内心受到冲击的郭健说,“你突然发现你站的位置不对了,你曾经认为是敌人的人竟然是你自己。我看到了两个自己,一个是当兵的我,一个是学生的我”。他说。
郭健说自己最后终于明白了,(在中共治下)敌人的定义就是,中共认为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你根本没有任何主动权判断对错,中共说你是错的你就是错的。只有到那一天你才会明白过来,我们只是他们把玩的工具,中共想灭掉你就可以随时灭掉。别人受的难就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我们受的难也是别人可能会遭遇的。
“六四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不会再上中共的当了,人的转变就是你怎么从一个骗局中站出来,就这么简单。对艺术家来说你的创作方式、创作思维全都改变了、完全改变了。我根本不会再在中共的体系中行事了,也因此,我比较能看清楚他们在干嘛。中共的骗局不是一个,是很多个。洗脑也不是一种,是很多方式。”
历经波折 摆脱恐惧
屠杀发生的第二天,郭健得知很多人准备去广州那边,需要去派出所办边防证,他看到派出所的人很同情学生,很帮忙,痛快地办理和盖章。他由于当时有点事情没走成,等到他6月8、9日再去派出所盖章,气氛就变了,郭健被赶了出来。
各国撤侨时,郭健的澳洲朋友找来一些护照,当时谁稍微像点能沾点边的,就都可以拿着护照登机,“不巧的是,里面没有和我像的”。他说。
后来,学校复课,郭健回到了学校,学校开始了整肃,要参与过六四的人写检讨,郭健写到第十一天,抄报纸上的内容,交了11页纸的检查,勉强过了关。
带有惩罚性质的,郭健被分配到家乡贵州的一个工厂里当宣传干部,他那时就决定不要跟中共这个体制再有任何关系。毕业时,就留在北京成了一名北漂,搬去了圆明园,那里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艺术家村。
郭健申请了三年护照,都未获批准。他被变相禁止离开中国。
我被警察骚扰,从很早就开始了。我离开中国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经常被干扰。
善良的澳洲人给了郭健很多的温暖与感动,
那段人生经历“从头到尾都是在挣脱恐惧感的过程”。 郭健说,“直到1998年我做个展,创作一些军人的角色,
责任编辑:宗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