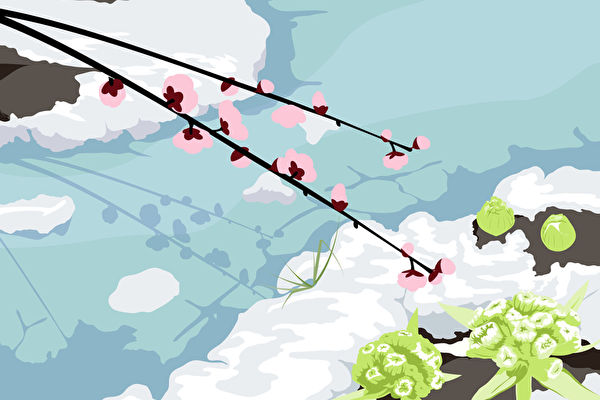第四章 铁骨金心(1)
末世七年
凤鸣书院。
吴致手腕推一盆花,置于蔷羽面前。
蔷羽微微一笑,摘下花朵,戴于鬓上:“好看么?”
“好看。”吴致点了点头。
“吾去做饭。”蔷羽走至菜园,蔷羽摘了几棵菜,生火造饭。冯亭脚步蹒跚,走入厨房,挽起袖子,便要洗菜。蔷羽连忙拦住,道:“这里烟熏火燎,你有身孕,快些出去。”冯亭道:“整日里闲的无事,想找师姐说话。”
蔷羽道:“小儿衣裳做了一半,怎地无事?”
冯亭道:“也不知是男是女,这才放下。”躺卧摇椅,望着菜园,一片绿油油,心中感慨:“当年幸得这片菜园,不然吾等只怕也要饿死了。”
蔷羽煮米下锅,坐于石凳上,剥着橘子:“要我说,大锅饭早晚吃得穷。人人忙着表忠心、告密,谁人种地做活,偏赶上朝廷收重税,家里粮都交了,赤军把守城门,饿死也不教人逃命。”说话间,眼睛泛起红色,橘子递给冯亭:“要不是严师弟,豁命抢回些小米,泽林只怕活不到今日。”
冯亭安慰道:“苦日子都过去,一切都会好了。”
“是啊。”蔷羽抹抹眼睛,抽噎一声,道:“来年家中添丁,大家都好。”说罢,转入厨房炒菜。
冯亭吃了瓣橘子,酸到心里。便在这时,严奉匆忙进院,阖门落栓。
“天还大亮,关门作甚?”冯亭道。严奉神情紧张,叫来吴致、蔷羽,道:“众人赶快收拾东西,随吾去乡下避难。”
“发生何事?”冯亭不解。
严奉道:“刚接到祸王策令,孔夫子贬到地下,说是宣传反动思想,还要破除一切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仰望高檐,矗立百年,叹了口气,道:“这凤鸣书院,命也到头了。郊外城隍庙早砸了,连各家供的灶王爷也不放过。众人快收拾东西……”
吴致、蔷羽慌忙收拾细软。“泽林呢?”蔷羽急道。
“还在城里开会。”吴致道,“吾去叫他回来。”
冯亭忽地腹中一痛,撑腰坐下,埋怨道:“这思想文化,住在人脑袋里的,怎生除掉?难不成,要将头摘下来给他们不成。”
严奉皱眉道:“别胡说!这书本笔墨,都不能留!”正要点火烧掉。忽地门闩断裂,一帮十几岁少年,皆身着赤衣,冲入门内:“给我砸!”一声令下,书院顿遭蹂躏。孔子石像,百代经典,千年古迹,皆被砸毁。赤衣小兵还不满意,挖地三尺,捡出无数古玩真迹,皆付之一炬。蔷羽眼见苏伊尸骨也被刨出,不由自主上前,却被吴致死死拦住。
赤衣小兵一顿摧枯拉朽,眼见四人,叉腰上前:“跪下!”严奉摆摆手,四人无奈,只得照做,赤衣小兵瞅瞅冯亭,忽地一抽皮带,冯亭立时嚎啕。
“怎可无故打人?!还是孕妇?”蔷羽喝道。赤衣小兵但要上前,严奉拦在身前,道:“吾才是书院先生,有何事情,冲吾来。”
“早就等你啦!”走出几个赤衣小兵,严奉定睛一看,正是七年之前,从书院赶走那几个,稚气虽被戾气掩盖,面目依稀可认。几人一哄而上,严奉头发被剃掉半边,衣衫扯破,挂上木牌“牛鬼蛇神”,游街示众。
“相公、相……”冯亭一时忧愤,晕死过去。
游街路上,严奉忍受不住毒打,不断喝道:“吾也是赤衣党!吾也是赤衣党!”
“赤衣党还宣扬反动思想!祸王思想不坚定!给我打!”赤衣小兵冷冷一笑,“打的就是你!哼!”
凤鸣书院已化作灰烬,吴致领着蔷羽、冯亭,暂且回至泉语琴铺:“听说以前那个找麻烦的赤衣人,被当作反动派流放了,吾等暂且在此,该当安全。”吴致道。
蔷羽抱住冯亭,眼中满是悲伤,泪早流尽:“弄些吃的来吧,师妹两个人,不能饿着。等晚上天黑,再去看看师弟……”
“哎。”吴致口中答应,转身抹泪,换上赤衣,转身交给蔷羽一粒药丸:“这七年来,吾日夜研究,终得这一颗还魂丹,你拿着有用。”说罢,出门去找吃食。听得其言,蔷羽心慌意乱,喃喃自语:“大人若是不行了,孩子还得活着……就、就这一脉骨血……”颤手端水,喂着冯亭服下。
不多时,冯亭醒转:“严奉、严奉怎样了?”蔷羽紧紧抱住冯亭,泪如雨下:“别吵、别吵,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真的么?师姐,你别骗吾。”冯亭泪眼相对。
“师姐什么时候骗过你?”蔷羽收紧臂弯,泪珠断线。
门外忽地吵嚷,心知不妙,蔷羽将冯亭藏于柴房,用干草盖上,自己走至门外。冯亭心内害怕,腹中隐隐生痛,偏又不敢出声。
片刻过后,吵嚷之声渐远,隐隐闻得烟火味道。 冯亭大惊,勉力起身,扶着墙壁,回首一望,房顶皆已着火。心中恐惧,却在开门一刻间,险些窒息:“师、师姐……”只见蔷羽倒卧于地,满身血痕,面目遭受重创,几不可辨。
“师姐……师姐……不、不……相、相公……”冯亭心下大骇,震惊之刻,尤念夫君,转身奔出琴铺。
****************************
话说吴致到得街上,一片狼藉,赤衣小兵,打砸抢烧,好好一座城,一夜之间,毁得不成样子。人群密集处,几个曾经书院少年,手持赤书,喊打喊杀。面前跪地之人,头发已被揪秃,露出毁容样貌,抬头仰望,眼中泪光闪烁。
“你说!她不是你亲娘,她是谁!干啥的!”一个赤衣小兵推搡,何明衣衫渗血,显然遭受毒打,跪倒于地,皮鞭再次加身,终于极端苦痛之中,良心泯灭:“吾坦白,坦白……她、她不是吾娘!她是娼妓、是吾爹买来的娼妓!”
“那你爹又是干啥的!”赤衣小兵叉腰喝道。
“爹、爹是大反动派……”何明被逼至极端,几近疯癫:“爹?吾没有爹。祸、祸王才是俺爹!祸王万岁!祸王万岁!”
吴馨闻言,冷笑数声,不知是笑命运捉弄,还是笑世道变迁,冷冷笑声,凄厉异常,终止于一赤衣小兵之手:“一日作妓,终身作娼!”放下染血铁锹,抹掉头上冷汗:“再去斗,下一家!”
一众赤衣小兵,手上沾血,眼中充血,大杀四方。忽地,前方红旗招展,一人道:“祸王特使来也!祸王特使来也!”
再观那特使,吴致脚下一个踉跄,坐倒在地。昔日师弟,竟身着赤衣,振臂高呼:“祸王万岁!祸王夸大家干得好!砸烂旧世界!砸烂反动派的狗头!”赤色小兵激动万分,竟眼含热泪,胡锵令众人安静,喝道:“宣布好消息!革命性最强之人,可随吾进京,得祸王亲自嘉奖!”提手指指点点:“尔等哪个?革命性最强?”
一人高举双手,道:“吾砸了十个佛像!”
“那算啥,吾砸了十个反动派狗头!”
“俺、俺亲手杀了俺爹,他是大反动派!俺们要跟其斗争到底!”
“对!斗争到底!”众人阵阵高呼。
杀声淹没大地,鲜血染红云霞。青天不再,红旗蔽日,良心尽灭,兽性狂发。
小东踹开家门:“娘,快拿饭,吾要饿死了。”
鲍氏端上饭菜,擦拭儿身污渍,皱眉道:“又去哪里鬼混?瞧这弄得一身脏。”小东不以为意,道:“别擦别擦!祸王说了,满身脏才最革命!”
鲍氏仍不停手,道:“那依你说,那下地里掏粪的,才最革命!”
“您可算开窍了!”小东穿上赤衣,戴上袖章,道:“娘,吾要跟特使进京,觐见祸王,回来以后,让你骑大马、坐轿子。”说罢,匆匆而去。
“啊?进京、祸王……”鲍氏喜极而泣,上香三柱:“保佑保佑,你个死鬼爹可看见,咱儿终于出息,要做大官啦!”拜拜鲍爹,抬头看见菩萨石像,心下一气,抓起摔得粉碎:“天天拜也不见得升官发财!哼!”说罢,将那祸王头像,摆至神龛,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还是咱祸王灵验,俺可得多拜拜,保佑俺的小宝,升官发财。”
****************************
冯亭四处寻不见严奉,又被那几个书院逃生遇上,四下喊打喊杀,危急时刻,忽见一熟悉身影,立时大喊:“俞芳、俞芳师姐!师姐救命!”那俞芳似乎也看见,忙叫赤衣小兵住手,将冯亭扶入客栈。
“俞芳师姐!”冯亭哭倒在地,“幸好遇到你,否则……”
俞芳递过丝帕,道:“你怎地在此?其他人呢?又怎会怀有身孕?”冯亭忙将此前种种,讲个大概,抬首看见俞芳一身赤衣,惊道:“师姐怎会?”
俞芳道:“当日吾等四人,未入深阙,退回琼林,却被祸王撞见。本以为将死,岂不料祸王宽宏大量,不仅赦免吾等罪过,反而多加重用。”
冯亭皱眉道:“吾想起来了,那赤书之上,改造之字……”
“便是胡锵师兄与吾一同做的。”俞芳端起茶来饮,道:“别说这些闲事。其他人究竟如何,现在何处?”冯亭讲了个大概,俞芳取出纸笔,道:“你别着急,严奉师兄不认得吾,尔且修书一封,吾便带他前来。”
“也好。”冯亭当下书信一封,俞芳收起,藏于袖中,道:“你在此好些将息,休要出去乱走,等吾回来。”
“知道了。”冯亭点了点头,俞芳阖门而出。
不消半刻,屋内忽然冲入许多赤衣人,架着冯亭离开。
****************************
话说严奉遭赤衣小兵毒打,幸得被另一赤衣领头见着,遂驱散小兵,带至琴厂:“你怎会惹上那帮愣头青?”严奉见是衙门领头,道:“外面闹成这样,草菅人命,尔等衙役,怎地不管?”
衙门领头无奈道:“祸王不叫管哪!今日还派了特使来,教吾等配合赤衣小兵。”
“什么工作?”严奉忍痛道,“不过是土匪行径,打砸抢烧,你们也是助纣为虐。”
衙门头领道:“别看人家年纪小,下手比吾等都狠。连这琴厂厂长之家,也被抄了,说是要彻底破除文化。”
“这琴也是文化?”严奉道,“哎呦。”
衙门头领道:“自古传下来的,不都是文化。说是砸烂旧世界,哪个逃得了?”
“哼!”严奉忍痛道,“说得好像他们不是旧世界人生的。”
“诶……”衙门头领道,“你可说对了,方才便见到几个,亲手打死父母、老师,唉……要说都是你们造的孽,不教人学好。”
严奉委屈道:“吾等也是奉命办事,只能教赤书。”
衙门头领忽地想起什么,道:“你这赤衣党身份,还没告诉老婆?”
严奉叹了口气,道:“若早告诉,能打成这样么?”
“这你可就是自讨苦吃。”衙门头领道,“想你立了多少大功,家里去不能声张?”
“立了多少次大功,卖了多少次良心。”严奉叹了口气,道:“若非是吾,斐音师妹也不会死。”
“你说那个尼姑?”衙门头领笑道,“吾等去时,还在顽抗呢!吾看是念经念傻了。”
便在此时,屋门打开,冯亭泣涕指问:“可是真的?尔当真卖友求荣,害得斐音师姐惨死?”严奉心下大惊,也忘了疼,跳下长凳,奔至其前:“你听吾说。”
“啪……”一声清脆,打在脸上,冯亭大哭,严奉握住其肩,道:“吾做这一切,不过是想咱们能平安度日……”
“背负愧疚,在世上煎熬么!吾真是有眼无珠,看错人!”冯亭甩开严奉,哭奔而去。
严奉愣在当场,不知所措,衙门头领道:“还不去追?外边杀人放火,可也小心孩儿。”严奉猛然醒悟,追出琴厂之外,不见人影;四下寻人,亦不见踪迹。
“泉语琴铺。对,泉语琴铺。”严奉奔回琴铺,凄惨景象,夺人心魄。吴致跪地,手腕轻触其面,七尺男儿,竟哭如赤子:“蔷羽……吾对不起你……吾不该、留你在此……”
“师哥、师哥……”见其心殇难抑,严奉不知所措,口中喃喃自语。
“你走开!都是你害的!滚开!”吴致双手使不上力,弯着手臂,几次三番想抱起蔷羽,皆作徒劳。
“吾走、吾走……”严奉失神落魄,游魂一般,在街市之上游荡:“自己究竟错了么?无非想让家人过得好些。为何、为何最后,人人都如此凄惨……”痛悔无济,委屈难平,无力跪地,痛哭流涕:“这艰难的世道,何时才能过去啊……”
身边走近一个赤衣小兵,踹其一脚,道:“你的信。”严奉拆信来看,竟是冯亭笔迹,顿时慌神:“人在哪?带吾去!”
“跟吾来吧。”赤衣小兵道。将其领至纺织厂,赤衣小兵祸乱之后,其地便被改造成集中营,四处铁栏,赤衣小兵持刀而立。
“进去吧,人便在那。”赤衣小兵离开。夜不掌灯,周遭暗黑一片,头顶一束星光,照在一人身上,双臂吊着,全身悬空,空气之中,血气弥漫,令人作呕。严奉望着地上一滩黑色,不敢近前,不敢相信。
“不是尔之夫人,一日之间,便不认得了?”尖声传来,黑影若隐若现。严奉头痛欲裂,慌忙抱住其人双腿,血满衣襟,滴滴而落。冯亭仿佛认出,动了动口,却不闻一声。
尖刻声音再现:“此人是琼林余孽,尔知情不报,该当何罪。”
“你们……不是人……”严奉恨道。
“哈哈哈……”尖刻声音再响,凄厉如枭:“你说对了,吾等本不是人。祸王所言不错,旧世界将人变成鬼,新世界将鬼变成人。吾等便是新世界之人,人形兽心。”
一股森然恐惧,萦绕全身,严奉忍不住发抖:“吾要带她离开。”
“还是跟她一起陪葬?”尖刻声音道,“上头有令,念尔是赤党份子,书院先生,也是有头脸之人,留下还有用处。”
“尔等要吾怎样做?”严奉咬牙道。
尖刻声音道:“写下书信,与其人划清界限,以表忠心。”
“吾若不写,又会怎样?”严奉道。
尖刻声音道:“不会怎样,就继续在旧世界里做鬼罢。”严奉心下一痛,无可奈何,跪倒于地,蘸着妻儿之血,一笔一画,但如剜心。滴滴眼泪,浸漫字迹,严奉抬首,面上冰冷,顺口入喉,苦咸入心。抬眼望见,星光闪闪,晶莹点点。严奉一提衣衫,头也不回,大步离开。
冯亭心殇至极,全身发抖,眼泪簌簌而落。忽地绳松,双腿落地,膝盖似碎。俞芳拾起血书,交予赤衣小兵:“呈予祸王,凤鸣书院严奉所书,必令天下士人死心。”
“是。”赤衣小兵转身而去。
“为、为何……”冯亭口角渗血,勉力开合。俞芳揪住其发,仰头面见:“还记得曾经画部之中,论画艺技术,你吾不分伯仲,但是为何,西白马总夸赞你,却从不肯施舍半字赞赏予吾。”冷笑一声,续道:“拜在祸王麾下,方知这世间,实该绝对公平。谁人言富贵天定,吾偏不信,得不到就抢,抢不来就索性毁掉它。”放下其首,起身傲立:“日后,再无人与吾比肩,你这一座高峰,终也教吾削平!”说罢,冷笑而去。徒留冯亭,倒身血泊,半死不活。
****************************
“肖彰、苏伊、师姐、冯亭,还有吾未出世的孩儿……死了,都死了……”击垮最后一丝底线,彻底暴露于残暴策令之下,严奉脚步踉跄,游走街头,耳畔读书之声犹响:“革命人……战斗到底……砸烂旧世界……”
湖畔荒凉,书院早成废墟,湖中芦苇荡漾,严奉再无力支撑,跪倒于地:“原来,天地之大,真的会有绝路;原来,头脑中之思想,也可被人拿干洗尽;原来,人的良心,真的可以被掏空泯灭;原来,一直认为的魔鬼,其实就在人世;原来;世间已堕魔道,容不下一丝人性!”晚风漾起涟漪,“扑通”一声,水波震荡,片刻不惊,变作原貌。腥风阵阵,席卷大地。
同一时间,小东高举赤书,奔出家门。鲍氏紧随其后,绊倒于地,勉力爬起,追其而去。话说小东上京,得祸王接见,入拜魔教,回来之后便心情激昂,口放狂言,要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适时风雨大作,阴云聚集,街上之人,纷纷入内躲雨。唯独小东一人,一路奔走,口中呼喝:“祸王万岁!革命!斗争!”
奔至海边,攀岩而上,鲍氏追爬不动,风雨之中,连连呼喝:“小宝!快下来!小宝!”小东爬至山石之间,对着暗黑大海,高举赤书:“向着美好新世界,进发!同志们,革命!斗争!”海潮汹涌,鲍氏之声早被淹没,呼喊无用,眼见一个大浪袭来,小东身形摇晃,不知闪躲,张开双臂,呼喝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间天堂,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忽然,巨浪席卷,眨眼之间,再无人影。
“小宝——”鲍氏惊喝一声,撕心裂肺。勉力爬上山石,可怜孩儿早已被海浪卷走,只余一本赤书,夹在石头缝中,任海潮来回冲蚀。(待续)
点阅【天地清明引】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杨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