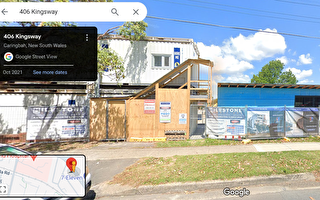【大纪元2020年09月09日讯】【编者按】澳洲仅剩的两名驻华记者上周遭警察约谈并被禁止出境,二人躲进澳洲使馆寻求庇护,后在外交官的斡旋下才得以安全脱身。紧急撤离后他们于9月8日早晨安全抵达悉尼。《澳洲金融评论报》记者史密斯(Michael Smith)自述了事件经过。以下为悉尼记者站对史密斯故事的编译。
当中共的情报、安全和秘密警察机构官员敲响我的门时,已是午夜过后了。
沉重的击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我急忙跑下楼,以为一定是朋友或邻居遇到了麻烦。
相反,六名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穿着制服的警官和一名翻译挤在我房门的前廊上。最前面的那个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问了我的名字并要求进门。
他们将我带到我的休息室,在那里我穿着睡裤坐在沙发上,周围是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一位官员用一台大型摄像机给我拍摄了照片,聚光灯的光刺激着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像家庭演播室。
虽然我无法记得(他们)用中文读出,然后机械地翻译成英文的三页陈述中的每个词,但总体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案件的受关注者,而我将不被允许离开中国,直到我回答了调查中的有关问题。
随着他们的半夜造访,我经历了四天“过山车”似的体验。
根据澳洲外交部的建议,我原本已决定尽快离开中国,这情况是由澳籍(中国)记者成蕾在北京被拘留引发的。我已经打包好了行李,本打算第二天晚上乘飞机回悉尼。
事实证明,澳洲政府的建议是正确的。当警官在宣读那份概述中共国家安全法的文件时,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像成女士一样, “消失”在中国一个臭名昭著的黑监狱中。
10分钟的表演结束后,那个警官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签署他们刚刚宣读的声明。我还必须用指纹确认我的签名。
他们突然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我不会被拖到拘留所,我放下了心。我跟随他们走到屋子外面并要求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想要什么?我可以得到那些文件的副本吗?但是,我的要求被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消失在暗夜中。邻居家的长者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看上去很害怕。
如同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欢迎来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生活。即使你没有涉嫌犯罪,当局仍可以在半夜闯入你的家中,恐吓并骚扰你。这是一个被强迫上电视自白,并且有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监禁,然后才可以接触律师的国家。
这次的事件有两点惊人之处。首先,尽管外国记者经常被驱逐出中国,但这是第一次被禁止离开中国。
其次,此次事件是有安排的,同样的造访也发生在澳洲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伯特斯(Bill Birtles)在北京的公寓,七个人也出现在他家门口。
当时我们是澳洲媒体仅有的两名在中国工作的记者。此举显然是具政治性的。
我们都通报了澳洲驻北京大使馆。
毫不奇怪,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距我家五分钟车程的澳洲驻上海领事馆办公室。伯特斯被护送到澳洲大使馆。
我是乘坐带黑色牌照的领事面包车回家的,该牌照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外交豁免权,例如,如果中共安全官员想要把我从车上拽下来。
当面包车驶入我居住和工作的居所的狭窄车道时,就像是一部间谍电影的场景。我被告知,为了我的安全我要留在车里,一位外交官急跑进房里取我的行李,所幸前一天晚上行李已经都收拾好了。
当我们在等待汽车发动机运转时,一个戴着口罩的可疑男子在车道上走来走去,假装在打电话,他显然在关注着我们。
陪同我的领馆工作人员震惊而困惑地看着这情景。当我们的车启动离开时,我从后车窗向他们挥手致意,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做这样的道别。
接下来的五天,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竭尽所能让我感到舒适。在这后面显然有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我尚不清楚是否会取得任何进展。
我咨询了律师,我担心我什么时候应该告诉父母。由于必须绝对保密,因此我只能告诉少数人我的处境,以防新闻泄漏和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复杂。
多年来我曾抱怨过澳洲外交部的一些秘密行动,我现在意识到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不透露这条新闻给其他记者是很必要的。
The inside story of my last week in China. A midnight visit by security police, exit bans, consular refuge and the high stakes negotiation to secure our freedom. https://t.co/w2WJ5b5fc9
— Michael Smith (@MikeSmithAFR) September 8, 2020
第二幕戏剧场景
几天后事情有了突破,澳洲外交部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就一项安排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比特斯和我本人可以在我们接受问讯的前题条件下离开中国。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它要求我们信任中共当局,但令我们感到些许安慰的是,这项承诺来自很高层,此外也别无选择。
我的问讯于9月7日下午在嘉里饭店31楼进行,这是上海浦东新区一栋不起眼的高层酒店。澳洲领事馆官员陪同我去,但他并未被允许参加会议。
此前凌晨造访过我的两个“朋友”在休息室与我会面,将我带到有另外两名警察的房间。当我走在昏暗的走廊上时,一个念头很快闪出:我是否能出来。
但是,一小时的问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礼貌地问我关于我待在中国期间所报导的事件类型,与谁交谈过以及与其他记者的关系等问题。他们问我是否认识成女士。鉴于我和成女士从未讲过话,我的信息一定很令人失望。
当这第二出戏结束后,我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通往自由之路的最后冲刺是一位领事陪同我前往机场,在那里我遇到了伯特斯和一群澳洲外交官。限制我们离开中国的禁令一直没有取消,直到对我的问讯结束,离航班起飞只剩几个小时,中方才取消禁令。
关键时刻是清关。
我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是海关官员敲下公章的声音。领事人员一直陪同我们到登机口。
尽管飞机升空时我感到欣慰,但在中国工作的近三年时间却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尾。我没有机会告别我的朋友,以及完成我一直在努力的故事,也没有核对过不断增加的游览地点的清单。
另一个恐吓演习?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是问题多于答案。
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中共当局拘留了成女士,或者为什么他们对两名澳洲记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
通常,中国的记者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写了一个令共产党头痛的故事。
有说法认为,这只是北京试图威吓澳洲政府的另一种做法。
这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澳洲首次在中国没有了通讯社。如果你不在这个国度,那么对这里就很难理解。中国还驱逐了许多美国记者,这对中国是有害的。
当我的航班于9月8日早上降落在阳光明媚的悉尼海港时,我由衷地感到这座城市前所未有地棒。
责任编辑:刘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