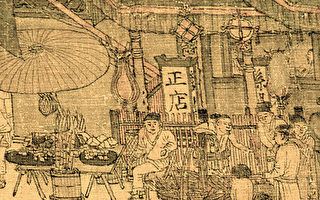年少时读《水浒传》,记得是在初一升初二的那年暑假。大热天里,每读到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痛快,心头涌起一阵激动,手臂上即显出鸡皮疙瘩。《水浒传》中的好汉全有绰号,绰号衬托人物个性,如响当当的“拚命三郎”,闻之令人热血沸腾;有的绰号让人唯恐躲之不及,如“母大虫”、“赤发鬼”。有趣的是,刚进初中不久,同学中竟也开始起绰号,但这与《水浒传》无关。
自然生成的绰号也有生命期,一经出笼即能存活。我进初中时,从家到学校,只须约半小时不足的行程。每天早晨母亲用铝制饭盒,给我准备好中午饭菜,学校食堂用大蒸笼加热。新认识的同学第一次在教室共用午餐,那种因新鲜感带来的愉悦,竟也终身难忘。当时没想到,同学之间绰号的问世,竟与午餐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我们那个年级共10个班,我在初一(9)班。时值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还是“老大哥”,学校从教室、门窗、讲台到所有课桌椅全是苏式:课桌与坐椅相连,桌面成一个坡度,上有一层盖板。上课时放下盖板,桌面随之扩大。课堂上起立或取书包时,可顺手翻起盖板。坐椅也不是平板,而是随臀部的轮廓形成小幅的波状。在一个新鲜的环境,大家一起边吃午饭边聊天,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也为绰号的生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起绰号仿佛也是一种艺术,因为绰号的存活必须获得大家的认同。某同学的绰号往往不是空穴来风,也许与他的个性、处境或经历有关,所以真实姓名也许会张冠李戴,绰号却不可能张冠李戴。有时候只要看一个人的外貌,绰号即呼之欲出。几年前我在小文《闲话饮酒》中,谈到绰号叫“大红鼻头”的少年,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其实“大红鼻头”姓唐,为人爽快好动,明显特征当然就是鼻子红,以至全班几乎没人喊他的原名,连性格内向的女生,也直呼“大红鼻头”,那口气是认真的,仿佛他生来就叫“大红鼻头”。“大红鼻头”自己对这个绰号早已默认,无论谁只要叫一声“大红鼻头”,他立即如条件反射般地应声:“嗳!”“大红鼻头”的本名唐□□,只有老师在课堂上偶尔才会点到。
另一同学绰号“三毛”,这个绰号不是创新,而是巧借。文革前坊间流传的三毛有两种版本,一是头上三根毛的大头儿童,是漫画家张乐平在《三毛流浪记》中创造的形象。另一个三毛,是上海滑稽戏《三毛学生意》中的成年三毛。我的同学三毛姓徐,在家排行也是老三,与张乐平的三毛无关,与《三毛学生意》中的三毛似乎有点缘分,只是年龄要差一大截。三毛与我很亲近,我们同年龄,在小学就是同班又是好朋友,他家到我家仅几分钟时间,小时候常来我家玩,母亲对他很熟。进中学不久,不知什么缘故,“三毛”这个绰号一下子就被全班公认,三毛自己不在意。升初二后,我在童年时居住的小街渐渐消失,我们家迁居到稍远的公有住房,三毛很少再来。
初一下学期,三毛把他家的《三国演义》带给我看。《三国演义》有古文成色,但明代话本的古文,比起唐宋古文,尤其比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古文,读起来容易。加之我在小学爱看“三国”连环画,对“三国”故事略知一二,大体能看懂原著描述的情节。书中许多细节脍炙人口,如“长坂坡赵云救阿斗”、“关公走麦城”等,我乐意讲给三毛听。下午的自修课,我和同桌女生也轻声谈“三国”。自修课轻松且无约束感,尤其是《平面几何》作业,根据已知条件求证,可自由讨论,偶尔也可走动,与课堂纪律的好差无关。如同中午吃饭,自修课上邻近同学之间轻声招呼,大多也用绰号,没人会大声喧哗。
我与三毛分手,原因是初二下学期,我们9班被学校拆散。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到4班,三毛好像分在7班,全班每人仿佛都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分手那天下午,其他班主任到我们教室,分别把我们带走,当时就有几名女生悄悄低头擦泪。学校为什么要解散9班?谁也说不清。刚进初一时,班主任是教图画的方老师。方老师擅长国画,尤爱画虎,会操京胡,估计那时年龄在40—50岁之间,却是一派老先生的风貌。方老师秃顶,借助后脑稀稀拉拉的头发遮盖前额,鼻梁上架着眼镜,开口是夹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同学私下称“洋泾浜普通话”。全班最胖的同学姓沈,绰号“阿六”。阿六的拿手好戏是模仿方老师的“洋泾浜普通话”,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尊敬方老师,也喜欢听阿六的模仿。初二换了班主任,事先大家全无心理准备。新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女老师,姓曹。曹老师约30岁上下,波浪式的齐耳短发显示出几分时髦,普通话远比方老师标准且嗓音明亮。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及元素周期表,化学反应式,这些人名和知识,我在曹老师的课上开始稍知一二。“罗蒙诺索夫”这个名字从曹老师嘴里说出,似乎特别顺溜,让人听一次就能记住。后来知道,罗蒙诺索夫不仅是重要科学家,在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也有贡献。
9班解体后,大家都怀念曾经在一起的往日时光。有时晚自修,会自发聚一起,互诉对新环境的失望。女生尤其怀旧,每次聚会多是女生串联通知。师生之间仿佛讲究缘分,如同水土服与不服的道理一样。方老师的时候,好像全班没人愿意让老师操心,换了曹老师不久,调皮同学竟一个个地冒出,其中原因无法说清。9班的拆散,或许与此有关。三毛性格温和,课堂上插嘴不多,但每次插嘴必引得哄堂大笑,他自己却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有点冷面滑稽。可见“三毛”这个绰号对他而言,正是“号”不虚传。其实此类调皮与道德品行无关,就像婴儿的啼哭一样,潜意识仅在于引起注意。不同的老师,对此有不同反应。有的老师跟着同学一笑了之,有老师认为这是影响课堂纪律。正如曹老师个子稍矮,同学大多不在意,但也有同学背后给曹老师取了绰号:“矮子”,虽对老师有失尊重,但也谈不上恶意。
最有意思的绰号,要数“咱班的王政委”。初一时有一篇课文,标题就是《咱班的王政委》,这里的“班”是指部队的班。课文大意早忘了,此类题材我天性不感兴趣。部队里有师长、团长……也有相应的搭档——师政委、团政委。连、排不设政委,何况乎班!课文大概表达部队某班的例外,这个班也有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搭档——“班政委”。回到正题上,那时我们在学校的班长是女生,姓周。班长显然比我们灵巧懂事,从小学起就是当班长的料。无论方老师还是曹老师,都满意周□□这个助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又是谁为班长安排一个“政委”作为搭档?没人能讲清楚。
这个搭档就是“咱班的王政委”,当然“咱班”指的是我们9班。“王政委”的本名王□□,读音与“王政委”相近。一篇课文的标题,就这样轻易带来一个绰号。其实王□□完全谈不上作为班长的“搭档”,妙就妙在“搭档”与“搭配”的含义相近,但如果改用“搭配”,也许仅因其中一个“配”字,恐怕就把这一层纸给捅破了。这层纸没人捅破,因为大家明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于是全班男生在一起,不再呼叫王□□,一致改称“王政委”。三毛常爱用全称——“咱班的王政委”,只有“王政委”自己拒不认账。“王政委”越是不认账,大家越在乎这个绰号。说来好笑,也许正因为这个绰号的弦外之音,每当班长在场的时候,“王政委”总有点神经过敏,甚至显得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样子。离开后,立刻又谈笑风生,恢复嘻嘻哈哈的本来面目。加上那时在班上“王政委”的个子最高,两道眉毛像“八”字挂在脸上,笑的时候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只要班长不在场,“王政委”仿佛就敢肆无忌惮。凭心而论,班长性情温婉又兼通情达理。对于“王政委”这个绰号,虽好像与作为“搭档”的班长有点关联,然而班长的表现很大度,只当没有这回事。
还有个绰号叫“寡妇”,绰号的得主,是名为秦□□的男生,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是秦□□童年起与寡母相依为命,父亲早亡故。这个消息也许是在填写家庭情况表时显露,也许是他的小学同学泄漏。与秦□□从小学一同升入中学的同学姓韩,绰号“甲长”,这个绰号也是全班公认的。韩甲长刚进中学就是近视眼,这在那时很少见。甲长这个绰号的由来我忘了,好像是从小学带来,秦□□干脆把“甲长”当成原名,张口就是“甲长”。秦□□的母亲帮人当女佣,藉以维持生计。夏天的时候秦□□在街头卖棒冰,挣钱补贴家用。光明牌赤豆棒冰是那时大众化消暑饮品,4分钱一根。秦□□碍于面子,在学校小心掩盖自己的这段经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想想那时的同学,也实在不谙世事,用绰号“寡妇”加在秦□□的头上,确有点过分了。不过这个绰号没被多数人认可,只有部分同学玩笑时直呼“寡妇”。秦□□对这个绰号虽反感,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面呼“寡妇”的同学脱口而出,完全不像故意过不去。“王政委”谈起“秦寡妇”,也总是嘻嘻哈哈的样子。
秦□□虽家境寒碜,但在初中读书成绩居中上。尤其从小临写颜鲁公碑帖《多宝塔》,汉字的书写基础也优于大多数同学。然而自幼在一个贫困且又缺失父爱的环境里挣扎成长,因自卑而投射在心理上的阴影,与小聪明带来的自负混杂,负面影响可能终生也难消除。才读初中的少年,秦□□理发就开始享受吹风服务。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学校小卖部里出售糕团点心,有条头糕、赤豆糕、松糕……,秦□□几乎每天不落,也许就是为了抵御歧视,向同学证明“我不穷”,全然不在乎他母亲的含辛茹苦、家里生活的捉襟见肘,还有每学期领取助学金的窘迫。如此做派,反让大家对他减少几分同情,私下流露出些许无形的不屑。秦□□可能已感受到,不久理发再也没有吹风,第二节课后买糕点也不再踊跃。9班解散时,秦□□分入几班我忘了,高中和我又在同一学校,虽不同班,与我的友谊却进了一步。以往的日子里,我对他从未呼唤“寡妇”。于是高中那段时间,他向我透露家里的私密——他的父亲是在政权更换时期去了台湾。庆幸的是,9班解体后,“寡妇”这个绰号总算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有关绰号的往事,与9班短暂的历史连在一起。初中毕业大家离散,5年后文革爆发,此后当初的同学再也没有相聚。谁料岁月沧桑,大家虽天各一方,却共同经历了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转眼间一个甲子已逝,暮年又同时遭遇病毒肆虐与封城之痛。以往的绰号当然不会有人再提,三毛、王政委、韩甲长……也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三毛、王政委与韩甲长了,但9班与绰号有关的那些往事,每个人都会永远珍藏在心里。@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