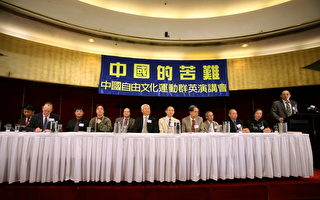【大纪元12月8日讯】这个题目是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这里概括地向大会作一个汇报,把汉字简化这个涉及民族文化的重大问题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和清算。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大家知道,自从电脑输入汉字成功,汉字书写已经根本改观。任何一种输入法,不论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与笔画的多少不再相干。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就开始的简化运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将近两千年基本稳定的汉字系统,未经全民族的充分讨论协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突然改换。凡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士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实际上是一场强制的非科学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简化字有什么坏处?
五十年代中学毕业就可以诵读古迹中的碑文、对联,现代中国青少年非经训练无法阅读古旧书籍,看不懂港台小说和文件。
简化字方案归并了异体字,只是减少了少量汉字,可是对历史文化总量来说,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简化字。古代文献不能抛弃,需要一套检索系统,简化字不能使用这套系统,另搞一套检索系统。结果在所有的正式图书馆都必须拥有两套检索系统,管理人员和检索者都必须学会两种检索方法。从北京、上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无一例外。精力和经费的浪费无法统计。
简化字胡乱尊重所谓的“群众首创精神”,违背了汉字原有的音韵系列和偏旁规则。例如“进”读jin ,繁体是谁字一半加走之。简化成井字加走之。井字不念jin 而是jing. “这”字里面是言字,应该简化成统一的言字旁一点一横再直向右勾,或者不用简化,这字也不算难。可是却简化成“文”字加走之。不合规范,增加了混乱。这类问题并非个别。
简化字立民间不规范书写形式为官方形式,首开恶例,造成各种不规范书写在社会上的恶性泛滥成灾。
电脑汉字系统也装备两套汉字系统。繁简转换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同音替代的词就会出现错别字。凡是用中国大陆国标码输入,又在海外印成繁体的文章出现了一套特有的简繁转换错字。许多描写旧时代的影视节目不断出现简繁对换的错字笑话,令海峡对岸的知识份子错愕不已,甚至在北大百年的纪念册上则是错字连篇,竟无觉察。
简化汉字造成了两岸人民文化上统一的隔阂。数千年书同文的中国变成了不尽同文。海外的中文学校很难统合在一起。无论欧洲、美国、日本和澳洲,没有一个地方的中文学校能把两岸的学生家长和教师统合起来。港台青年不愿意主动阅读大陆报刊和网页,大陆青少年更难阅读台湾网页和文献。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功勋卓著,那么共产党造成一国两字,分裂文化阻碍统一,该当何罪?
文字的功能是读写两用的。如果简繁都认识,阅读一样快。而且任何人都是阅读大大超过书写。简化以后,增加了辨认的困难,例如设和没,计和汁,造成笑话:“本店设有充电装置”,被读作“本店没有充电装置”,“我没法去办”和“我设法去办”,很不容易看清楚。
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
毛泽东决定方向,周恩来主持简化汉字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中国的历史文化好像被毛泽东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孽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昭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简化无助于快速认字
为简化字洗刷的人们多半说,“简化字简单,认字能快一些”。这是中国社会愈百年来的重大误区。随着电脑的进步和应用,人类的认知(习得)心理逐渐明朗。根据认知心理学的探讨,人类大脑的学习有些类似于电脑,当然比之更加灵活和迅速。实际上一个字无论繁简,它的音、形、义,都要通过视觉、听觉,发声器官和大脑的理解反馈多次,才能建立记忆。字形,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图像被传输,繁体字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简化字也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视线扫描的面积也是相同的字形方块。简化字的空白虽然多一些,可是视线扫描并不能忽略这些空白,空白和笔划在传输信号意义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号。所以简化字和繁体字建立记忆的过程是一样的。汉字不容易记忆的问题,简化字并没有解决。大脑的记忆不是机械地专注于笔画的多少,而是概括地掌握一个方块字和另一个方块字的区别。心理记忆中不在乎个别的笔画,却认同固定的模块(例如边旁或固定搭配),所以把言字旁变成“言”,把报字原来的幸字旁改成“手”,在心理习得上丝毫不减省心力和时间。减少了部分笔画,汉字认读的心理过程根本没有简化或易化。
极端地说,在方块字中三笔两笔的字,大概总是比二十笔三十笔的字好认。但是从实践上说,三到五笔的字不可能太多,多了也易于混淆。一般在十多笔左右才能组成形态各异,又适合习得的汉字。汉字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为了少数难写的相对冷僻的汉字,去改变大部分的边旁,进而改变了整个的正字法系统,实在是得不偿失。简化对于认字没有帮助,最雄辩的例证就是小学的学制依然没有削减,仍然是六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各地学校教育实践的结果,不由个别领导的意志而转移。
简化字并没有提高书写效率
简化字能否提高写字的效率,也是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重大误区。汉字简化了,写字就比以前简单了,快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现在电脑输入已经十分普及,大陆的五笔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输入速度都超过了同量字符的英文输入。说提高了写字效率,是假定每个人都是一笔一划(全规范型)写字的。其实,除了小学生,只有写招牌、画广告的工人才一笔一划地写字。一般到了高小阶段,就开始连笔带草了。在实行简化以前,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地区,都已经流行着不太统一,却大致差不多的简体字,当时称为“俗体字”。其中如“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风、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字跟今天的简化字一样。1935年国民政府曾经颁令试行简化字,公布了324个简化字。不久因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戴季陶等人的反对被饬令收回。当时的上海文化界还在民间推行过简化字(手头字)运动。而且汉字历来就有草书和行书在民间流行。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他的方言口音难懂和草书字迹难认,引起陌生师生不悦,刚好证明了当时民间的书写情况。但是毛此时此地行为是不对的。书写图书馆卡片、签条应当严谨、易认为好。行草笔画给民间书写提供了较高的效率。比如明白的明,日字旁边仅仅弯上三道,新鲜的新,一点一横折再上弯斜出,上绕一圈向下甩出。这类行草简字有的减少了笔画,有的仅仅改换了笔顺的方向,并一笔连成,加快了速度。例如州、每、四等等,类似的行草简字还有很多,当今规范简化字总表并没有包含。实行简化之后,不断强调规范化,这类民间简字反而被认为不规范,客观上抑制了它们的继续流行。所以推行简化字以后,已经确认的简化字被纳入规范字,没有确认的民间行草简字反而受压抑而萎缩。尤其是课堂笔记或是会议笔记,历来都是十分个人化、实用化的,可以大量使用民间行草简字。所以,从民众书写的总效率来看,推行简化字以前人们的书写速度并不比简化后慢。请看潘汉年的题词。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请海峡两岸学历相同的朋友一起听写,约定不要求工整、规范(可用俗体),只需要快速、可读,文章“中性”,不带有任何一方的冷僻词语,听写的结果往往就是一样快。
仅仅在小学生习字的阶段,每个简化字可以少写若干笔。根据国家语委的统计,简化字从过去平均十六笔,减少到十点三笔,节省了五点七笔。一般文章并非全部是简化字,所以按一半计算,大概平均减省了两三笔。实在可以说微不足道。而且从民族文化的深层角度来说,幼年学童在汉字书写上稍微多花一点功夫,认识边旁和组合,注意搭配和间架,是对祖国文化基本功的一种操练,一场入门热身活动。
汉字是落后、难学的文字吗?
汉字落后、难学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最早来自欧洲那些半路出家学习汉语的语言学家。黑格尔甚至描写汉字是“聋子的阅读和哑巴的书写”。带着西方人自视优越的傲慢。中国经济落后,派遣留学生出洋,这些学生就开始追随西方学者的说法。钱玄同和赵元任是代表,鲁迅和瞿秋白甚至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以及类似的恶言恶语,只是重复他们的想法而已。然后苏联开始注意中国革命,以吴玉章等人为代表的文字改革人物跟随苏俄共产党派往远东华侨社团和派往中国的干部一起,接触华工中的文盲半文盲,接触中共党员,浩叹汉字难学、落后。在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成人教育,又遇到扫盲的困难,觉得汉字太难。1949年以后,大批共产党的文盲半文盲干部走上各地的领导岗位。面临严重的困难,自然叫苦不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西方半路出家的语言学者、苏共干部、旅俄华工、根据地农民和进城老干部都是青少年时代错过了学习汉字的机会,成年之后才来学习汉字,事倍功半。正是这些人最强烈地痛恨汉字,难写难认。启蒙教育在任何民族都安排在幼年,是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以德国华侨为例,现在许多中国移民德国立足之后,将十来岁的子女接来团聚。按理说德文是世界上拼写相当规则的文字,能说,大致能读出。可是这些孩子一般都能掌握会话,文字能力则悬殊极大。很多孩子就是有语文障碍。英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英文的言文不一致,几乎跟汉语汉字差不多。也就是说,言文一致的拼音文字也跟汉语文一样很难学。德国全科中学Gymnasium的德文课程一直上到七八年级。拼音的德文就容易学吗?汉字难学难记,但是一旦记住,就没有变化,终身受用。西方文字英文人人都知道拼写太不规则,德文和俄文堪称最言文一致,但是也有很多听写陷阱。词内屈折、词尾、音变、性、数、格都有变化,还有种种例外。这些语言变化都要表现在文字中,所以掌握外文也绝不容易。26个英文字母、33个俄文字母学起来不难,可是离开学会英语、 俄语却差得很远呢。
将文盲现象怪罪于汉字繁难是不公平的。两岸三地的实例不言自明。海峡对岸没有实行汉字简化,注重教育,不到三十年,约在70年代末基本消除了文盲。香港长期被称为文化沙漠。旅欧港人文盲比例在七八十年代很高。香港1974年实行义务教育制。现在的中青年港人已绝无文盲。香港学校教学也没有推行简化字。中国大陆简化了汉字,赔上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半个世纪过去,仍有文盲八千七百万(2004)。现在在欧洲的中国难民文盲绝非个别。他们回答为什么不识字的原因,都与汉字难学无关,几乎全是社会性的:要么是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入学;要么是(文革动乱)没有老师没有学校。再过十年,成年的中国人文盲大概要说:“因为教育产业化,上不起学”了。总之,文盲现象跟汉字的繁简没有关系。关键还是社会环境的安定,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台湾的教育预算高,师资阵容强,政府善待知识份子,鼓励人民尊师重教。我们的教育落后,恰恰是土改摧毁了农村的文化根基,运动整肃了城乡知识份子,发展军备和核武器,压缩了教育经费,政治严重地干扰了教育,几代人积重难返。
汉字简化与共产党的关系
每当提出简化字有害无益的时候,总有人指责说是港台人不懂简化字,不懂简化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大陆人早就有人提过意见,可是凡是反对简化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简化的最初想法的确不是共产党人提出的,但后来也跟鲁迅、瞿秋白、吴玉章等共产党人有了关系。真正实行汉字简化的完全是共产党。这个历史责任是要有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承担的。文字并不是不能改革。俄文经过了改革,德文改革现在仍在争议中。伦敦也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拼写改革协会,鼓吹英文改革。问题是要不要采用政治运动的手段, 要不要实行民主决策,听取人民,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建议和反映,能不能说改就改,不经过试点和研究讨论。一个党和几名干部能不能决定全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工具的命运。
汉字简化是1955年1月提出草案,10月文改会通过,1956年2月1日起全国推行。以后又公布第二、第三方案。到了1957年发生了整风鸣放。共产党为了引蛇出洞,组织高级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鸣放。共产党员邵力子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章)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罗隆基发言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开展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章伯钧说:“将汉字改为拼音我是怀疑的。但是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鸣放不久,惨烈的反右斗争,至少五十五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受到各种严酷的处分。1958年2月3日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作文字改革的报告时,特别指出:“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简化汉字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时,吴玉章直接点名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的鸣放讲话“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污蔑”。这些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白纸黑字说明共产党分明是把文字改革作为政治斗争来展开的。因为文字是全国人民都使用的。所以除了文字改革,任何其他专业都没有如此的殊荣,在人大点名批判。章罗两位是中国最大的右派分子,至今没有获得“改正”。他们被打成右派当然远不止是因为汉字简化和拼音。但是反对汉字简化也是诸罪并罚中的一项小罪。另一位名人就是新月派诗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学研究员陈梦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出“文字改革要慎重”。文革中他作为右派不堪折磨自杀身死,夫人翻译家赵萝蕤精神失常。另外国务院文改会干部李涛也因对文字改革发表不同意见,被划成右派。其余各地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讲师、教授、机关干部因此被打成右派今天已无法统计。五十年代共产党人急切推行文字改革绝非偶然。实质的背景是当时干部队伍教育程度的先天不足。部分中低等教育程度的干部“调干”深造,但是大批文盲半文盲仍然需要安排工作。大批以大老粗自居,不肯下苦功脱盲的老革命进入各级党政军领导岗位,从行伍到行政,水平与权力比重失衡。普遍产生矛盾导致心理的焦虑和躁狂反应,折射到文化政策上,就是仓卒推行文字改革。甚至逼使高层接受拼音替代汉字的想法,把简化当作权宜之计。
共产党有权进行这样的民族文化决策吗?
汉语汉字是全民族的文化载体。共产党夺取了大陆政权以后,至今没有统一全国。当时还有大批学者专家避居台湾、欧美、日本。在大陆搞一些在“党已经决定了”的前提下的讨论,完全是过场做秀,没有代表性。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战争,全国和平统一,让全国人民和专家学者自由讨论和协商,汉字简化恐怕未必不能获得通过。因为当时胡适、赵元任、周作人等人都还健在,他们都会支持改革。同时钱穆、胡秋原等人也都健在,他们会提出许多反面意见,胡适、赵元任、陈梦家这些赞同人士也会提出批评建议,这样的对立可以形成制衡,使文字改革不会这样仓促,不会从文改会通过仅三个月(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1日)就开始全国推行。德国的文字规范化改革从政府主导列出方案几乎实行了八年,还没有定论。其间经过宪法法院的裁定,获得合法性;并邀请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的专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不断收集中小学校教学反映。至今仍然受到著名作家和部分报刊的抵制,学者更提出大量改革方案的漏洞和缺陷。中国的文字改革到了整风时期,大概十五个月,正是接受反馈,改进调整的时机。可是一场惨烈的反右斗争将任何讨论的气氛都驱散了,除了服从没有选择。如果1956年的简化被批评讨论延宕下来,只要拖过十年,遇上文革动乱,就彻底被搁置了。动乱之后,人们敢于讲话,如同简化字第二表那样,遭到抵制,电脑普及和中文输入接踵而至,这一场民族文化的劫难就避过了。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汉字简化运动实质上是一个文化浅陋的武装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后,对民族文化实行的一场强制性媚俗整容。简化运动对扫盲无甚帮助。1964年中国文盲两亿三千多万,占人口33.58%,文革后改革开放,1982年文盲两亿两千九百多万,占人口22.81%;2005年文盲率才降到了8.33%。
文革浩劫诛杀功臣、迫害文人,但是与历代的情形颇多相似,大部分中国人不再能阅读古代文献,今天,中国的文字局面已经出现类似焚书坑儒之后的“古文”和“今文”的时代。而跨越世代的语言文化伤害将比仅及一两代人的身心伤害更加痛楚,更多遗憾!而且时间愈久,伤痛愈深。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要不要恢复繁体?
既然简化得不偿失,要不要恢复繁体?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关键还在于我们的国力。英国这样的小国,改行公制度量衡,耗费的财力非常巨大,牵扯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民族历经劫难,专制政体尚未结束,能否经得起再次的波动?对于这样重大的民族文化决策,再也不能凭一两个人脑袋一热,就全国推行。非经人民讨论和专家协商,基层试点和征求意见,不可轻举妄动。
如果可能,只要两岸政通人和,携手合作,由于电脑逐步普及,要恢复正体汉字系统,重续文化源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发自内心的呼吁仍然是希望我们祖国的民族文化不论遇到什么新的问题,重大决策都应采取民主的方式,让人民和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和酝酿,再作裁定。
2006年11月13日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