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百万右派中,尚活在人间的那些人已经做了十九年贱民。其中相当多还在他们“就业”的劳改农场里等待生命之灯枯竭、熄灭。已经回到社会的那部分也还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直到两年后中共才决定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予以改正,并于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决议,公开承认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1: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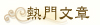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两句诗,可以用来说明反右风暴尘埃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百花齐被吓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热闹的鸣和放在知识份子心头只剩下了痛和苦。
 2005年7月9日 11:35 PM
2005年7月9日 11:35 PM 反右高潮中,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真死也罢,装死也罢,对这些命如蝼蚁的小人物,毛泽东是不存怜悯之心的。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2005年7月8日 9:57 PM
2005年7月8日 9:57 PM 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个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入干涉。”
 2005年7月7日 9:32 PM
2005年7月7日 9:32 PM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公布后,谁也不再提共产党整顿作风的事了。尽管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过不要求各党派整自己的风,各党派还是安静下来,各自回窝,整自己的风去了。
 2005年7月6日 10:47 PM
2005年7月6日 10:47 PM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运动”定下了甚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2005年7月4日 4:59 PM
2005年7月4日 4:59 PM 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无数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狱。
 2005年7月3日 11:16 PM
2005年7月3日 11:16 PM 一九五七年落网的右派分子,几乎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和共产党中的知识份子干部,一一列举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论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举若干事例。
 2005年7月2日 9:38 PM
2005年7月2日 9:38 PM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2005年7月1日 10:57 PM
2005年7月1日 10:57 PM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2005年7月1日 12:07 AM
2005年7月1日 12:07 AM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2005年6月29日 3:14 PM
2005年6月29日 3:14 PM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2005年6月27日 11:59 PM
2005年6月27日 11:59 PM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2005年6月25日 1:06 PM
2005年6月25日 1:06 PM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2005年6月24日 12:52 PM
2005年6月24日 12:52 PM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2005年6月23日 12:04 PM
2005年6月23日 12:04 PM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 ,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2005年6月22日 3:39 PM
2005年6月22日 3:3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