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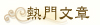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空山诗选》是一个手抄孤本且内容多为当局所不容,故首先在成都的朋友间传观时,就严格限制外传;若需转抄一律使用作者认可的化名。朋友中间转抄得最多的是吴鸿、杨枫、罗鹤、熊焰等人。当时,陈墨尚在盐源,白水已返甘孜,张基仍滞喜德,阿宁、峦鸣、长虹长困荥经。这些友人飞鸿传书得知《空山诗选》已经搞出却不得一见,恨得牙痒痒的。阿宁来信说:“行行好,明年新年探亲,请务必将《空山诗选》带来让荥经诸友一睹为快。”我顾虑太多,不敢遵命。
 2004年8月20日 5:38 AM
2004年8月20日 5:38 AM “全国山河一遍红”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爷爷”被赶下了乡,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网”也越收越紧。我已是成家之人,不得不四处找临时工做,只要有活干,脏累都不怕,能挣钱养家糊口就行。陈墨属无业闲杂、东飘西荡、总感觉被“网”住了,决意邀九九一起到西昌盐源县插队落户。1970年3月1日晚,是一个“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日子。我和徐坯、罗鹤、冯里、杨枫、云朗、祖祥、伯劳、黎明等10多人,聚在浆洗街办事处所安排的武侯祠大街一家旅馆里,为即将上山下乡的陈墨、九九送行。大家挤在一个房间内,分坐在两间床上,亮灯夜叙,或慷慨高谈,或激昂阔论,或轻声叮嘱,或掩面暗泣,坐待天明。3月2日晨,一群人浩浩荡荡从旅馆出来,步行到浆洗街办事处大门外,送陈墨、九九登上一辆带篷的解放牌货车。汽车开始启动,陈墨忽然从车内人丛中挤到车后挡板前,大声地向诸友挥手说:“再见了!”一声未了,他已是泪流满面。送行诸友受其感染,竟哭声大起,响成一片:“哭声直上干云霄”,尘埃不见万里桥。我于当天一气吟成一首《送友人赴山中》,又于第2天写了1首《似水离愁》。
 2004年8月14日 9:03 AM
2004年8月14日 9:03 AM 1966年7月,“文革”运动已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由“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大搞打、砸、抢、烧“破四旧”的阶段。我在雅安,被单位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难保,“天兵天将”们又几次上门查书收书,随身带来的一箱书籍也已被收缴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陈墨却偏在此时突然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书,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艺书籍。其中有一本残破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北极风情话》,显然是一本禁书。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陈墨一生喜书,无奈家贫,藏书寥寥,忽地将其全部“家当”给我寄来,肯定处境比我更糟,但这样做于他是损,于我可是祸呀!我无计可施,只得将这包书付诸一炬。
 2004年7月28日 8:29 AM
2004年7月28日 8:29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