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暗中苟且求生的民族,一个千疮百孔、遍地冤狱、民生凋敝的中国,一颗新星,在宦海沉浮中拼搏了半个世纪的胡耀邦终于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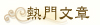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在窒息了三十个春秋的中国,星星的作品,震撼灵魂!特别是汪克平的许多木雕,其中《沉默》表现的正是中国人做人的现状,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2004年3月,我在美国参加纽约《汪克平艺术作品展览》的开幕酒会。在曼哈顿“SOHO”,欲匆匆从纽约离美回国的我和急匆匆从巴黎赶到纽约的汪克平,是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第二次握手!世事和人生恍如隔世,像是在阴阳界上,感概万千。
 2005年12月12日 4:15 PM
2005年12月12日 4:15 PM 1975年夏秋的台风季节刚过去,革命委员会又刮起了强大的红色风暴。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抓进变相的集中营。专政工具们以革命的名义,大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我刚出差在上海,从电话里我得知:打办人员抄了我们工厂,拉去生产原料,使我们企业停产倒闭。我清楚这是县工交局长蔡继卓对我们的报复。我不能沉默了,唐吉珂德对风车的宣战,即是我此时心境的写照。我从上海打电报给县政府,列举蔡继卓的种种罪行。电波的传递,如爆开的炸弹,在海门和黄岩的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动用了一切专政的工具,向我围歼过来。
 2005年12月10日 10:01 PM
2005年12月10日 10:01 PM 冬去春至,大地开始裸露出她那茶绿色的胸怀。我骑着白马,驮著一个大包裹,怀抱着一个镶著银子图案的马鞍,去公社送还展览品。
 2005年12月8日 11:51 PM
2005年12月8日 11:51 PM 他是乌鲁木齐市有色局的干部,住在一间平房里,他为我铺了地铺,我住下了。第二天他给我办好了"身份证明",由其单位盖公章以他自己作为我的担保,证明我是个良民,使我顺利地在乌鲁木齐安置处报了名。和我一起录用的人将分派去北疆的富蕴县温都哈拉良种繁育场工作。多么动听的名字——"良种繁育场",一种诱人的新生活在向我召唤。我赶回去谢谢他,留给他几幅速写作为纪念,连他的名姓都忘了记,就这样匆匆告别了。
 2005年12月7日 10:38 PM
2005年12月7日 10:38 PM 一件事,让我重新正视起现实来。著名油画家于长拱自杀了。苏联油画大师马克西莫夫的门生,大白天躲在被窝里用刀片割断喉管,求得对尘世的超脱。
 2005年12月6日 4:22 PM
2005年12月6日 4:22 PM 忘不了那个寒冷的早晨,小镇街道的墙上刷满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标语。一种内心的惶惑:我的姓怎么会和这可怕的文字连在一起……
 2005年12月5日 10:31 PM
2005年12月5日 10:31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