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已远离我们的视野,消失于人们内心世界的或狂躁的、或荒唐的、或疯颠的标语,我竟然还在南方乡村偶或见到。“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话我在广东清远和福建泉州官桥蔡资深民居群里都曾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话则是我从湖南宁乡万寿山一处民房墙壁上看到的,估计是口号满天飞的“大跃进”时代残留下来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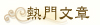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在福建长汀,毫无来由的,一扇土墙撞入了我的眼里。或者说,是我四处乱转 的眼珠子撞到了那扇墙。因为这扇墙,这本书就多出了以下一截文字。 长汀古城镇那扇土墙很苍老了,可我没去打听它究竟历经了多少年月。我所关 心的是,同一面土墙上出现的三条标语很有意思。标语如下:“毛泽东思想万岁!” “福两全保险,分红保障两皆全。”“全民齐动手,奋力奔小康!”
一个城里人偶尔下次乡,他会乐得忘乎所以。把农村夸得似乎到了爪哇国: “桃李树下走,鸡狗伴我行;喝点农家酿的米酒,尝点农家种的菜蔬;再跑到鱼塘钓只王八……美哉胜神仙!”
喝农药确实是农村人选择自杀的最常见方式,不过有个人跟我说:“我要自杀 ,我就不喝农药。最便宜的农药还要花好几块钱呢。干嘛浪费那钱?我要死,就给自己身上绑块石头跳河……”
我有个朋友名叫邱贵平,福建作家,中短篇小说写得很棒。现在他却开始将小说创作放到一边,去琢磨农民大大小小的问题了。他写了篇杂文,痛心不已问:农民,你为什么爱喝农药? 是啊,农民为什么“爱”喝农药?实际上,农民不仅仅是“爱”喝农药,还 “爱”悬颈,“爱”跳河跳井……总之一句话,农民好像很“爱”自杀,而喝农药自杀却是他们的“最爱”。
问一万个乡下人,你希望拥有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是什么?九千九百九十 九个人会茫然无措看你。农村人的悠久习惯是:小病不理,中病久拖,大病犹犹豫豫去看医生,绝症和重病——对不起,等死!
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个别乡村跑一跑,你会发现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这些地方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为躲避有关部门的追查,他们往往是倾巢而出一窝蜂跑城里去了。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工业蓬勃发展的珠三角城市里,三五步就可能见到潮汕人开设 的士多店(小小杂货店)。他们宁愿在城里吃苦受熬,也要坚持不懈地猛生孩子,哪怕已生了三个四个孩子,只要是女孩,他们仍难以甘心,不生一个带“小棒槌”的男孩绝不肯罢休。而即便没逃进城里,而守在村里生孩子的妇女,因为不少农村基层管理机构采用“只罚不管”(罚款了事,不严厉制止)的措施,超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民工进城要在城里站稳脚跟,得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这些是看得见的证件支出,看不见的是意外支出——我敢打包票,进城打工的众多民工也许都遭遇过不同性质的敲诈勒索。要么是保安大哥、要么是难辨真假的警察叔叔、要么是个别社会渣子人员……反正多少得被强迫着支出一点子不想出但又不得不出的钞票。
乡村小妹们本来与“黄祸”无关,没有一个乡下女孩当初是扛着“小姐”的大旗进城的。但当她们在上当受骗之后,在走投无路后,父母的教诲就在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显得挺苍白了。任何城市,无论法制部门的口号喊得多么强烈,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总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现,性产业严重“超标”。而这些从事性产业的女孩,也确实有大部分来自乡村。失业的农村女性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驱使下,蜂拥进城来谋求个人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里阳光灿烂的大多数“机遇”没她们的份,城市却又将她们扔进了阴暗灰色的命运底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将所有“小姐大军”来一通迎头痛击,却不去探求性产业兴盛而无奈的“来龙去脉”,只能算是社会冷漠者的行径。
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句老话,但在而今的农村,仍能经常听到。这话,难免被众多的城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很懂得读书作学问的重要性。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乡下人有种传统的意识: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粪。
在乡下与人攀谈,问起他们心里最想望的念头。“啥盼头?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万事满意了。还有,儿女能读上书,以后比我们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这话,或与此大致相彷的话,我至少能每天听到5次。在中国总人口数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农民,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并不高啊,温饱无忧身体好,希望儿女有出息就够了。
41岁的蔡关说:“正月初三就出门,走路出村,坐汽车到长沙,再赶火车。打工苦啊,要是家乡富裕,谁愿抛妻别子去打工?”蔡关是湖南益阳土生土长的农民。26岁南下广东韶关打工,后来赶上南方城镇狂卖非农户口,靠多年在韶关工作的叔叔帮助,蔡关用钞票使自己摇身一变为“城里人”。接着,艰苦奋斗几年后,他主动下岗回到了家乡。再接着,用多年打工收得,凭在城里增长的见识,再筹措资金开了个规模不小的砖窑厂。




 2006年10月11日 7:38 PM
2006年10月11日 7:3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