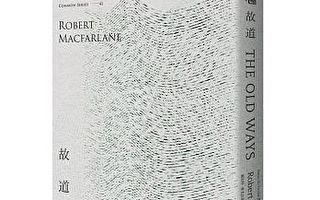无论恩典来自于你的上帝或是我的老天爷,在这世界上,总会有光。
即使在阴暗的角落,也能在隙缝中感受到随着光线穿透而来的暖意。
抉择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纽约市充满节庆的繁忙气氛。人行道挤满了人,商店橱窗妆点得璀璨亮眼,人们携家带眷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转。似乎人人都铆足了劲想让这段诡异而不幸的日子变得正常。我发现这现象很值得庆幸,但也很让人不安。
距离天崩地裂的那天已过了三个月,然而生活继续拖着我们前进,就像拖着绑在车尾的锡罐。这便是这个充满圣诞过后购物人潮以及到世贸灾变现场看热闹的人的群魔乱舞区——一台摔坏了、看不见的噪音制造机,只有我听得见声音——给我的感觉。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不是那对带着相机的年轻夫妻,不是那个把孩子扛在肩上的父亲,不是那个兜售世贸中心照片的男子。问题出在,对我来说,他们身处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一切都是虚幻,直到我通过世贸灾变现场的安检站。这时我终于能呼吸,这时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了归属感。
熟悉的卡车隆隆声和机具辗轧声取代了警戒区外的噪音。烤栗子的香气和湿水泥的味道在我嘴里混合,很快地将被不容置疑的腐败臭味所取代。朝着死者——不是你的亲人,而是别人的——走过去是相当奇怪的一件事。
更奇怪的是,唯有在这里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活着。这是在世贸灾变现场工作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大家累毙了,但充满生气。
工人们很气愤但没有怨怼,朋友与同事遭到蹂躏但没有被击垮。我在消防员的眼里、在警员们紧绷的下巴看见这些。不过,话说回来,才经过短短三个月。也许彻骨的疲惫还没真正到来,也许心还没全然粉粹——或者也许世贸灾变现场已经自成一个小岛,里头的居民说着一种秘密的语言。
在这里,大家述说着故事,不必担心遭到批判,或者得到充满好意却讨人嫌的意见。不必字斟句酌以避免刺激听者。没人会畏缩或转过头去,没人会要求我们融入一个期待我们做回从前的自己的世界。
禁区外面是正常状态,和照常过生活的人们。而栅门外也有着哀伤和勇敢的人们,存活者和一整个国家的同情怜悯。当轮班结束,我不舍地离开小岛时,我会为了那些从没有机会做抉择的人、那些我会为他们的破碎遗体祝祷的人,以及那些我鞋上沾着、肺里吸着他们灰烬的人们,踏步离开。
我在这里的临时停尸间——通常被称作T-Mort——担任牧师。这是一辆简陋的长方形活动拖车,一发现遗体和残肢,就会送到这儿来。这里是那些失踪者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站,地磅站。
在这里,遗骸被逐一登录、拍照、祝福。祈福是我的工作,当然也是在我之前交班,以及在我之后接班的牧师的工作。我们以八小时轮一次班的方式运作,组成一个持续不断的祈祷之轮,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转动。我们之间可以互换,也不分宗教。
我们在黑暗中点燃一支闪烁的蜡烛,提醒自己和别人,生命仍然具有意义,上帝并没有遗忘我们。当烛光被绝望扑灭——照例会有的情形——我们便怀着大无畏的希望,竭尽全力再度把它点燃。
我们全都是自愿到这儿来的——牧师、消防员、紧急救护技术员(EMT)、警察、建筑工人。光是这点便足以将我们紧紧牵系在一起。大家的理由各自不同。
有个消防员当天休假,可是他的兄弟还得值勤。当双塔倒下,他答应母亲一定要找到哥哥,否则绝不离开。搜索了两周,他找到一条带有他哥哥熟悉刺青的腿。一条腿。这也是他终于能带回家向母亲交代的——还有承诺的达成。
还有一名警员,从事发后就每周六天、持续不断地在遗址的同一个转角工作。回家后,他努力挡住的那些意象涌了出来,在他梦里萦绕不去。只有在世贸灾变现场,他的心跳才能恢复正常。在这里,他没有空闲多想他看到的东西。等这份工作一完成——如果真有完成的一天——他知道那些阴魂便会找上他。
我到这儿来——不只是世贸灾变现场,也包括停尸间——是我从不曾怀疑的一个抉择。双塔倒下的那一刻,我的心便已飞来了。两周后,当一位圣公会主教要求我到这儿来替他轮值夜班,我的其余部分便跟了来。我和其他神职人员一样很想帮忙。我想我比其他人感觉更适合这工作的原因在于,安宁病房牧师的工作让我对死亡有深入了解。能够参与救援工作——能够做点什么——远远凌驾了事前的深思熟虑。
感觉就像冲进黝黑的森林里去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在热血奔腾的当下,你不会考虑里面可能有熊或狼。一旦到了那里,工作规模的浩大,不知会发现什么东西的恐惧,还有迷失自己的可能性,以及埋伏在暗处的绝望无助,才终于一股脑儿向你袭来。
主教第一次派我到世贸灾变现场,是轮值午夜到早上八点的班。在正常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时段,我从纽约市北郊的住所开车只要三十五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然而,那天晚上,我知道在我抵达灾变现场之前的部分道路会被封锁。若是搭地铁,又不确定出站后距离现场会有多远。跳上车就像闭着眼睛跳下悬崖。我只能朝着大致方向跃下,管不了如何着地或者会在哪里着地。
我还记得,当我把车子开出车道,街道好安静。从后照镜看过去,街坊的房屋有如一整排巨大的婴儿床,所有居民都正安稳地窝在里头。那种牢靠稳固的感觉很让人安心——等我回来,所有一切和所有人都还会在那儿。我想像我的手指轻拂过每一栋房子,像是亲吻道晚安或者祝祷。但是我只轻轻说了声“明早见”,然后拐弯上了高速公路。
接着我开始想现实的问题。我担心该如何到达那里,还有通过警卫关卡时会不会发生问题。我也不确定这工作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但这时我还无法想像——更别提担忧——可能的风险或者各种长远的影响。我只是一头栽进森林里去寻找某种失落的东西,尽管我还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沿着罗斯福快速道路,我赶在遇上路障之前尽可能往南开。接着我把车停入一座二十四小时停车场,然后找到地铁站。
当我走下楼梯,通过验票闸门,站内静得可怕。我踏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引起巨大的回音,声音从昏暗的墙面弹回,宣传着我的到来。我突然惊觉到一个事实:我正在午夜里孤零零一个人走在曼哈顿下城某处的一个荒凉的地铁站里。
光是想到自己在地底下,我已经口干舌燥、心脏狂跳。双塔倒塌时数千人被挤压、埋入地里的画面永远铭刻在我脑海,我们都已经看过不知多少次了,惊骇的感觉依然鲜明。我感觉耳朵里的血液开始跳动起来。这一刻,我不清楚到底何者比较可怕——遇上抢劫,还是在又一次攻击中被埋在水泥里。而无论哪一种,似乎都眼看就要发生了。
所幸,终于有两道光束出现在隧道深处,后面紧跟着一路顶着两只大灯前进的列车。尽管我很庆幸我不是列车上的唯一乘客,里头的乘客却稀稀落落的。换作九一一事件之前的任一个夜晚,情况肯定很不一样。肯定有很多人准备在晚上出门找乐子,在街头艺人的音乐中快活地聊天。纽约的某些地区总是要到午夜过后才会真正醒来。如果这个时段连纽约人都待在地面上,那么我跑到地底下做什么呢?
我一直搭到列车不再前进为止。在距离世贸灾变现场几个街区的地方出站,我不可思议地失去了方向感。原本在这地区有着北极星功能的双子星大楼消失了。如今在黑漆漆的夜空中只有一个裂开的洞口。当我试着分辨方向,圣保罗教堂出现在我前方,而且四周有不少人走动,让我松了口气。群体力量和斗志旺盛的团结气氛在这时莫名地令人安心。
我顺利通过了安全检查站(多亏主教帮忙)。许多消防车罗列在围着警戒线的灾变现场周边,大批人员等着把从瓦砾堆送来的一桶桶碎石残屑传递出去。严重的挫折感正酝酿中。
位在中心的是一座数量难以估计、闷烧中的残骸堆栈。找到生还者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是它薄得就像圣体——你才刚尝到,它马上在你嘴里溶化。唯一留下的是那股充满期待的记忆,以及再尝一口的渴望。
接下来八小时,我到处听听走走、走走听听,尽我所能提供慰藉。这时心灵支援工作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也不清楚该期盼什么或祈求什么。最初,牧师的工作时程安排是由圣公会主导。攻击事件发生后,圣保罗教堂立刻敞开大门成立休息中心,数百名义工日夜不停地服务,准备食物、分送物资,为那些在世贸灾变现场工作的人提供支援。
光是这部分便是一项极为艰苦的任务。不时会有未经许可的人自称牧师,通过了安全检查站。其中有些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有些则是想趁机劝人入教。我不止一次遇见有人指着闷烧中的大片残骸,对任何听得见他声音的工人说,要是不接受耶稣作为救主,他们将会下地狱。或者更糟,还有人谴责那些在攻击中没有被救出、确定已经死亡的人。
这种情况绝不能再发生,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更紧密的组织。◇(未完,待续)
——节录自《让光照亮你的心》/联经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安卓雅·雷诺(Andrea Raynor)
毕业于美国哈佛神学院,为联合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医院牧师。自1997年起,她便开始担任安宁照护牧师,目前任职于康乃迪克州格林威治医院的居家安宁照护科。
责任编辑:李昀
点阅【书摘:让光照亮你的心】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