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时间里,黄伟被非法关押的时间达五年余。这,也是迄今看不到任何改变迹象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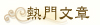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从七月十二日始,就尽早结束陕西省、榆林市及靖边县三级地方政府的非法、野蛮关押国内外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及其他十一名涉油经营者的局面,我及许志勇博士、滕彪博士、李和平律师一同抵陕北靖边县。
 2009年5月2日 11:36 PM
2009年5月2日 11:36 PM 上个月,我参加了几十家媒体在北 友谊宾馆召开的一个有涉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的研讨会,会后一记者问我此时想对政府说点什么,“当今的政府不做事,是对中国公民的最大善举”,我如是回答。
 2009年4月26日 7:07 AM
2009年4月26日 7:07 AM 我的面前摆放着三个已死去孩子的材料,其中的两个孩子的照片已在我的写字桌上摆放久时。仅照片即能证明十一岁的小男孩高棣的活泼、聪明及帅气。
 2009年4月22日 8:51 AM
2009年4月22日 8:51 AM 现在中央政府已明确规定,大学城不是教育事业,也就不是公共利益,法院根据广东省政府二○○二年一九七号文决定建大学城的文件来作为拆艺术村的法律文件依据。
 2009年4月17日 12:25 PM
2009年4月17日 12:25 PM 艺术村除了不定期的进行艺术交流外,还举办“艺术节”。近年已举办过两届“小谷围艺术节”(在行将举行第三届“小谷围艺术节”之际,官商合体者的黑手伸向那里),邀请国内及海外艺术家聚会,举行画展、观摩、交流。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2009年4月13日 8:16 AM
2009年4月13日 8:16 AM 被中外艺术界誉为与法国艺术家聚居地“蒙马特高地”媲美的广州小谷围艺术村已被广州市及广东省两级人民政府的恶行摧毁,但还未彻底摧毁。
 2009年4月10日 2:51 PM
2009年4月10日 2:51 PM 每个稍微有一点现代文明社会常识者都晓得,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律,那么,刑法对社会关系的保护及调整价值完全与聋子的耳朵之功效无异。没有宪政机制保障的《宪法》,与没有刑事诉讼法保障的实体刑法价值毫无二致。
 2009年4月5日 10:54 AM
2009年4月5日 10:54 AM 二○○四年九月,上海徐汇区朱钢等九位教师在联合署名的信中写道:“上海永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徐汇房地产迁有限公司 迁。
 2009年4月3日 10:49 AM
2009年4月3日 10:49 AM 黄老汉被摧毁前的家,距人民大会堂约三公里。就在黄老汉的房产被荡维废墟前的前几周,在人民大会堂里,近三千名人民代表激情难抑至雀跃,私有财产被纳入《宪法》的保护之列。
 2009年3月27日 3:01 PM
2009年3月27日 3:01 PM 一九九九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九岁的脑瘫病孩。
 2009年3月25日 9:10 AM
2009年3月25日 9:10 AM 伟毅案是我律师生涯中一起刻骨铭心的案子,当时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们在给孩子打官司的过程中的付出,今天讲起来我自己都感动,但社会给我的更多。
 2009年3月22日 8:59 AM
2009年3月22日 8:59 AM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点意思的,或者说从新闻的角度看有些新闻亮点的,都是为弱势群体打的一些免费官司,给受害儿童提供了一些无偿的法律帮助,其余都是经济官司。
 2009年3月17日 7:30 AM
2009年3月17日 7:30 AM 我曾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政府不做事是对人民的最大善举”,事实上,它们不去做事也是对它们自身的一种善举,它们不做事则已,做即全做愚蠢事,这也符合规律,即一群无理 、无道德、完全无自重意识者,亦仅能若此!
 2009年3月14日 5:11 PM
2009年3月14日 5:11 PM 又如,立法者完全认识到毁灭、伪造证据、唆使、引诱证人作伪证具有社会危害 ,应当受刑法罚责,但却只特别将律师列为犯罪的构成主体,律师据此被科罪者众,难道立法者能有律师以外的其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 的认识结果?显然不会荒唐至此,不难看出立法者对律师深深的歧视和戒备心理。
 2009年3月8日 10:17 PM
2009年3月8日 10:17 PM 袁红冰教授的文章引发我的感慨无尽,连我的夫人前天都不解地问,为什么你在国内有如此大的名声,却从来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来找你做律师。
 2009年3月1日 10:15 PM
2009年3月1日 10:15 PM 非常感谢袁先生对我的理解,形单影孤的独处、独行大致上算得上是一种孤独,但袁先生文中点到的我的孤独的内核是,我以我认准的方式去思想、去选择,这种思想及选择有时让人痛苦以至绝望,岂止是孤独了得。
 2009年2月24日 8:52 AM
2009年2月24日 8:52 AM 命运没让高智晟选择,从他律师执业第一天开始,就匆匆把他抛进了扶羸弱,护一方的角色。很难说这个角色对高智晟最终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维权律师要比其他的律师承担更为深重的道义,付出加倍的艰辛。
 2009年2月10日 4:26 PM
2009年2月10日 4:26 PM 九八年在乌鲁木齐,有一次高智晟回家交给耿和一笔钱,耿和一看都是零钱,问是怎么回事,高智晟告诉她:“当事人给我的代理费都是十块二十块凑起来的,那是他们的血汗钱。我的钱挣得越多,我的当事人的苦难也就越多!”
 2009年2月6日 1:59 PM
2009年2月6日 1:5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