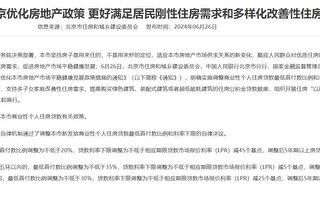【大紀元5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天光編譯/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2004年4月22日報導: Beijing crushes a student group–Beliefs tested in saga of sacrifice, betrayal)
2000年夏的一個週六上午,8位年輕人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一間簡陋房間相聚,組成一個討論中國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討小組。他們當中,有的是學生,有的剛畢業,都不過30歲。
他們當時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為一個共同願望,即讓自己的國家更美好。午飯後,由7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組成的這個小組在校園裡散步,沿一條綠色湖畔柳蔭下認真討論著國家的問題。
兩天後,其中一名學生在其大學的橫格信紙上記錄了當天的活動。
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李宇宙(譯音)潦草寫道:「我參加了一次「新青年學會」會議。」他記錄了聚會時間—8月19日上午10時—和與會者姓名。他描述了他們對政治變革的觀點,並稱有的人主張「暴力手段。」他補充寫道,他的朋友們希望小組活動保密。
隨後,他將報告交給了國家安全部。
三年半後,研討小組的4名成員被以顛覆罪判8至10年囚禁。兩人獲釋,但因在警察詢問中出賣他人而生活在恥辱之中。李則逃往泰國。 一天下午,他翻看著他過去寫的報告,痛苦地解釋起他為甚麼要當線民和出賣朋友。
天安門廣場屠殺近15年和蘇聯解體13年後的今天,中共在開展世界上規模最大或許也是最成功的權威主義試驗。「新青年學會」的遭遇使人對中共為維持其對權力的獨攬而採用的手段和身陷其中的人們所面臨的困難道義抉擇略見一斑。
研討小組的命運還說明中共在運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則之一時絕不手軟的程度,即視一切獨立組織為潛在威脅並予以粉碎。
「新青年學會」的8成員從未就政治綱領達成共識,也沒有任何資金來源。他們從未在其它城市建立分支或發展新成員。他們甚至沒再召開過全體出席的會議,總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們卻引起中國兩大安全部門的注意。有關他們活動的報告送達中共最高官員,包括負責國內安全的政治局委員羅干。據見過一份概述高級官員就該案所做指示的內部文件的人士說,連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都視該調查為國家最重要的之一。
領導層如此重視一個平民小組反映出其對權力的惶恐不安。儘管有人認為經濟改革必然導致政治自由,但中共還是實現了20年的迅速增長。 但它難以應對日益增長的社會緊張和大眾不滿,並對學生活動格外緊張。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就是學生運動引發的。
因此,中共迅速剷除「新青年學會」。在剷除的過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輕人思考他們願為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犧牲。
本報導是根據對「新青年學會」研討小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員、遭監禁人員的親朋好友和參加過小組會議的人的採訪以及該案法庭上出示的文件編寫。
一個論壇的誕生
路坤回憶說, 當時她正一邊在其單間住房外的走道火爐旁做晚飯,一邊在嘮叨她丈夫楊子立。她丈夫坐在屋內作為結婚禮物的電腦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貼在網絡上的關於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當時她是這樣告誡他的:「你沒必要這樣做。憑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應該想想你的父母、家庭,還有我們的經濟狀況。我們連套像樣的住房還沒有呢!」
但楊對她的抱怨不願多想。陸說:「他告訴我說,總得有人站出來,為社會進步出力。他決定要站出來。」
她補充說:「我知道他是對的,但我很擔心。」
楊子立身材健碩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滿年輕人朝氣、有稜角的臉龐。他不僅是電腦高手,而且在北大求學期間便形成其政治見解。雖說他是機械碩士,但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等思想家的著作也沒少讀並深受激勵。他貧窮的農民父母不得不將其其他兄弟交人收養,作為家中長子的他特別關心農村貧困,常到農村調查當地黨官濫用職權的現象。
1998年畢業後,楊找到一份編程員的工作,並設立一個頗受歡迎的網址,取名為《羊子的思想家園》;他在該網址上發表譴責中共和主張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寫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我關心的是人權、自由和民主。」
秀髮垂肩目光憂郁的路坤是一名雜誌編輯,她從不閱讀她丈夫的文章和詩篇。她渴望寧靜的生活,常敦促丈夫學學自己的同學們,追名逐利,早過小康。楊卻不願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夥朋友,同他一樣,關心被新興經濟遺棄的人們。他們都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不久,如他一般,從其它省份來京讀書,平時願意談論如何能改變中國和幫助不幸的人們。
當一些朋友提議建立俱樂部作為討論場所時,楊毫不猶豫地便加入進來。他們以中國著名的五四運動時期發起的一份頗具影響力的雜誌名稱為該俱樂部命名為「新青年學會」。當時就是學生和知識份子熱烈討論1911年最後一代皇帝下台後中國的未來走向。
張燕華(譯音)是一位語氣溫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擔任公務員。他專程花兩個小時前來北京參加小組討論會。他回憶說:「我們就是不甘平庸。我們要為社會做點甚麼。」 他們在不同的大學校園、宿舍、教室或乾脆在露天舉行聚會。 他們歡迎朋友、同學們加入進來。有時他們會邊喝茶或吃飯邊聊,但一般他們都是坐那聊,一聊就是數小時,話題包括政府腐敗、下崗工人境遇或農民家庭的稅務負擔等。
范而軍(譯音)是一位身材矮小頭髮粗密的北航畢業生,畢業後留校做助教。他說:「我們對我們這代人的冷漠談論很多。我們感覺,其他年輕人過於追求物質,不考慮該做的事。」
他們時常意見不一,例如,相互辯論著政治變革到底是應該始於黨內還是黨外,何時採用選舉制為適宜等等。但他們都認為,中國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對言論的限制阻止了人們討論緊迫問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當時28歲的楊是俱樂部中年紀最大的,也是小組中西方自由主義最堅定的主張者。與其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是他的朋友26歲的徐偉。身材較高帶有書生氣徐是報社記者,同時他也是堅持馬列主義思想的中共黨員。他倆是俱樂部中最成熟、最有修養的成員,徐當選為組長。
另外還有4名成員。
張宏海,27歲,北京廣播學院畢業,臉上常帶友好的微笑,但卻是小組中情緒最易激動的一員,最易提高嗓門或口吐臟話。
靳海科,24歲,范的高中同學,一頭濃密的黑髮,穿著隨便,是最外向的成員。他被指派負責發表成員的文章,因為他可以在其工作的網絡公司利用電腦上網。
身材矮小的大四學生黃海霞是小組中唯一的女性。22歲的她也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黃很敏感,時常在惡夢中看到兒童沿街乞討。
最後是李宇宙。
征招特務
李在國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觸他時是大三學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機叫了起來,屏幕上閃出他不認識的號碼。他回話時,對方是個男士,自稱是國安部官員,並問李能否到城裡一家飯店與其見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學正因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北約轟炸而民怨沸騰。許多中國人都不相信是誤炸。李也參加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外的抗議活動。他確信他沒做甚麼錯事,也就同意了與該特工見面。
時年27歲的李,寬肩膀,方臉龐,寸頭;他回憶說:「我認為沒甚麼大不了的。我當時甚麼也不怕。我甚至還有些好奇,因為國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難測。 」
兩名男士在飯店前廳與他見面,並對他前來表示了謝意。他回憶道,兩人都很年輕,30來歲,他們解釋說在調查一名無業教師,稱該教師在大學校園散發措辭嚴厲的講稿,既譴責美國,也攻擊中共懦弱無能。
李知道他們是在說誰,就幫助了他們,因為他認為那個人可能很危險。
但是特工不斷地給他打電話,開始問他有關校園內的情況和學生如何看待各類問題。李還是同意幫助他們。
他說:「當時我想的很簡單。我想這是在做好事,因為我在幫助國家。就像他們在搞民調,想要瞭解校園的政治傾向。」
李說,他每隔2、3週便同他們見一次面。特工會問他學生們如何看臺灣2000年總統大選和北京申辦2008年夏奧運。他們還會問如果江澤民決定不退學生會做何反應。李後來說,幫助國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個,但他從未與其他人見過面。 那兩名特工告訴他國安部內有一個專責監督大學的司,並稱他二人僅負責人民大學。
然而,李似乎成為國安部有關學生活動的最佳消息來源之一。他說,政府開始每月向他支付約值60到75美元的津貼,並要求他呈交書面報告。他說,數月後,國安部向他索要個人簡歷,決定待他畢業後招其為全職特工。
從許多角度來講,國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廣,因為他經營一家網絡咖啡廳並協助發起一個學生組織。他本人似乎對干特工也滿感興趣。他在一個貧困的鄉村長大,從小夢想當警察,時常聽到他父親在抱怨毛澤東搞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認為在國家安全部某一份職是糾正此種不公正的機會。
他說,他認為中國政府需要變革,他希望從內部推動改革。他說:「在高中時我就知道共產黨不好。我知道這是個政治制度問題,這個制度是獨裁製。」
當他遇到楊子立和另外幾人時,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們的理想和決心,幾乎每週都與他們見面。他說:「我們就像兄弟一般。我們志同道合。」
但當國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關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時, 他答應了。他說, 在他為國安部書寫的30幾份報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關於他的朋友和他們一道成立的小組。
李自認為, 小組當中有人在國安內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幹了, 那不僅會毀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將引起他的朋友們被注意。而由他自己來調查他們, 他還可以保護他們。
李說,無論怎樣, 他確信他的報告不會帶來甚麼不好。他說, 楊和其他幾位畢竟沒有在幹壞事。
麻煩開始
「新青年學會」從未實現其創始人的初衷. 他們曾試圖使其正規化: 簽署誓言,制定決心致力於「探討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章程, 甚至想啟用會費制度. 但一要開會或搞活動, 大家都是功課忙, 工作忙或個人生活忙. 很少能有超過3或4人擠出時間聚一下.
偶爾小組會組織研討會.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動中, 兩位被禁在國家媒體發表文章的自由派學者參加並批評了中共政府, 他們主張民主改革. 李說, 一位遭禁的中國民主黨成員也出席了.
數週後, 中國的主要警察機構公安部開始騷擾研討小組成員之一靳海科. 他們多次將其拘押審訊, 詢問有關「新青年學會」的情況及其與中國民主黨的聯繫. 他們通知其單位他被調查, 還想說服他監視其朋友.
靳非但沒有出賣朋友, 反倒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他們. 李對警方在調查該小組感到意外, 但他沒有驚慌失措, 把情況透露給他在國家安全部的上司. 其他人更感不安.
來自天津的小組成員張燕華回憶說:靳「告訴我們說, 他向警方交代了我們的姓名. 我們並不生氣, 我們知道他是想保護我們. 但我們感到緊張.」
一月靳丟了工作, 顯然是因為來自警方的壓力. 他的朋友們同意結束新青年研討小組.
兩月後靳去找他高中同學范而軍. 范回憶說, 他來時情緒不安, 想要召開小組緊急會議, 因為他認為警方正在準備大搜捕.
范講, 與靳談完話後令其不寒而慄. 非但沒有去參加會議, 他猶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學他當作導師的一位黨官出主意. 當晚, 那人把范叫到其辦公室. 國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著他.
范說:「我盡力向他們解釋, 但我記不住那麼多, 他們也不滿意.」凌晨3時, 特工放他回家, 但提醒他說他們還會回來找他.
四天後, 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 國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討小組成員: 靳海科, 楊子立, 徐偉, 張宏海和張燕華. 幾名特工還劫持了楊的妻子路坤, 他們將其強行押入一輛小車, 用布袋罩住她的頭後把她帶到國安部拘押所.
路說,特工連審她三天,逼她說出有關她丈夫及其活動的情況。她講,當她拒絕向他們透露任何姓名時,特工便笑她。她援引一名特工說:「你今天的麻煩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 你的朋友出賣了你。他們甚麼都告訴我們了。」
張燕華說,他被連續30天每天10小時提審後獲釋。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 因為特工主要問他該小組有否在該市活動「他好歹回答中沒有傷害他的朋友。
黃海霞沒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學政工幹部叫去見幾名國安特工。她被提審三次,每次時間都很長,並且都需在自述記錄上簽字。她說,特工多次談到長期入獄的可能性,讓她要考慮自己的學業前途。
在她第一份記錄中,黃寫道,「新青年學會」想要「把中國變為更美好的國家。」但在第二份記錄中,她說她後悔「與這幫自命不凡的年輕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詞語攻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她感謝國安特工「幫助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在經歷了長達6小時提問後簽字的最後一份記錄中,她寫道:「「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組織。這是一個非法組織。它企圖推翻黨的統治和動搖黨的領導和威望。」
國安部特工還多次提審范,3月和4月各兩次。他說,最後一次是在市拘留所。
他回憶說:「他們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筆錄並要我在上面簽字。我看到上面我說楊想要將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張宏海贊成革命手段。我確實講過類似內容,但那都是憑印象講的,我認為他們不應以此作證據。」
他說,筆錄中還有他沒有講過的話,如其中有寫:「我們組織的最終目標是推翻中國政府。」
但范說,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異議。他說:「我身在拘留所,周圍都是鐵絲網和荷槍實彈的獄警。感覺上去他們在威脅我。他們總是說,他們是國家機關,我得與他們合作,否則後果自負。」
所以他在筆錄上簽了字。
面對後果
李宇宙回憶說,當他聽說他的朋友們被捕後難過至極。他逐一給他們打電話,沒有一個能打通。次日,他給他在國家安全部的上司掛通了電話。
他的上司證實了被捕消息,並讓他暫避幾日。
李說:「我想他是要讓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盡力安慰我。他說,如果我們不逮捕他們,別人也會逮捕他們。接著,他說,他們將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們被放出時,他們不會再認識我了。但這讓我更難受。」
李說,他當時頭腦混亂的甚麼也說不出來。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訴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內抱頭痛哭。一時怒起,他用香煙燒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記住當時的痛苦和愧疚。
李說,幾天後,他開始使用筆名替他的朋友們在網絡上發表申訴文章。
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沒有斷絕同國家安全部的關係往來。他也許感到愧疚,但還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獄中朋友的行列。他說,他要找到幫助他們的另一途徑。
李說:「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他補充說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擔心我無法畢業。他們可以以任何理由將我逮捕。」
三週後,李在國家安全部的上司請他去吃午餐。席間,李同特工們共進煙酒,對他們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飯後,他們要他在一份筆供上簽字,作為案審正式提問時他的答覆。
筆供上說:「我認為,「新青年學會」是一個非法組織和政治組織。首先,它未經登記。其次,它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性,我認為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以多黨制和西方資本主義取而帶之。」
李簽了字。他說他沒有仔細看。
宣佈判決
六個月後,當檢察官在法院陳述案情時,主要依據黃海霞、范而軍和李宇宙的簽字筆供。
根據列席一日審判的家屬記錄,四位年輕人為自己做了當庭辯護。身著被捕時穿的衣服—多為絨線上衣,他們逐一站起對著三位法官為自己陳述。
張宏海反問道,研討小組連設立網址的資金都籌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偉指出,研討小組的成員一半是中共黨員。當檢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張「結束老人政治」時,他反駁道,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使用過同一說法。
楊子立爭辯,檢察官指控他們推動的「社會制度自由化」不等於顛覆。他說:「自由化意味著通過改革擴大自由度。例如,過去20年的改革,難道那不是自由化的過程嗎?」
李宇宙那時已經畢業。國家安全部在為正式僱用他辦手續,並要他開始調查和潛入其他涉嫌異議小組。但他不再有興趣為他們效力。
而他隨後採取的行動顯示出他的內心矛盾性。李似乎非常想幫助他的朋友們,但也不願承擔出賣朋友的全部罪責,或為了他們而犧牲自己的自由。
首先,李給法官寫了一封信,為其四位朋友辯護,同時宣佈他簽字的筆供作廢。但他沒有透露他與國安部的關係。他將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稱這樣做是為了提高其在異議群體中的可信度。
後來他又與楊的妻子路坤聯繫,約她在麥當勞店見面。他給她看了香煙燒灼留下的傷疤,但沒有勇氣向她承認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
他還試著到中國最高法院為楊和其他三人尋求幫助。他同樣沒有告訴法院官員他與國家安全部的關係。但國安部很快發現了他在幹甚麼。他說,他人還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撥通了他的手機,要他「馬上回來,不然會逮捕你。」
當日稍晚,國安部的一名司長把李帶到一家茶館,客氣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遠。李回憶說:「他講:「我們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難受。回家休息一下。」 但他還說我是個成年人,要為自己的所為負責…他說:「別以為離了你我們就找不到間諜了。」」
李拒絕再為國安部幹事,而開始以中國人權黨的假組織名稱在網上發表有關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來電話問他是否聽說過這個組織。李說沒有。兩天後特工又來電話並告訴他一個電話號碼。是他女友的號碼,他就是使用這個號碼登記上的網。
李回憶說:「他說,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寫的,他就沒辦法幫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煩了。」
第二個月,李搞了本護照,並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幫助下於7月8日飛往泰國,緊接著在聯合國的一個辦事處申請了難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楊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兩年多之後,法官舉行第二次聽證,庭審該案件的新證據。檢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為國家安全部效力時提供的筆供報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帶進法院聆聽判決。他們每人身後站著兩名安全官。但法官還沒來得及宣佈判決書,徐偉便向前衝去後摔倒在地。
現場人證說他大聲喊道:「我抗議!北京國家安全局毆打我!我不會承認犯了任何罪!我不會無辜冤枉他人! 」
他緊緊抱住一個桌腿不放,5、6個安全官一起動手才把他拉開,隨後將他抬出去。接著,法官宣佈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顛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監禁。楊子立和張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將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給他們任何抗辯的機會。
充滿悔恨
數月後,李宇宙細讀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飯店的前廳。看上去,他好幾天沒有盥洗了。
他抬起頭,眉頭略皺,表情茫然,終於開口了:「是我寫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報告最長,主要談徐偉。報告中說,他在忙於計劃成立一個秘密組織,並認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為政治變革的手段。報告還說,他已確信李「完全信得過。」
李說:「我不記得我為甚麼要寫這些。我當時不知道調查的目的是要逮捕這些人。。。」他深沉的聲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報告稍短。它記錄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學會」成員參加的會議。報告提供了每人批評中共的言論。
李認為這份報告的內容沒甚麼。 他說:「任何中國百姓都可以說這些內容。課堂上的老師也說這些內容。」
第三份報告描述了「新青年學會」的第一次會議。篇幅更短,內容不很具體,把與會者分為兩類:5人讚成「暴力手段」,2人主張「和平手段」。
李說:「國家安全部對這份報告不太滿。他們說,這事不小,我應再寫具體點兒。但我偷懶沒照辦。我總是盡力少寫點兒。」
第四份報告是講發生在李的宿舍內的一次會議。當時靳海科告訴他警方在騷擾他。張宏海也在場。報告說,張主張他們必須擴大他們的組織。
李說:「當時我在為國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須寫這些東西。」當問他是否在欺騙朋友時,他稱他是在工作,但他補充說,國安部濫用了他的報告。「用我的報告分析社會還可以,但不能用來作為給人定罪的證據......如果我是編造的怎麼辦?」
李說,個人野心似乎是國家安全部決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動機。他的上司們想要破一個大案,好增加經費、獲得提升。他們的上司無疑也想得到同樣的好處。李說,所以各級官僚都誇大他的朋友們的活動,或許一直到中共最高層都是如此。李說,當競爭機構公安部開始介入時,國安官員決定採取行動,保證自己立功受獎。
但李否認自己匯報朋友和在報告中誇大其辭是個人野心所然。後來在被問及他此時要對朋友們說點兒甚麼時,他回答前停頓了一下,然後輕輕地說:「我從未想過會傷害他們。我不想推卻責任。我的確後悔寫了那些報告......它們被用作證據,傷害了他們,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後他們從未再見面。但在沉默了數月後的去年10月,逃脫逮捕命運的另三名研討小組成員鼓起勇氣,代表他們的朋友在上訴聽證上作證。
張燕華仍住在天津。他說過的話沒有被用作給楊等定罪的證詞,但事發後他沒為他們做甚麼。他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每天為他的朋友祈禱,並且當楊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時同意作證。
黃海霞知道自己簽字的筆供傷害了她的朋友們,但她在盡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審判後,她在徐偉女友的要求下給法官認真寫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國家安全官員「在某種程度上歪曲了。」然後她去了上海。張在那裏找到她,並說服她回北京參加聽證。
范而軍仍在北航教書。連續數月他害怕得連打聽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氣都沒有。有一次,路坤要見他,他推了,稱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但就在上述聽證要開始的數週前,楊的律師電話找到他,提醒他簽過字的筆供。他對自己所說過的話的嚴厲程度感到吃驚,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證。
但法庭拒絕他們入內。三人坐在路邊,寫了一份聲明,為他們的朋友辯護和否認「新青年學會」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絕接受。
後來,陸說,她已經原諒他們三人。她說:「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是在壓力下才這樣做的。」
但她不會原諒李宇宙。她說,他的行動是自願的。她說:「他撒謊並出賣朋友,然後又出國,而不是留下來幫助他們。他不應獲政治庇護......他應該回來,哪怕是要坐牢,因為他就應該坐牢。他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一次李從曼谷打電話給她,要她把法庭文件複印件寄給他,他好盡力幫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駁回四名被告的上訴。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許探視她丈夫,幾乎是他被逮捕後整整三年後。她說,他的頭被剃光,人消瘦慘白。兩人隔玻璃牆對坐,通過對話機交談,但很難聽清對方講些甚麼,因為房間內擠滿了其他犯人和探視人員。
路說,她哭了,並告訴她丈夫她終於開始閱讀他所寫的那些文章了,她現在明白他為甚麼要堅持寫下去。但主要還是楊在說。他說話速度緩慢,對自己讓家庭失望表示難過。他讓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況下照顧好自己。
陸說:「他講他是冤枉的。他告訴我要有思想準備。他說他不會為獲假釋而承認自己有罪。」
僅20分鐘,電話線便斷了。他們的時間已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