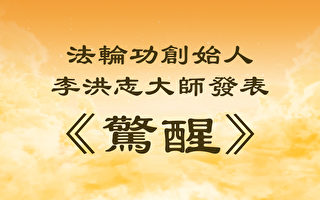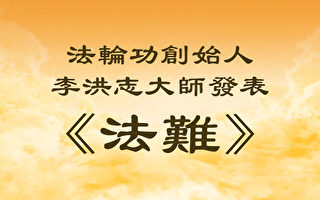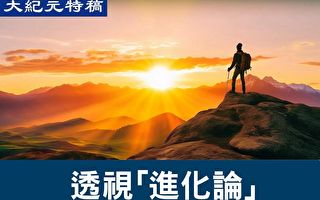【大紀元7月17日訊】來安慶之前,就被這裡的大把人傑地靈深深吸引著……從乾隆二十五年至1938年,其間170多年,一直是安徽省府所在地。既然是安慶文化徽州商人構成“安徽”二字,自然在人文上地理上大有其可觀之處。
“桐城派”諸位大文豪、陳獨秀、徐錫鱗、鄧稼先、趙樸初﹔太平天國安慶保衛戰、辛亥革命徐錫麟起義、安慶馬炮營起義……古往今來,這些同安慶息息相關的人物與事件莫不在黃梅戲的閑牌散韻中任時光靜靜淘漱著,把自己的功過榮辱交給了茶館中的後人品評。
出差辦完事情迫不及待地在城中四處游走一番,印象至深的是迎江寺的振風塔和陳獨秀墓園。
迎江寺位於長江之濱,寺中無非佛祖菩薩金剛羅漢,雕藝上無一例外地佛祖歡喜、菩薩慈悲、金剛怒目、羅漢怪異,各地同一版本,全部似曾相識。倒是寺中的那座七層高的八角振風塔與全國各地的各處寶塔頗頗不同。外觀上看來古樸憨重,與兄弟產品並無二致,等到攀延而上時才發現別有機關。上下都難,上完一層樓梯找不到另一層的臺階,有時轉夠三百六十度有余方才如獲至寶地尋到一條出路,忙不迭地跑上去卻又早忘了來時的途徑,莫名其妙闖到第七層塔頂算是到了頭,用不著極目遠眺,便已俯瞰長江和江面上的點點貨輪。上午的一場傾盆大雨似乎把江水翻轉過來,混濁的江水既不波瀾洶湧,也不波平如境,就這樣昏昏黃黃地蕩溢著,分不清到底是長江還是黃河。如今的江船早已是有船無帆,“孤帆遠影”的盛景同樣隻能出現在影視劇中劇了。回過頭來還是覺得這塔雖始建於明代,數度翻修依然形神不改。相傳該塔是為了振興文風所建,400多年來的“五裡三進士,隔河兩狀元”也許就是借了塔的鐘靈之氣才得以文風大振,想來設計者——當時的北京白雲觀老道人張文採一定是個妙人兒!放在今天一定是位“高工”,而這塔也因了他老人家的奇思妙想方不枉了“長江第一塔”的英名。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不知他老人家是否救過人命,但退而求其次這塔卻造得絕無僅有,他想告訴後世什麼?世間本無坦途須歷經尋覓方可登峰?來路與去路本無更改卻來時找不到去路去時記不得來路本是庸人自擾?還是世間的復雜遠遠不是文人的想象?又或者老道士原本就是個老玩童僅想同後人開個玩笑而已,徒留後人牽強附會同我一樣傻呵呵地胡猜亂想?
在進士與狀元隨著大清王朝在歷史的長河中遠遠流走之後,陳獨秀這個晚清小秀才也憤然脫冠,徑直走出安慶去領導了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近代史上也由此嵌入了一位不可或缺的領袖人物。也許歷史真的是越久遠愈清晰愈公正,無論如何他的墓園和紀念館再不必隱姓埋名了,墓地周圍那濃厚的綠意仿佛上天伸下一隻巨靈之掌也不能一把抓透,在中共這個政治環境下雖則連塊刻寫生平的墓碑都沒有,但蔥郁無邊的草樹依然讓人感到那是老夫子冥冥之中不息的學者之氣。勝者王侯,對王者大量的褒溢之詞,公眾似乎早已乏味而麻木,而對於諱莫如深的人物和事件卻由好奇心及潛在的崇敬感驅使著亟欲一探究竟。
晚景下孤獨的大理石白墳包有些落寞,滿目的綠色漸漸變得幽暗。雙層的漢白玉欄桿圍不住這一刻黃昏的蒼涼,盛夏的微風中一大群亂飛的麻雀吱吱叫著忽地落在幾棵松柏樹梢上,青白的石質摸上去有些濕漉漉的。陳獨秀畢竟是改寫一個時代的人,想想前不久連戰與宋楚瑜拜謁中山陵的煊赫,此刻的孤墳益形影隻。聽過一句西諺——孤獨隻屬於固執的人。固執於學問讓他學富五車,固執於於信念讓他五度進出牢房,最終固執己見也讓他失去了一片江山……天黑下來了,霎時間我有些分不清固執與忍耐有何質的區分與共性。
好象沒聽說三位夫人中哪位陪他沉睡墓中,情感上順理成章地應該屬於第三位潘蘭珍女士。如果說前兩位所嫁的陳獨秀是秀才和教授,這位女士所追隨的卻隻是個政途不濟的落迫文人!在陳氏退出政壇埋頭深巷最狼狽最惶惑的日子裡,蘭珍女士在很久都不知其真名實姓的情形下,隻出於對文人的憐惜與仰慕遂攜手相伴,陪他走過了顛沛流離的晚年。都說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位肯付出的無私女人,但成功之後走向衰退的男人背後的女人又豈是“無私”二字所可包容?人性的偉大似乎隻有在落寞與失意中的持之不懈才更能詳釋得淋漓盡致!可悲的是陳獨秀在中共內部斗爭中被趕下臺時,得不到救助,連2位優秀兒子都被內部出賣致死,人生之悲!
一位同伴採了一大束野花放在了墓前,我想這束花更該獻給潘蘭珍女士!(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