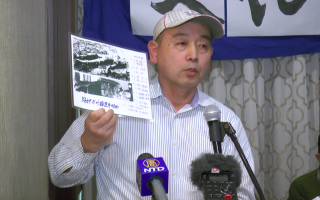【大紀元8月14日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學從屬於政治」的論調,加上列寧「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的「無產階級文藝」綱領,中國音樂藝術的「黨性」原則得以確立。後來中共又提出「雙百」方針,為其破壞傳統的民族文化資源披上了看似合理的外衣,同時也為其利用音樂施行意識形態的統治找到了「理論基礎」。從此,中國的音樂便成為捆綁在中共政治武器上的工具。
在「文革」期間,八個「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濱》、《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交響音樂《沙家濱》成為全部中國音樂的代名詞。這時期的音樂文化現象,從表面上說是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但由於這些音樂作品基本上是中共刻意篡改歷史的產物,是中共謊言的包裝物,因此在這些作品的傳播和接收過程中便明顯地把謊言和虛假的歷史植入了人們的頭腦中。由於十年間這八個「樣板」戲是「文革」十年當中八億中國人僅有的音樂資源,人們在強制地「學習」和反復地「欣賞」這些音樂作品的同時也就是一個不斷地接受共產黨「洗腦」的過程。這個洗腦一方面抹煞了人們對於真實歷史的認識,同時也無條件地接受了「無產階級」的審美原則。
江青說:「這八個樣板戲就已經把帝王將相、資產階級趕下了舞台、趕下了銀幕。」在中共的眼中,中國傳統戲曲的主題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但應該看到,這種所謂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題材源自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特點和文化發展方式的藝術特徵。以此為題材的戲曲劇目在講述歷史故事的同時,也在微觀上塑造著民族的性格。以京劇《四郎探母》為例,這部戲以宋遼的戰爭為歷史背景,在以舖敘歷史背景的基礎上,描繪了楊延輝雖身在異國但愛國之心未泯,幾經周折重踏故土並最終返遼的故事。整齣戲交織著以佘太君為首的楊家將的愛國風範、鐵鏡公主的深明大義、四郎結髮妻子孟氏的賢惠溫柔•••••在這一幕幕的感人故事當中,人們學會了分辨善惡情仇,也懂得了作人要忠誠、愛國的基本道理。在另一出傳統戲曲《鍘美案》當中,則演繹出秦香蓮不畏權勢、狀告當朝駙馬的英勇,也展現出有包公替民伸冤、救民於水火的剛正無私,同時人們也在陳世美這個角色身上看到了甚麼叫背信棄義。這些傳統戲曲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來,使得人們在欣賞舞台上演員唱念做打藝術美的同時,接受了戲曲中所蘊含的道德準則。
但是,在中共的文藝政策當中,由於文藝的黨性特徵,使得階級鬥爭成為藝術表現的主要內容。在「樣板」戲當中,我們看到的基本上是「敵我」鬥爭,也就是兩個不同階級或主義的鬥爭。更進一步,在這種由共產黨所虛擬出的「鬥爭」當中,由共產黨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在客觀上營造出一個扭曲的價值標準和審美標準。這個審美標準通過在殘酷的敵我鬥爭展現「英雄人物」敢於犧牲自我的「高尚品格」,通過「英雄人物」的機智和敵人的「愚蠢」產生對比,製造出藝術作品所必需的「美」,而最終「英雄人物」的必勝和敵人的「必敗」為這個審美過程製造了一個理想的終點。但是,這種被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是以基本的人性為出發點,而是在共產黨虛擬出來的「鬥爭」環境中擠壓出來的,在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是對階級敵人的惡和對階級親人的愛。這種基於階級的愛與恨本身缺乏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愛恨情仇的真實性,因此並不具有真實的「樣板」價值。但當這些被變異了的「模型」植入人們的頭腦中,便會取代了人原有的思想感情。當人們不斷去「學習」這些「英雄人物」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強化著這種變異了的思想感情而最終演變成對黨的愛和忠誠。
其實,很多在「樣板」戲中曾經擔任主要角色的演員,他們的生活境遇並沒有像戲曲角色那樣成為樣板。《紅燈記》中的錢浩梁、《智取威虎山》中的童祥苓都曾在中共專制統治之下有著不幸的遭遇。其中的原因在於藝術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藝術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至於藝術家,也只是其工具上的一顆螺絲釘而已。隨著政治鬥爭的「風頭變換」,藝術家就如同波濤中的一葉扁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歷史已經走過了那一頁,但願今天中國的藝術家,尤其是那些還同中共權力捆綁在一起的藝術家們,從這歷史和現實的反思中找回自己的位置,伴隨著《九評》的春風,重新定位作為人和作為藝術家的基點,進而為我們的民族創作出真正的藝術。@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