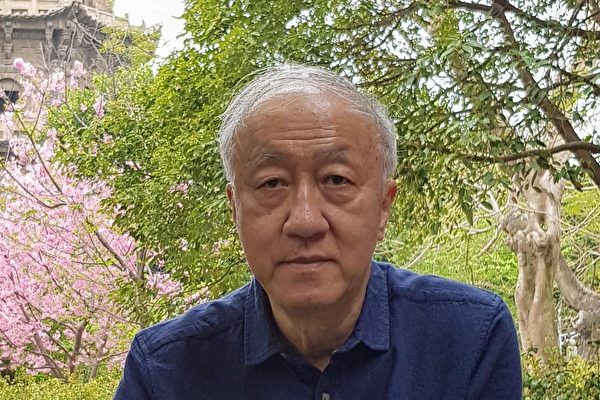【大紀元2024年04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46年前,顏純鈎,這個中學畢業的紅衛兵,拖家帶口逃難到香港。而立之年的他,「兩袖清風、舉目茫然」。40年時間,這個文學青年不但在香港圓了自己的文學夢,並且獲得了超越他對自己期望的成就。正因如此,他永遠不會原諒中共踐踏香港,對香港所遭受的厄運痛心疾首。
2024年2月底,在公民協進會與列治文公眾圖書館合辦的「閱讀自由在加拿大」活動中,記者幸運地見到了著名作家顔純鈎先生。作爲主講嘉賓之一,顏先生分享了他的新作《香港我的愛與痛》,一部記錄了對香港「反送中」那段歷史的思考卻無法在香港發行的書。期間,顏先生欣然答應接受採訪,和讀者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和文學創作之路。於是,就有了在顏先生家附近的一間咖啡店裡的這次訪談。
香港改變命運
顏純鈎人生的前30年是在多災多難的大陸度過的, 文革過後有幸移民香港。從1978年到2018年,在香港40年,他活出了精彩的人生。因擔心九七政權移交,許多港人被迫離開香港移民海外,顏純鈎一家選擇了加拿大。之後他經歷過回流香港,2018年,退休兩年後,顏純鈎和太太回到了加拿大。走過不一樣的兩岸三地,如果你問顏純鈎是哪裡人,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香港人。
想不到的是, 2019年一場反送中運動, 香港成了顏純鈎有生之年也許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在《香港我的愛與痛》這部書裡,他深情地寫道:「幾乎每天,我都會想起我的香港,那裡的山水城廓,那裡的親朋好友,一一在心頭徘徊…… 今生今世,盼有機會回香港重溫舊夢,如果沒有,那就讓我的魂魄悠悠,從太平山頂俯瞰,為我的香港祈禱祝福。」
這種對香港的感恩與深情,也許只有那些在逃港潮中從大陸移民或逃難到香港的人們感受會更加深刻。
顏純鈎表示:「我想很多大陸來的人其實那種感受差不多,因為我們在大陸是紅衛兵那一代,知識青年那一代。我們這一代在大陸受過很多苦,個人的前途是完全沒著落的,又沒機會讀書,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是怎樣的。」
來港前是文革尾聲,大批被毛澤東用完即棄的紅衛兵,被下放到農村。中學畢業的顏純鈎,做了工人。他回憶道:「我在大陸做那些『架線工』,就是架設電線。那些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險的。」

1977年開始大學恢復招生,紅衛兵那一代也有機會讀大學了。
顏純鈎記得「那時是兩年制,短期培訓出來做非正式教師的」,「我曾有機會,單位要推薦我去讀,但我那時很倔強,不是我喜歡的我就不去讀」。
1978年,30嵗的顏純鈎到了香港,五年後太太和兒子也獲准來港團聚,女兒是後來在香港出生的。

他表示:「來到香港後,因為我自己興趣是文學方面,有個同鄉介紹我去報社做校對。就從那裡做起,一邊做校對一邊讀書。
「因為在香港很自由,你什麽書都可以讀,沒人禁止說這樣東西你不可以想,那樣東西你不可以想,你就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它又提供所有平等機會給你,還有很多社會對你的資助,讓你會發揮自己的潛質。
「就因為這樣,我有機會在香港,可以説基本上實現了我自己的理想。我的小朋友在香港受到教育,雖然香港教育制度一般,但他們一路都很自由地成長,所以,應該說香港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仍在大陸,就不知我到現在的情況如何了。」
顏純鈎的老家是在大陸福建,談到對家鄉與對香港的感情有什麼不同,顏純鈎表示:「我對家鄉當然有感情,因為我自小在那兒成長。到上山下鄉及後來工作、離開家鄉,一年可能也會回去十幾廿日,所以對家鄉感情很深,但是對家鄉以外的生活環境就沒什麼感情了。我對香港當然最有感情,因為在香港,我由一個不是香港人,慢慢變成一個香港人,一個外來的人變成一個在地的人,由一個自我價值感覺很差的人,慢慢變成一個自我價值感覺比較好的人,這過程相當刻骨銘心。」他深深地知道:「沒有香港,便沒有我的一生,所以我對於香港,永遠懷著感恩之心。」
香港人有逃難的基因 稟賦異常
顏純鈎在新書中提出了「香港人是稟賦異常的中國人」的觀點。 他認爲: 「香港人與大陸人、台灣人有著顯著的區別」,「香港人的血液裡有逃難的基因,有移民的衝動」。
他解釋:「除了在地的土著外,香港人的主要組成就是3波人。第一波是臨近1949年大陸 被中共竊權,國民黨撤退時走出來的國民黨老兵、國民黨的一些文人、一些政治難民。
「第二波是50年代三年大饑荒時,因為餓到撐不住,偷渡來的一大批難民。那時政府又放開了,批了一大批出來,我媽媽基本上由那時出來的,因為我爸爸在菲律賓,我媽媽就可以申請去香港。
「接著就是我們這一波,就是文革後的紅衛兵這一波。這一波其實是因為政府沒有那麼多職位安排給這些知青,所以它打開一個口,讓能夠出去的人出去。我們這一批出來很多,我那間中學估計有幾百人來了香港。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有很多香港和海外華僑的子弟;另外有一批是六十年代印尼、菲律賓排華時回來大陸的。文革後一開放,他們再次成批地出來。」
顏純鈎認爲:「這三波人其實都是政治和經濟難民居多,這班人其實在大陸算是文化程度比較高,受過教育,他們的基因都是有見過世面的,比較有見識。比如黎智英,他是一個地主的兒子,但因為他有那種冒險精神,所以他會去嘗試。」
「人在絕境時,生出赴死的勇氣,鋌而走險,做人生一搏,這種人比一般庸眾更有膽識,更勇敢堅毅。」
「這種冒險精神本身就是香港人的一種特質,基本上構成了香港人性格共通的地方,而這其實很有利於香港本身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逃離迫害 投奔自由
從大陸逃到香港,再從香港逃到加拿大或其它非共產國家,顏純鈎一家所走過的移民之路,和千千萬萬香港家庭所經歷的相同,就是爲了逃避中共的迫害,一次又一次地背井離鄉,投奔自由。
逃離大陸
顏純鈎介紹:「其實那時我太太家裡受了共產黨很多迫害。她家是印尼華僑,她兩個伯伯、一個姑媽都是印尼華僑,在49年臨『解放』的時候,印尼的親戚寄錢回來,想在鄉下買地建房子。怎知買了地就被『解放』了,工作隊一來,見到你有地,就不管你是要建房子還是要租給人耕種,總之歸為『地主兼華僑工商業』。當時 『地主兼華僑工商業』就是最黑的家庭成分。
「她阿嫲八十幾歲,老人家經常被人抓去批鬥。她爸爸因為『解放』前讀中央美術學院,跟著名雕塑家劉開渠雕過蔣介石像,本人又是國民黨員,於是,凡有政治運動就會被人整。文革時她爸爸被人抓走,她跟媽媽在家裡,就將爸爸收藏的那些名家書畫全部拿去燒了。
「我太太潛意識裡有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所以,文革後一開放,就要離開大陸。」
逃離香港
「香港大概是從九五年開始講『回歸』,太太就一直說要走」 ,顏純鈎繼續講下去。
「我家也是華僑,但我家沒有像她家受那麼多苦難。我太太一直想走,一直想走,覺得『共產黨要來了,有多遠就跑多遠,只是不想把孩子留下來給共產黨糟蹋。』
「本想去台灣,於是帶家人去了趟臺灣。但到台灣走了一趟後,看到當時臺灣還比較亂,太太孩子都不喜歡,已準備作罷。」結果於顏純鈎有知遇之恩的香港文學界名人戴天,有一晚和他吃飯,建議他也移民加拿大,後來還介紹了移民律師給他。
「既沒有親戚,也沒有錢」的顏純鈎,按照戴天的建議,賣掉房子,趕在「九七」之前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作爲新移民,一切都要從頭做起。顏純鈎記得:「九六年來溫哥華,住在列治文。原本打算在這兒找工作,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我後來就回香港,就做太空人,太太帶兩個孩子留在在加拿大。
「直到我兩個小朋友出去讀書,我就對太太說,你一個人在這兒不如也回來香港,她於是也回到香港,跟我一起,等到我退休才一起回溫哥華。」
在加拿大生活有自由和安全感
經歷兩次遷徙,一家人在加拿大找到了安居之所。
顏純鈎覺得:「加拿大最重要的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我們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很重要,因為你如果今日不知明日事,這種生活會很難挨。譬如我來了加拿大,黎智英叫我寫社評,我就去寫,我不用擔心將來可能會坐牢,這些就是你用錢都買不到的。」
另外,「加拿大、溫哥華本身是一個適合退休的地方。這兒也都有些朋友在,雖然沒有在香港那麼熱鬧、朋友來玩那麼開心,但生活很安定、很平靜,你可以在家做自己喜歡的事。」
香港已經不是心目中的香港
顏純鈎新書的內容是關於香港的,香港「反送中」以後,不但出了《國安法》, 現在《基本法》第23條又立法。作為香港人會有怎樣的感受?
顏純鈎表示:「大多數香港人的感覺都是差不多的,因為基本上香港就是沒有了,我們印象中的香港已經沒有了。香港對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自由,有了國安法、有了23條,基本上就沒什麼自由了。沒自由,那已經不是我們心目中的香港了。
「還有,現在的法治正在逐步消失。法治沒有了,就不能保障原有的自由,也不能保障我們原有的那些人權。民主現在也沒有了,所以基本上《香港基本法》答應給我們的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不僅一人一票沒有,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舊香港什麼都沒有了。」
對香港的遠景仍然樂觀
被問到對香港的前景的看法,顏純鈎回答:「對香港長遠來説當然是樂觀的。你如果覺得大陸長遠來説是樂觀的,香港就是樂觀的了。」
顏純鈎認爲,共產黨有機會倒台,大陸就有機會有一個新生,雖然那個新生要經過多長時間沒人知道,那個過程也可能會很痛苦。
相比之下,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有自由、又有法治。中共倒台後的香港社會可以很安定。所以顏純鈎覺得「我對這件事相對比較樂觀,唯一就是等共產黨倒台。」◇#
責任編輯: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