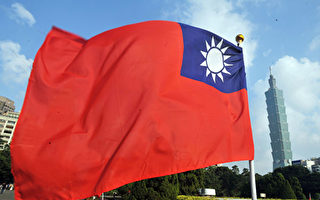【大紀元11月18日訊】國家信息中心的官員2001年說,中國將有2億人口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蕭灼基說:10年後中國將有五類人能進入中產階層,蕭老的預言,給給向上爬的人打打氣,給他一個大棗吃。本人想提三個問題:中國的新階級、新權貴和新精英。
* 新階級
故事一:
狗熊帶兔子玩,上廁所時沒帶手紙,狗熊問,你怕髒嗎?兔子說不怕,狗熊用兔子毛當手紙了。狗熊的塊頭那麼大,兔子沒法子只好拿自己的衣服給狗熊當「手紙」了。中產階級象隻兔子,跟富人玩好了就變成手紙,玩不好……
中產階級——難以界定,文學家形容他們像一塊沒有凍好的冰,藝術家編了一套老闆麗人偽幸福的夢,經濟學家說他們是中國穩定的核心,社會學家說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政治家怕他們長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員吃拿卡要想捏死他,民工們恨不得宰了他,再來一次均貧富。
一提中產階級,人人都特敏感,弄得我好生尷尬。不是我存心找不痛快。在我們這個貌似平等的社會中,一談中產階級,人們就老大不自在,心中暗想:我算老幾?老大、老二、老三,還是個零蛋……有人私下裡對我說,其實我是格格。我心說您甭提滿清這一壺。路邊的小飯館變成了宮庭宴,電線桿上的小紙條兒變成宮庭秘方,街上的小妞也全都變成了格格。經濟學家管這叫「預期紊亂」。關於中產階級爭議和對中國公民社會的企盼,像是學術界吐出一串好看的泡沫。人們不否認他的重要性,鮮有人進行分析、量化和實證。我一接這題就發覺不妙,看不見摸不著找不到著力點。中產階級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方的園的還是三角的,他的政治理念、社會意識、生活預期全然不清楚。
中產階級這一概念,原本是個舶來品,歐洲是經過了 300 年工業原始積累,再加上戰後持續 50 年的高工資、高福利的保護才出現了中產階級。解放後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消滅了有產者,改革 20 年,中國出現了一個新階層,他們有很強的購買力,他們辦公司、投資、信貸、交易和納稅,在這一奇跡中,他們很有特色。所謂中產階層,是以知識份子、職業專家為代表的主流精英的群體,有院士、研究員、教授、律師、醫生、作家、專家、藝術家、自由職業者、高級職員等,包括文官、學人和企業家。他們成長週期才10年還很不成熟,我們缺乏訓練有素的文官來操作民主,又缺少公益的學人來堅實公民社會基礎,更缺乏講信用的企業家來完善產權制度,從而使經濟和民主同時陷入僵局。
早在 1997 年劉吉曾說過,中國很有可能產生新階級。中層消費者怎麼形成的?大約是在 1992 年後,要素市場(資本、信貸、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資源中介服務等)開放後,形成的所謂的「第四代富人」。大批政府、企事業機構的幹部、知識分子下海後,利用他們過去的資源和社會網絡,中層才迅速擴大。據中國社科院歷時 10 年的一份全國性調查,民營中小企業家中幹部下海的占 31%。是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化過程中才形成了廣大的中層。也正是 90 年代中期,一大批中層的金融資產早已超過實物資產。中層消費者其實就是潛在的中產階級,他的生活預期要遠遠超過其它預期。知識、財富、地位等資源的分配本身就傾向於官員,或接近官員的人,文官和學人本出自同一條根,卻走上不同的路。如何保持官僚制度廉潔,又不脫離民眾?他既保持充分的權限,又不損害地方、企業的利益,引導國家經濟發展。這些問題曾折磨過歷代國家決策人。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受益群體是知識分子,由於市場稀缺資源的知識、權力和資本三大資源首先向他們傾斜,他們走上快速上升通道。在富人和中產者流行的個體排它法,你不富說明你沒路子,你費物。
新階級一起步就像走上了鋼絲繩,沒招他惹他,他都害怕自已一不小心栽下來。極度渴望別人尊重,又怕受人忽視的痛苦,是中產階級一大特色。天大的事,莫過於他們自已的地位下降,他們不自信,虛榮勢利活得很累。中產階級最擔心的是社會地位,中產階級社交網絡是它化解生存危機的有效工具。二極分化!貧富懸殊的分化中,迅速分化出來一個獲利的少數和失落的多數。任社會學家大喊大叫,富人離散傾向和不滿情緒,窮人的反社會和暴力傾向,都是極難對付的。
在改革大潮中,晃晃悠悠的中產階級像一條船,經濟變量越大,人們越是經歷著角色和預期紊亂的過程。窮人多以富人為藍本或參照物,中產階級更信奉權威和官員,垂涎更高的社會地位。對於名聲、地位和輿論都驚若寒蟬。像叔本華所說:所有的痛苦來自慾望。中產階級的多重性,即得一些利益,又常常犧牲受挫,寄望於小勝即安,又常常失算。人人自危,即便目前還好,可擔心未來的情緒正在蔓延,人們預期不定,社會角色不確定會對社會造成紊亂。精英離權貴資本很近,離窮人卻越遠。中產者們憎恨比他更富更黑的貪官和富人,可他們也並不喜歡窮人,中產階級好於同類相聚,遠離那些越發好鬥的窮人。他們常把自已的不滿發洩出去:一個為富不仁的高層,一個充斥暴民的社會!「官不像官傍大款,商不像商勾黑幫,學不像學向官場。」富人在中國近乎無形階層,神龍見首不見尾,一年中只在國家級中國新年團拜會中露露面,他們生活在一個特殊圈子,他們害怕窮人的敵視,也討厭中產階級的巴結。客觀上中國出現了大分化,可誰也不願給窮人貼標籤,這讓窮人更抬不起頭,中產階級處在積累期,他們的收入、消費、投資的理念正在形成。過剩經濟下,商品市場對他們已失去吸引力,要素市場上他們已成為主體消費群,金融、證券、信息、信貸、勞動力資源等,中產階級已佔主導地位。一旦他們預期不穩,市場必然有反應。預期紊亂會增加了不穩定因素和動盪。
中產階級總得有個標準吧,有人說有房有車,有人說年收入 20 萬,有人說不得少於 50 萬。有錢就能提高社會地位嗎?那只是給向上爬的窮人打打氣而已。實在繞不開錢的話題,清華李強在 2000 年初《經濟展望》的統計,全國 3.9 億戶家庭,利益群體分為四層,社會底層、利益受損群體、普遍受益集團、特殊獲利集團。社會底層全國大約在1.48億戶,戶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總人口43%,利益受損群體全國約1.6億戶,戶均存款不足2萬元占總數47.6%。兩者相加共3億戶,涵蓋人口近11億人口。普遍受益2513萬戶,戶均不足10萬元,占7.4%.中國富人是特殊獲利集團,441萬戶,戶均54萬元,占1.3%。普遍受益加上特殊獲利集團總共不到3000萬戶涵蓋人口1.2億。(天元數據)這是我們迄今看到最全最近的統計數據了。我們常說的 2:8 規律是錯的,現在是 8.7%的人擁有 60%以上的居民存款。全國 7萬億元居民存款中,他們起碼佔了 3.72 萬億元。在基尼係數達到 0.468,中產階級是不能保持穩定的。
不單單有錢就可以小小不然的擠身中層,還有職業、社會地位、公眾評價。綜合因素很多,你受的教育,你所從事的職業,你的愛好、品味,你穿什麼,用什麼,住的如何,開什麼車,說什麼話,你一張嘴,你的語音就暴露了你的身份。深入研究中產階級的生活形態、心理預期,對宏觀、微觀經濟相當有用。中產者想什麼,他們怎麼消費,怎麼投資,他們的責、權、利是什麼?分析他們的生活預期,這就是個大市場。中層的生活預期,需要有一個長期穩定、信用良好的社會界面,以保護他們的收益和地位。迅速擴大的中層,將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核心。世界金融業認為,中國如果沒有自已的中產階級,中國經濟要想和世界經濟真正接軌,幾乎是不可能的。社會意識是建立在公眾意志之上,民主政治強調的則是誠實、公正和效率。公平正義不是市場問題,道德淪喪也不市場化的結果,恰恰是制度工具出了問題。人大輿論研究所對社會地位評價,90年代初排在前 10 位的是教師、軍官、科技人員、工人、農民、大學生、醫生、作家、記者、警察。90 年代未排序則變為科學家、官員、教師、醫生、律師、廠長、經理、軍官、私營業主、演員、外企僱員。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地位也在重新排隊。經濟變量越快,人們自身命運的不確定性也就越增大了。
有人擔心中產階級生成得太快太大,急需擴大他們對社會輿論、決策上的影響力。富裕起來的新階級,急需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實力。人們一般高估了他們的政治預期,低估了他們生活預期,有專家指出:中產階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核心,其政治人格在向經濟人格的轉變。中產者有政治理念嗎?他們只在小圈子裡發發高論,敢到大街上說說嗎,馬上就滅了你。學者們想得挺好,富裕的人越多,中產階級是一個擴大的平民化「中層」,當中產階級融匯了平民階級,形成擴大的公民社會時,那麼民主社會的確立也就為期不遠了。此話當真?不是說無產階級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嗎。老大哥都快變成了小阿弟了,海外學者還在那空談工人變成中產階級,開什麼國際玩笑啊。老大哥早都被失業嚇破了膽。
新階級正在穩固陣腳,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瓦解。中產階級走的三部曲,通過市場活動達到他們的生活預期,通過生產實踐來達到他們的社會預期,通過專業、學術或院外社會活動,最終將達到他們的政治預期。其中任何一條路走通了,都會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影響決策不靈,走市場掙錢再受挫,那只有一條不歸之路——社會參預。預期紊亂是會影響穩定的。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對政治的恐懼。中國人很少有政治預期,學人的為權貴賞識,暴民的招安,那是陞官發財的夢,陞官發財絕不是政治預期。價值觀的改變,要比汽車、豪宅的普及慢得多。
亞洲模式都一樣,要想出人頭地無非是兩條路,一靠家族,二靠官僚。第三條路社會參與可能性極小,所謂民間組織 NGO、某某論壇、那僅僅是精英走穴瞎起哄,圈子裡豎豎小山頭充大個。受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知識分子自已行使主權後,更加擺脫不了集權和專制。缺少公民意識的認同、組織化和程序化,缺少公開的制度化,人與人之間就缺乏一種穩定的關係,隨機性行為不斷擴大,在個人、家族、利益集團壟斷的社會裡,腐敗才最為猖獗。亞洲價值觀被劉軍寧概括為: 其一,亞洲價值的核心就是安定與和諧高於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國家的權利絕對優先於個人的權利;國家的安定絕對高於每個人的尊嚴。在亞洲價值中,最重要的不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是國家的安定。其二,亞洲價值的支持者認為亞洲價值的意義在有利於經濟發展,但亞洲價值在經濟方面也種下了不少惡果,如官商勾結、金權交易、貪污腐敗、操縱市場、壟斷經營、與民爭利等等。使得腐敗幾乎成為東亞政治的固疾。其三,亞洲價值觀還特別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亞洲的民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也給發達國家帶來借口關於人性人權的的問題攻擊,並最終妨礙了亞洲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進程。
真佛只說家常話,中國最大的問題: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首先是尊重他人的產權。通縮、二極分化、暴富群體、貪官、暴民大凡都與此有關。流動人口、新移民削弱了原有的社會的紐帶、宗法和家庭的控制,兩極分化會造成冷漠反常的群體偏見,衝突與混亂就在所難免。不穩定並非是因為他們窮,而是他們都想致富,暴富的期望值超過其滿足希望的能力。只要預期紊亂,社會就不會穩定。「只要發展經濟,就能保證社會穩定。」那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暴富群體是特殊獲利的富人,即使破產,他不是中產者,也不是窮人。於祖堯曾指出,暴富群體的崛起,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險之一。不能用佔有財富多少來劃分是否暴富。只能從牟取利潤或租金的途徑和手段來判斷。暴富者侵吞勞動者成果,掠奪公共財產,揮金如土,敗壞改革聲譽。解決暴富和解決腐敗問題,關鍵要從整頓分配秩序、理順分配關係、加強法制,從政治體制改革上找出路。國家的政策,貨幣、財政、稅收、利率、匯率等政策,不應成為富人的天堂,應當成為窮人的飯碗。首先是任何資源也不會向他們傾斜,我們一些低級決策(貨幣、財政和稅收),沒有給窮人以上升通道。結構性失業把他們最後一條生路也給堵死了。這種群體性排它法,使弱勢群體變成危險的邊緣人。
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在卸任前說:「我們這個星球正處於兩種強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左右——全球化與邊緣化,自由化與極權,民主化與專制,富裕與貧困在齊頭並進。二極分化到什麼程度,政策是對富人傾斜還是對窮人讓渡。政府能否利用稅收再分配政策來調控危機。處於變革中的人們,只有極少數才懂得這場變革的終極意義」。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給了富人和想當富人的機會和預期,也給了窮人和絕望者以反抗的手段,發展中國家也找著一個理由,以專制集權方式來推進民主化和現代化。像家長打孩子:是為了孩子好。
我們針對社會穩定的研究,處在一個低水平上。不應忽視中產階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作用。中產階級不再是窮人,可遠遠不是富人,不能讓他們惶惶不安像隻兔子。
* 新權貴
故事二:
狗熊帶兔子出門,看一群民工幹活扛木頭,狗熊問兔子,你選擇幹什麼,兔子說,扛木頭太累了,我當喊號子的。狗熊的機智在於,一下就趴在木頭上,讓窮人抬著走。於是狗熊座轎子,聰明兔子為窮人喊號子。
英國有句名言是:「三代陪養一個貴族」,中國有句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反差挺大不是?年青時我在英國,參觀過伊頓公學和皇家海軍學院,25 年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英國的貴族不腐敗。我們的文化、物質傳承到底是什麼呢?教育的目的是:「做什麼人,幹什麼事?」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專家、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這種偶像崇拜是英雄崇拜的繼續,對年青人是一種精神感召,使人們走向成功的信條和行為保持一致。中產階級如何保住現有的地位,並提取高現有的生存狀態。在社會的急劇變革期,人們的道德行為和價值觀很容易走樣,潛在的東西已跟不上經濟生活的發展,從經濟變量上看中產階級,繞不開錢,也繞不開教養這道門檻,油是油水是水。我理解的文明就是教養,當代中國人即不會教,也不會養。
教育的作用,在於闡述一個中產階級的夢想:在受教育的一生中,接受的是中產階級價值觀和技能的訓練。相信艱苦奮鬥、公平競爭,尊重首創精神,進取和個人奮鬥,最後取得社會地位、財富和成功。中產階級對名利的想往,對政治權力的渴望。他的精神支柱是未來預期上。中產階級的原則:走過艱難時世,戰勝挫折和恐懼,必然迎來美好生活。我們重申勤勞致富的原則,富裕是通過刻苦工作、生活節儉,建立新文明、新道德的一個長期過程。中產階級強調的是誠實、公平和效率,而不是屈從於個人和利益集團的動機。教育的目的也防止預期紊亂,防止窮人過度不滿意,富人過度不知足。夢想一夜暴富,不擇手段,投機取巧、作偽構陷、鋌而走險,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貪白不貪,貪了也白貪」,那是流氓無賴的投機理念,劫財犯罪,走私偷稅,秘密拆分流失國有資產,那叫黑幫大盜理念。
窮人與富人,高等教育與亞文化群在道德操守上並不佔有任何優勢。良知是靠人文教育代代相傳的。像教育家費羅培爾說過:國民的命運與其說掌握在政治家手中,倒不如說在母親手中。教育從廣意上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重要手段,教育的兩大功能:一是防止貧窮。二是防止犯罪。我們的教育制度與其說是治學,還不如說教人怎麼當官。教育成了脫貧致富的唯一手段,那會造成文明的退化。50-60 年代對人文、教育的破壞,當初是一代人受害,現在是幾代人品嚐苦果。文明的傳承是由基層的精英來承擔的,當這些精英受壓制和被消滅後,文化就只剩下糟粕了,從而也使得傳統文明的恢復變得極為艱難。中國人在追求幸福預期上,是傳統「福、祿、壽」,手段是非正式的、不規範的,有時甚至是迷狂而凶暴的。英雄觀變成江湖大俠,生活觀充斥著嚴重的痞子化和虛無主義。低級庸俗下流的尋樂主義、東方神秘主義不一而足。現代化的主要四個方面是工業化、城市化、平民化和民主化。現代化最終要涉及價值觀、心態和期望值的轉變,是人的根本轉變。把忠誠、認同感從家族、集團的小圈子擴展到世界上來。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社會暴力、及腐敗現象驟起,這都是個人主義發展極致的惡果,從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教育的失控。中產階級在物質生活正處在上升通道,他們的社會意識卻在退化,對罪與非罪,守法和違法,公與私之間的混淆,價值觀和預期的紊亂,使社會出現了無序。「精神文明」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長,反而出現了萎縮,而新文明恰恰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核心。中產階級在完成了積累期後,有兩種趨勢,一是投資成為法人,一是脫離機構成為自由人。其資產為防止風險,也有兩個出處,一是擴大內需投資,一是抽逃境外,無論從何而論,都應避免後一種情況發生。大量的資金外逃會導致一個國家破產。
權力犯罪會使一切傳統犯罪相形見絀,會引發一連串下層的暴力犯罪。劣幣趨逐良幣,貪官趨逐良紳,刁民趨逐良民。當良幣、良民、良紳統統退出交易後,結果就是黑吃黑。民謠說,「官員不壞,提拔不快,官員不貪,就地罷官,官員不黑,立刻升天。」一些官員背離為國家服務的宗旨,也背離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官員和學人同出一源,同樣素質的一群人,在一定條件下,犯著同樣的罪。他們都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案發前,他們都是好官、好家長、好父親、好黨員、人大代表、政協代表、勞動模範,這種雙重人格,根子是否在教育上。公開場合和私下裡是「雙面人」。貪污、腐敗、犯罪到如此嚴重地步,居然沒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使人不得不思索,我們培養些什麼樣的人?法制、國家、社會、機構、學校、社區、家庭這每一個輝煌名詞後面,都有一個極其強大的規範制度,強制每個人去遵循。如果中產階級都變成了盜賊,這些輝煌大詞都變了味,那小人物也會哭泣,也會流血,也會趴下的……一些學者所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邊際滲透」使貧民受益。這完全像狗熊氣功師侃山。
一個時代的道德本質,應該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意識,國家的制度、法律應當保護公民及國家利益不受侵害。腐敗和暴力,性質上都是非法,只不過手段不同。恰恰是缺少政治意識的組織化和程序化,缺少這種公開的制度模式,社團和個人就缺少穩定的關係,腐敗才會高度氾濫。當公民容忍腐敗時,腐敗就最猖獗,高度腐敗就會引發高度暴力。如任其發展,社會就會變成仁者的地獄,無良者的天堂。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道德自律,沒有價值觀的中產階級會使國家富強。當價值觀約束減弱,道德自律又不起作用時,社會角色的演變就會產生混亂。在不安定、無效的社會裡,公民之間就會缺乏信任感,會使大批人對政治疏遠,以至不擇手段地追求短期效益,毫不顧及公眾利益。當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時,也會把中產階級拖下水,連基本的安全感都難以應付。
中國的大分化正在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維護穩定將是壓倒一切的話題。中國積累期發生的許多正人君子的故事,連資本主義世界也要為之驚詫。中國的危機來自三個方面:金融層面,社會層面和權力層面。防止內生性危機的關鍵,首先要防止社會信用失常,它的危害是毫無遊戲規則可言,交易成本提高,合同失效,三角債越滾越大,銀行壞賬居高不下,假冒偽劣氾濫,欺詐四處發生,資金不斷抽逃;要防止利益集團的矛盾激化,協調地方、部委與企業之間利益格局的矛盾,生產要素和資本,城鄉與地域經濟,不同領域的資本。
維護穩定與和平的原則要通過公平、正義而建立的,減少對家族、階級或意識形態的絕對忠誠,培養人們對正義、公理的認同。公民社會最終要涉及價值觀、心態和期望值的根本轉變,力主社會公平,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尊重,對國家事業忠誠才是社會和平的基礎。要求人們把忠誠、認同感從家庭、集團等小圈子擴大到國家與世界上來。是人的根本轉變。
中國穩定的要素繫於三方面:富人、窮人、中產階級。中國經濟穩定,從金融層面防止危機動盪的關鍵,明確產權制度,防止信用失常。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和民營經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中國的政治穩定取決於政治家、官僚、輿論代表三方的相互妥協的結果。防止利益集團的矛盾激化,協調地方、部委與企業高度協作顯得愈發重要,化解利益格局的矛盾:生產要素和資本,城鄉與地域經濟,不同領域的資本。中國社會穩定的要件是,經濟增長,預期穩定、社會角色相對穩定。把個人預期、價值觀與公眾利益相統一,才能減少動亂的因素。防止內生性危機的權力資本擴張、黑社會抬頭和流民犯罪。中國動盪的根源是權力資本擴張、黑社會抬頭和流民犯罪。
中國社會穩定,取決於精英和決策層如何調和三大勢力的衝突:激進的政治勢力,溫和世俗勢力,和下層的極端勢力之間矛盾。制度是否有能力和空間培養出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來避免動盪,不能讓新階級惶惶不安,擔心自已不久就要倒大霉。
新階級要對中國的穩定有所作為,不要只喊喊號子。
* 新精英
故事三:
狗熊病了躺在床上,兔子給他看病,狗熊問他:「誰派你來的」。兔子說:「我是大夫啊。」狗熊說:「你有執照嗎?」 兔子只好打道回府。狗熊快死了。兔子又自作多情來了,「上帝派我來作禱告,我是神父。」狗熊不信:你有聖經和十字架嗎,嚴防假冒!」
90年代發生了最大的社會變遷。小人、狂人、窮光蛋,在逃犯,投機家、封疆大吏、社會名流都極盡表演。
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權力資本、經濟資本與知識資本的總體性精英集團。10多年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來迎合權力資本的擴張。精英傍上權力資本,傍上國際資本,儼然成為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的代言人。社會地位迅速分化,體制不變,僅產權制度鬆動,意識形態、文化思想、體制層面則基本不動,一些社會控制工具跟不上社會形勢的飛速發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這些社會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無的地步,不同的利益衝突、協調、合作、制衡就很難完成。一元化意識形態控制不了多元化社會發展。精英靠什麼?權力加資本。尚若精英無視「草根」生存狀態,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呈現無序脆化狀態,中國已具備導致社會無序的諸多要素,不穩定因素最後聚焦在–腐敗與暴力上。鬧得連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
爆炸、沉船、翻車、塌樓、跨壩、斷橋、火災、搶劫、綁架,接二連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學魏尚進曾論述:高度腐敗導致高度暴力和高發事故。腐敗使政府科層組織優勢喪失,產生負效率加大社會成本,惡性事故瀕瀕不斷,恐怖活動開始抬頭。假如中國腐敗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國的事故及犯罪率會降低93%。
經濟學家說尋租說了多少年,啥是「尋租」?草民也不知道。克魯格在《尋租社會經濟學》認為:利用資源通過政治特權構成對他人的損害大於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定為–尋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干粹就把壟斷與偷竊類比,形成壟斷的活動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對壟斷的指控,面臨龐大的律師和法律程序。持續談判的花費非常大,因為稀缺資源的獨特性質,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計擠入壟斷活動中。成功的壟斷者明白:贏家有所得,輸家有所失。收入轉移不是直接帶來的福利損失,收入轉移是引發人們竭力獲取或阻止這種轉移。我們預見:為爭奪這種轉移的「浪費」性投入也非常大,以至無法測算壟斷的社會成本。偷竊本身是一種轉移,沒有福利成本。偷竊的社會成本是防盜私人保護和警察保護的公共投資之合。只要存在偷竊活動,就會有大量資源被轉移到實際相互抵消的活動。 每一次成功的銀行劫案將激發盜賊加倍努力,銀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會成本非常之大。
精英和媒體不顧一切的給富人臉上貼金,「中國有多少億萬富豪,中國多少富人的排行榜。」 學人放棄社會的責任後,最終惡果就會降臨。誰為窮人說話?中國精英已演變成什麼東西?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眼睛還向下瞅,20世末,知識分子眼睛全衝上了,中國精英自1900年一百年來背離民眾最遠的時期,假如中國精英全都找一個富爸爸,或自已就想當富爸,那麼窮人也會把權貴精英們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布爾迪厄說,知識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資本」這樣一個稀缺資源。也就產生了福柯所說的話語霸權,話語本身成為一種權力。精英處在大分化時代,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相比,他們善於表演,容易動搖,受名利誘惑,更容易被收買。留美學者程曉農(方國良)先生在《當今社會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國知識精英「商務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據知識精英與各種利益集團相結合狀態劃分的。在精英的觀念明顯分化的情況下,精英們很可能分別傾向或認同於某一知識精英群體的觀念,這是部分知識精英「智囊情結」越來越重的原因所在。韓曉萱說:中國知識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1.坐而論道。2.爭論偽問題,3.為當權者獻策。北大陳平說:經濟和學術多元化的發展對社會有利。多元社會的特點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協。學者可以公開地為利益集團發言而無須掩飾。精英在極力妖魔化草根並仇視工農大眾,一些精英及主流媒體,懷著對文革的恐懼仇視工農大眾,建國後及文革中知識分子曾被妖魔化多年,精英對亞文化的總體判斷,認為亞文化的破壞性遠大於建設性,並沒超出自古的「暴民、賊匪」之說。改革開放長期忽視犧牲工農利益,在決策上向利益集團靠攏。精英「通往被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警句,卻變成知識分子的一個理論怪圈和眼睜睜的陷阱,他們常依附於某一個階級,常被權貴所利用,「御用」或「幫閒」。他們還不構成經濟實體,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以知識為中介交換,從而獲得自身的價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鬥士,卻吸著外國資本的奶,搖身一變好像自已就成了高官權貴一樣。精英們為利益集團獻身服務同時,招致非議也就愈來愈多,精英的聲譽也就越混愈低。
腐敗與暴力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總是時機已逝,人們才想起「改革」了。制度改革愈遲,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越大。反腐敗最終要靠制度改革,反貪殺一儆百已失去威懾力,加大財政負擔和社會成本,(紀檢、監察、糾風辦、政法委、中央特別稽查),反腐敗已變成權力鬥爭的一種武器。小打小鬧不起作用,大干會使體製麵臨綜合風險。近10年來決策者幾乎陷入兩難境地,決策者徘徊在推行高風險的全國改革和無所作為兩個極端之間。完全可以搞一搞特區試點,特區的成功也將為進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礎。1、減少政治風險;2、減少社會成本和財政壓力;3、為政治制度改革掃清空間。費正清50年前說過,共產黨遇到的最大麻煩是如何保持他龐大的文官糸統的廉潔。中國遇到了腐敗最瘋狂的內部進攻和外部挑戰。
哈貝馬斯訪華時,感到中國精英有為利益集團辯護的傾向。中國知識分子經常對無良現象、不法行為進行猛烈抨擊同時,一有機會,他們馬上就可取而代之,精英比官僚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做不成「御用」,也幹不了「幫閒」的精英,皓首窮經在忙啊在寫啊,我偶爾看到梁漱溟在民國36年在河北定州所做的「鄉治」實驗報告,與1997年以來民政部大搞的村民直選別無二致,何清漣女士在《歷史的鬼弔》中說,民國33年的安徽教育廳檔案中有些關憲政的論文,跟90年代精英們大談民主威權何其相似,幾乎沒有歷史空間的阻隔,旦歷史的鏈條生生中斷了50年——–
知識、財富、地位等資源本身就傾向於官員,或接近官員的人,文官和學人本出自同一條根,走同一條道,方向略有不同。雙方的符號糸統也很相似,信息傳播學上叫 「准文官糸統」。中國教育功能為學人當官做了長期的準備,自古有「學而優則仕」之說。清華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者之間可轉換性有重要影響,……在對中國社會資本轉換類型研究中,我們發現一種和撒列尼的轉換類型相當不同的資本轉換類型。對於這種資本轉換類型,我們可以稱之為『圈內轉換』。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佔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眾多社會階層的利益。
信仰是一種終極需求,也是人類最基本需求。50-60年代對人文教育的破壞, 20年來被顛覆的最徹底最體無完膚的就是價值觀,一個國家20多年沒有信仰,構成價值觀的幸福觀、英雄觀和生活觀全面向傳統回歸,幸福觀變成了福祿壽,英雄觀變成江湖大俠,生活觀充斥著嚴重的痞子化和虛無主義。低級庸俗下流的尋樂主義、東方神秘主義不一而足。人類歷史上對精神追求–古希臘求真、求美,古希伯萊堅持信仰,中國自古以來的仁愛精神,都變得越發遙遠。沒有信仰,社會就失去規範,不規範導致不均衡,不均衡導致衝突不斷。人們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廣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臨十分尷尬的局面。公安大學靳高風認為:失去信仰,建設法制社會可謂「蜀道之難」。罪與非罪,守法和違法,公與私的混淆,價值觀預期的紊亂,使社會無序和文明衰退。當官場腐敗發展到猙獰的地步,學人作偽肆無忌憚(評職稱、出書),高考做弊(買文憑)。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教育和法律和雙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預期紊亂,防止窮人不滿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從廣意上講,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貧窮,二是防止犯罪。而現在的教育成了脫貧致富的唯一手段。
精英的大分化早已發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虛幻的憂患意識、理想主義,從人文關懷、憂患意識、啟蒙主義進入主流社會,90年代精英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尋找最低成本進入主流社會,否則即被邊緣化。經過10多年,他們的符號已經完全不同,語境也支離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種專家圈子,圈子內,他們象白癡一樣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權力、追逐資本,傍大款、傍大官,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無耐。精英傍上權力加資本,儼然成為壟斷資本或國際資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論戰中,利益背景影響削弱了所有的建設性,凡牽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學術爭論。中國精英與利益集團、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繫。利益的糾葛使爭論流於感性階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對弦外之音的測度上,以致發展到人身攻訐。理論的勝負不重要,要緊是贏得決策層,最終誰佔上風,還架不住實踐的檢驗。精英追求名利,為官、經商、再不濟也得跟著媒體瞎起哄,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要麼接近權力,要麼接近資本,接近「草根」能撈到屁!知識精英在爭奪話語權之戰中,昔日的同道可能會成為宿敵。
精英拿人民幣、拿美元、拿盧布,那口氣絕對不一樣的。精英全面放棄社會責任以後,將是全社會的腐敗與徹底墮落。古人云:士大夫無恥,謂之國恥。
凡是自栩為時代精神領袖的傢伙,不是賣假藥,就是歪理邪說。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