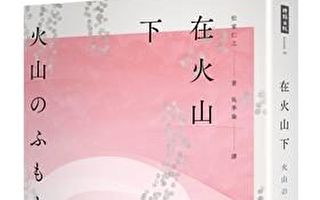這個世代一定要觀看的35部電影,你,看了幾部?
「燈滅幕啟,上映的不是電影,而是人生。」
*有時候需要記住的,是那回憶的心情~~《腦筋急轉彎》
回憶有時候太重,記得了,跑不快。但回憶也給我們力量,沒有它,飛不高。這當中的幽微忖度,人生百態,經驗的褪色和不願化作塵沙,要幾歲的孩子才能懂?
《腦筋急轉彎》(英語:Inside Out)的十一歲主角萊莉(Riley),跟著爸媽剛搬家,她必須要適應新房子、新學校、新城市,但是她好不安。她好想念原本的家,想念死黨和校隊,甚至突發奇想,要回去原本的地方……
有些電影,你一看完就知道自己不一樣了。看世界、看自我和他人的目光,都不再相同,《腦筋急轉彎》就是這樣的一部片。它說心理,談記憶,但其實緬懷的是童年,記錄著成長。它把人心的五種情緒:快樂、憤怒、恐懼、噁心和悲傷擬人化成五個角色,這五個活寶在大腦總部指揮著萊莉處世,所有的經驗則形成一顆一顆記憶光球,儲存在腦海深處,特別重要的還會催生一座座性格之島,驅動她的人格。
這是一部讓人看完,覺得自己「長大了」的電影。真正的故事不在劇情,而在萊莉的腦袋裡,在那情緒/自我的創造和處理、儲存的大工廠。真正的問句不是「她經歷了什麼」,而是──「她為什麼這樣想?」
我們總是好奇別人腦袋在想什麼,更常惱怒自己的言行不受控制,如今《腦筋急轉彎》試著解釋心情、言語、羈絆和夢境,而且說得極好。我甚至相信它會形塑我們這一代對內心的認知。
且看:那五個活蹦亂跳的傢伙「為了萊莉好」,爭相主導她的言行,樂樂(Joy)永遠樂觀亢奮,恨不得所有應對都讓她經手(當然囉,我們誰不希望自己永遠開心?);厭厭(Disgust)和驚驚(Fear)卻不時插手,意味著保護自己的本能;怒怒(Anger)更不用說了,當他執意出頭,沒人能擋得住;至於憂憂(Sadness)看似低調,卻一直忍不住東碰西碰;他們不只是萊莉內心的小聲音,這整個團隊(as a team)就是萊莉本身。
當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萊莉顯得猶豫不決,當負面的情緒(如厭厭)要「拒絕」他人,樂樂會先試著友善、婉轉地協調人際。他們還會「重播」某一段回憶,基於思念或是警戒,讓萊莉想起特定的經驗,供當下參考⋯⋯
當一顆光球生成,會先放在短期記憶區,待入睡後被送到長期記憶的大倉儲。在那裡,如果一直沒被召回,就會掉入遺忘的深淵褪色、風化成灰。記憶庫和指揮室之間還有思緒的列車(Train of Thought)不斷在穿梭——當我們努力要「想起」某件事,那攀住一絲線索不讓飛散的著急,不正像在趕火車嗎?
這一切像個五彩繽紛的遊樂園,當萊莉情緒起伏,園內風雲變色,甚至地震震垮列車的軌道,意味著「腦袋一片空白」。而年幼萊莉的記憶都是單色(單純)的,且多數是金黃色(快樂),到了片尾經歷成長,那些晶球變成雙色、三色混合,意味著「複雜的心境」了。
《腦筋急轉彎》不只分析童年,還緬懷它,它說成長、遺忘和記得,說留下什麼回憶我們就變成怎樣的人,它說其實流淚是不要緊的,示弱是不要緊的。
電影後段有兩個轉折,先是配角Bing Bong犧牲自己,幫助樂樂逃出潛意識,牠象徵著童年的幻想,不被理性和邏輯馴化的想像力。那曾經煞有介事,無邊無盡的編織,如今連細節都想不起來了,更遑論「相信」。但這故事告訴你:有時候需要記住的,是那回憶的心情,不必是回憶本身。那童年任性/盡興的笑聲,是一顆顆發芽的小種子,也許哪天掉入深淵的時候,會拉你一把。
更重要的是,它讓樂樂代替迷信正能量的你我「懂得」了憂憂。後者說:「哭泣讓我慢下來,好好煩惱人生沈重的問題。」她也說:「我看他難過,所以陪陪他,聽他說話。」
悲傷是整理,是抒發,悲傷也是「悲觀」,但悲觀帶來實際,可以在某些時候真正解決問題。而情緒不只構成記憶,還決定你我和他人的互動。所以悲傷是示弱,是召喚外援的笛音。
《腦筋急轉彎》最後,傷心的情緒接管萊莉,換來家人的擁抱,也縫合了歸屬。據說在構思過程中,導演彼特.達柯特來回磨了四年,才把概念落實成故事,這中間他一度挫折得想離職,又捨不得並肩作戰的老友。這讓他悟出了:悲傷是求救,而身邊人的扶持,是你我所擁有最美好的東西。
當樂樂明白了即使是快樂的回憶,也可能因為「不再」而變得感傷,這時候我們只能哭一哭,然後放下它。就像那粉紅色棉花糖大象,有些童年不可能永遠打包帶走,但它們可以被沈澱,被萃取,變成心底的誓約,靜靜閃亮。而流完淚才有清晰的腦袋,從中學習時光的必然,和無常,進而珍惜美好——這就見山又是山,真正地長大了。
在《腦筋急轉彎》的最後,有一行字寫著:「這部片送給我們的孩子,請永遠不要長大。」童年是最單純無憂的,失去了固然失落,但不會真正逝去。
曾經發生的不會忘記,只是想不起來而已。記憶可以再造,可以置換,可以重啟核心,最放不下的還可能被喚醒。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是由我們遇見誰,想過什麼,經歷了多少故事決定的。
而我們抱著初心飛高高,終有一天會在俯瞰來路的時候,明白人生百味,欣賞五色交融,在下一次面對攀不上的高峰時,為自己唱起彩虹之歌。這是二○一五年我最愛的一部片,也是因為電影長大的我們,給記得和不記得的每一個自己,最好的祝福。◇#(待續)
<作者簡介>
張硯拓
影評人,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評審,多次舉辦講座和電影導讀。
——節錄自《剛剛好的時光》/三采出版
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