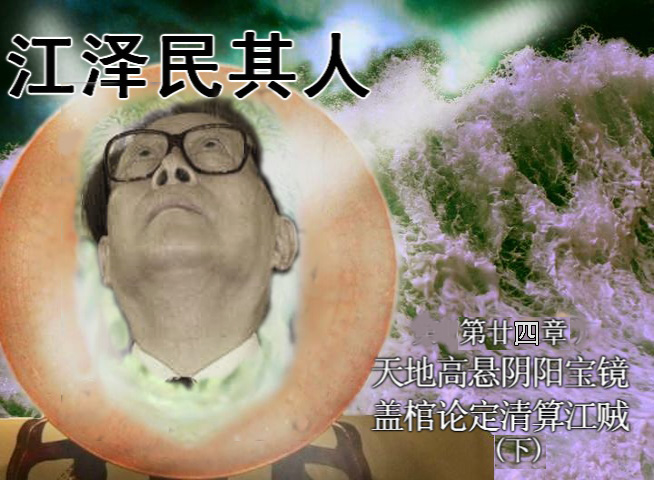【大紀元2017年09月24日訊】近期有陸媒報道,「在教育部北辦公樓的五層,有一間『4%辦公室』」。據媒體所稱,「這是中國為數不多的以數字命名的政府機構」。既然如此罕見,大家就會猜想,它的存在一定有著某種特殊的意義。
對此,陸媒是如此介紹的: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要在20世紀末達到4%」。「2012年,4%的目標終於實現」;「在這20年的努力後,國家才真正有了建立『4%辦公室』的基本資格」。也就是說,政府為了慶祝達到了4%的目標,並想藉此向公眾證實和炫耀自身對教育的有所作為,才特意打造了這樣一個標誌性的辦公室。
我們且不說,公開財政預算和支出本就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職責和義務,有必要為此成立一個辦公室來加以註解和強調嗎?相比「世界平均7%左右」以及「發達國家達到9%」的水平,中國有何理由對長達20年才最終實現的4%感到如此榮耀?此外,相比GDP趕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勢頭,中國在整整20年間,都無法做到將GDP的4%投入到民生之大計的教育中來。因此,如今這般慶祝和炫耀也只能反襯出中共多年來執政的失敗與無能。
話說快要餓死的,終於吃上了飽飯,這的確值得慶祝一番。然而關鍵問題是,4%的教育投入真的彌補了中國孩子在教育上的短缺與不足嗎?來自官方的說法是,「4%大盤子的分配,更多的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傾斜」;「國家有了這3萬多億,就能更合理的進行分配,在分配中體現更多的教育公平」。
相比官方所言,現實情況顯然並沒有那麼樂觀。就在今年6月,一項針對100個縣9200多所農村學校營養餐情況的監測報告顯示,有近半數學校的營養餐沒有「基本達標」。要知道,這個營養餐計劃是國務院致力於「消除貧困」,早在2011年就開始啟動的,並且「中央財政累計投入了1591億元專項資金」。然而5年後的結果卻顯示,投入與成效呈現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投入不夠,還是執行上有問題?
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學生的吃飯問題?教育投入只需保證孩子有書念、有學上即可。然而,2016年官方的報告卻指出,「中國大陸農村地區整個中學階段學生的累計輟學率高達63%」。相比之下,這一數字在2005年時只有43%。也就是說,對教育的投入雖然多了(2012年已達到4%),但學生的輟學率卻不降反升。顯然,這與中國農村普遍存在「學生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的現實難題一直未得到解決有關。於是,我們這才發現,相比投入金額的多少,如何一分一厘、恰如其分的使用這筆投入才是關鍵所在。
在中國,財政對教育的撥款是否達到了4%,甚至超過4%,其實並不是當務之急。對於教育經費,首當其衝應該解決的,是中央的投入一旦下撥到地方,這筆錢是否真的會分配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而不是多半進了官員的腰包。此前已有人一語道出,「執行好不好,關鍵在領導」,由此足見,教育部大員對財政經費的絕對掌控力。
在如今「一黨獨裁」的體制下,部級大員們這種絕對的掌控力,負責撥款的中央又如何不知?因此,在反腐大潮中,來自中央的「如何守住4%的底線」、「4%能不能保得住」的設問或許更像是一種提醒和暗示。上述「底線」一詞就已表明,4%既是教育部可以擁有的活動空間,又是其不可逾越的界限。這「4%辦公室」就如同警鐘,時刻警醒著教育部要牢記,無論為私為公,中央能給的就只有4%了。
說到底,中國人民上交的財政始終不能由人民來決定怎麼用,甚至最終都用不到人民身上。從長久以來教育支出已成為中國父母們所肩負的大山之一就不難看出,中央的投入即便多了,也無法減輕學生家長們的負擔。
要想4%的教育經費切實的「用之於民」,就不該在教育部的大樓裡成立什麼辦公室,而是應在「權力」之外,公開設置由人民來監督的辦公室。然而,成立這樣的辦公室卻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權力中心本身也得由民選產生。因為與民主相悖的獨裁政府是不可能心甘情願來接受人民監督的。#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