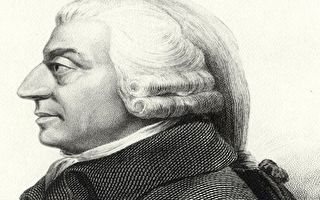【大紀元2018年11月06日訊】一般都同意,經濟學自1776年就成為一門既可教、又可學的「學問」了。最早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較被熟知的中譯是《國富論》。但此譯名會對保護主義、將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視為戰爭、國際間的紛爭、甚至戰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也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達的內涵,因而使用這個早年的翻譯名家嚴復之最初譯名較妥切),作者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經濟學之父」的美名。
在亞當‧史密斯和《原富》的開創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先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4)、馬爾薩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爾(J.S. Mill, 1806~1873)等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繼而在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為新古典學派。由於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提供了供需圖形等分析工具,經濟學的教學講授更為方便,這門學問也就粲然大備了。一直到今天,眾多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都還沿用該書所創的分析工具呢!
1930年代,經濟學有了重大變革。主要因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引發迄今世人還聞風喪膽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一時經濟蕭條、失業者遍布,直到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1936年的巨著《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問世,才提出「創造有效需求」解藥。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也開啟了「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1901~1985)和有「國民會計之父」稱呼的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 1913~1991)發展成形,更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物質性」國民所得(GDP)成長的依據,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財經消息報導,幾乎都是總體經濟的範疇;而經濟學也的確在總體經濟學誕生之後,才成為顯學。
最暢銷最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
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雖是好書,但講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經濟學》(Economics)。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分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Jevons, 1835~1882)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隨後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發展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69年首次頒發,得主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第二屆得主公布,又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這就更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具備了「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當然,讓政府扮演經濟舞台要角的總體經濟學,加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促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夠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預經濟主角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被稱為混合經濟大師–的貢獻,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場失靈」因而產生,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來達到福利最大的論述,這也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礎。稍後,當「賽局理論」興起,數理化又更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趨勢看似沛然莫之能禦,不過一直以來,反省的聲音還是不時出現,屢見不鮮。
讓經濟學回歸「人性」本質
1949年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無論是質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段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十三年後,米塞斯又在《經濟學的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寫著:「如今在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這個叫人誤會的名稱傳授的那一門學科,毛病並不在於任課的老師和教科書的撰寫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經商失敗者。而在於他們不懂經濟學,以及欠缺邏輯思考的能力。」這不啻在為上一句話提供答案。
奧國學派一向反對經濟學數理化,米塞斯告訴我們:「許多撰述者誤以為,人的行為科學必須仿效自然科學的方法,所以致力於某種量化經濟學的工作。這些人認為,經濟學應模仿化學,從定性分析進步到定量分析。他們的座右銘是實證論的這一句箴言:科學即測量。他們獲得豐沛的基金支持,汲汲營營於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業公會、大公司和其他企業所提供的統計資料,他們努力計算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之間的算術關係,藉此來決定『相關』與『函數』的一些東西。他們未能意識到,在人的行為領域,統計永遠是歷史,而他們所謂的『相關』與『函數』,除了描述某一段時間和某一區域的某一群人行為的結果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
所以,米塞斯就說:「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經濟學家的理論,並非建立在歷史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邏輯學家、或數學家那樣的理論思考上。…經濟學家的確能夠像邏輯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窩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來完成工作。使他有別於其他人的,並非他有什麼秘密的機緣,得以處理别人接觸不到的某些特殊資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夠從中發現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不過,米塞斯在書中特別澄清:主張經濟學不應模仿、以其他科學作為榜樣,並非鄙視或無視這些學科,相反地,必須努力去理解與精通這些學科。他說:「任何人若想在行為學方面有所貢獻,那就必須熟諳數學、物理學、生物學、歷史學和法理學,以免將行為學的任務與方法,同任何其他這些知識部門的任務與方法搞混了。」他又舉例說,形形色色、所謂數理經濟學的基本謬誤,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基本謬誤,沒有哪一位「合格的」數學家看不穿。
當今數理化、量化、數字化不但是經濟學主流,也是所謂的「科學」,而「拿出(數字)證據來」更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詞,政府各種政策也都是以此為基礎提出的。或許大家琅琅上口的「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追其源頭就是經濟學被誤導呢!就讓我們好好讀讀米塞斯的這本書參悟參悟吧!!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