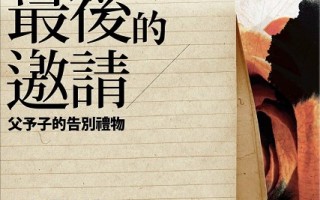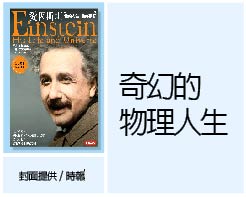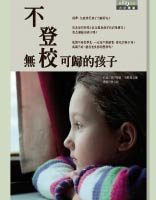我開始寫「思鄉草」遠在50年代,那時我們全家住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市。
「思鄉草」每一篇都很短,只有一兩千個字。那是應一家華僑的中文報紙副刊編輯的要求才寫的。我沒有每天都寫,大概是一周一兩篇,好像專欄的文章,有許多人愛讀。可惜登了不久,華僑社會有人散布謠言,說是有鼓勵華僑回大陸的嫌疑,就不許我再發表我思念家鄉的散文。
其實當時的馬尼拉市前後只有三個江陰出生的人。第一個是東門的吳研因。他派來馬尼拉名義是視察華僑學校的教育專員。第二個是南門的邢光祖,他是中央社的特派記者,也是一家華僑報紙的編輯。第三個就是我,出生在北門的朱一雄,華僑學校的教員。
文章既不能發表,我亦不再寫我的「思鄉草」。那些發表過的我剪下收藏,後來我們幾次搬家,竟把這些剪報丟失了。到了美國,住在薛那度亞的山鄉三十多年。除掉寫了五十多篇的「草葉堂隨筆」,又開始寫「思鄉草」。「草葉堂隨筆」陸續在上海、台北、馬尼拉的報紙發表。因為我寫的是美國山鄉的生活,大家都覺得有趣。至於「思鄉草」的文章,只限於我的家鄉,又是幾十年以前的舊事,就沒有機會和讀者見面。
我所思的鄉是我的鄉,是我兒時和少年時代生活的地方,當然內容全是往昔,又多半是紀念生我育我的父母和哥哥姊姊的緣故才寫的。到今天,只有我的小姊姊和弟弟在世,其他的都早入黃泉,沒有在人間留下什麼蹤跡。所以我寫這些文章無非是要讓人們知道這些影響我整個人生的人,他們的靈魂何等的美麗,他們的苦難何等的深沉。
「草葉堂隨筆」裡,仍有許多我思念家鄉的意念。朋友們看到我們山鄉的園地有十多棵大楓樹,曾經建議我用「丹楓」為堂名,寫在我的書畫作品上。他們說我從前在國內抗戰期間發表了許多木刻版畫署名為「丹鋒」。「丹鋒」和「丹楓」發音相同,應該很合適。可是我覺得「丹楓」兩個字似乎太平常,也許已經有人用過。園子裏野草叢生,每一片草葉都有它們的特色。『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正好是我住處的寫照。因此我決定用「草葉」為堂名,而我的隨筆亦都是寫這「草葉堂」的故事,我和「草葉堂」的悲歡離合。
如今「草葉堂」已經成為廢墟,成為歷史的一頁。滄海桑田,一切都已消失。我希望能靠這本小冊子,在世上為「草葉堂」留下些痕跡。
美國朋友聽到我的「草葉堂隨筆」在台北印刷出版,全書都是中文,非常失望。他們希望我把它譯成英文。但願我雖老邁,仍盼望在不久可以由我完成英譯,給更多的人知道「草葉堂」的往昔。◇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