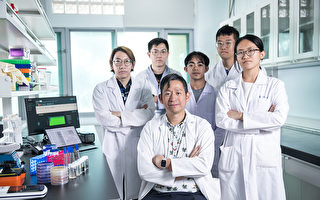【大纪元5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台北报导)在台海两岸颇富知名的小说家严歌苓,随着美国外交官夫婿在台湾定居已经三年,她的夫婿任期届满,他们将离台转赴欧洲。在美国在台协会的邀请之下,4月30日下午在美国文化中心,严歌苓以“为讲故事活着”(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为题,畅谈她创作小说的因缘,以及具备哪些特质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
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12岁(文革期间)考入成都军区,参加解放军,在一文工团当了八年的舞蹈演员;20岁在中越战争前线当过战地记者。1986年在中国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第一次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青年写作。1989年赴美进修,获有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艺术硕士。
1991年以〈少女小渔〉获中央日报文学奖,并引起文坛和电影界重视。1993至1998年,连续获得台湾多项文学大奖。作品译成英、法、荷、日等多国文字。2006年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说The Banquet Bug(中译书名《赴宴者》)。除了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严歌苓也参加“美国影剧作家”。
题目灵感来自马奎斯的自传
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奎斯,是严歌苓最崇拜的作家,马奎斯有本回忆录《为讲故事活着》(Living to Tell the Tale),提及苦难越多的地区,人的日子不好过,故事就多,作家就越多。马奎斯出身南美哥伦比亚,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整个社会的走向常常是未知的,人的生活当中变数非常大,于是产生戏剧性、张力,很容易写出极致下的人心。
严歌苓说她生长在五十年代末,中国正好走进了思想意识型态的斗争──反右;生活上则有三年大饥饿,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有很多没有被证实的鬼故事、恐怖故事,她和所有的大陆中国人的物质非常贫乏,但是故事非常丰富。
八、九岁时,她父亲是反党作家,工资遭银行冻结,停止发工资没钱,他们那一帮孩子就结伴在下雨天去买菜,常常能捡到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掉在地下没有声音,人家就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穿拖鞋上街,人家就叫他们拖鞋大队。
他们那帮小孩有一种反社会的情绪与愤怒,为什么父亲会这样?生活会这样?也没有学上?常常拿着一把很有力的大伞,去刮人家的纸雨伞,学会了去搏斗、抢东西、偷窃。“很早我们就经历了人性的两大堕落──撒谎与偷窃,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不撒谎就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
当时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五十多位艺术家住在他们院子里,其中三十多位是反革命,要派军队的宣传队、工宣队、学生的宣传队这三种人,来进驻管理那些艺术家。他们每天都要问起小孩,你爸昨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他们就编出很多话来讲,“我爸昨天晚上在家里抱怨共产党能讲吗?”她说那些是非常不幸的经验。
严歌苓表示,身为作家来讲,很早就看到,人在你面前可以表演很多面目,你也可以在别人面前戏法他们,这样就看到很多可能;我说假话他会怎样,说真话会怎样,这对她来讲是很好的作为小说家的训练。
“所以我从生下来到今天,都是在戏剧的漩涡里转,文化大革命看到各种各样人的嘴脸丑行,今天是朋友,明天就背叛,各种各样血淋淋的东西,每天都看人跳楼,我从五十年代末期到后来的经历,不同于任何人的经历。”
在西藏高原与中越战事前线
12岁去参军,她敏感的程度到了军队以后,不能表达私人化的形式,否则会觉得自己很得罪人,然后她收敛起来,不敢表达,担心万一又得罪人,就格外的内向。
譬如她小时候爱讲俏皮话,在西藏高原见到有个女兵穿的很少,她说:“你是耐寒作物。”这位女兵觉得很受侮辱,怎么这样讲。她看一个人唱歌,牙齿缝很稀,就说:“你这个西班牙女歌手。”又得罪人。她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表达,她才发现不行,那不是爸爸他们艺术家的地方,他们不会讲她很幽默很好玩。
到了西藏以后,很多事情靠她自己的内向记忆储存起来,消化掉,变成形象。她们每年都要到西藏演出好几个月,后来写些西藏的故事,真实的原始形象都给了故事很多养份,不能够知道的空间用想像力去填满,最后变成一个个故事。
20岁时,到中越自卫反击战,严歌苓去了一个野战医院的包扎所,一夜之间接受一千多个伤兵,很年轻的小战士,大概18-19岁,全都是残废了,整个走廊里有一股血的味道。
她采访一个小战士,地雷把他下半身全炸坏,没生殖能力。他是孤儿,从小订了娃娃亲,他的丈人把他养大,他唯一对丈人的报答是退伍后去做他女婿,他不能生育就变成无法报答他丈人。
当时医生检查他,碰触他腋窝,他咯咯笑了起来,当时严歌苓觉得他活了,不会寻死,因为他笑得挺开心的,像孩子一样。后来等回到成都,第二次又去前线,他们说小战士自杀了。那些事情给严歌苓刺激很大,从此以后她就反战,不再相信战争的意义要比人的生命价值还大。
“这些就是我在青年时代、少年时代,involve(融入其中)的戏剧,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戏剧,我被围绕在戏剧里,同时也被创伤了。”严歌苓说道。
放下跳舞 开始写作
20岁时,严歌苓从前线回来以后,就不跳芭蕾舞了,突然发现有比跳舞更大的使命。过去她想加入共青团,被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她说:“我要做独舞演员。”对方说:“你的理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吗?”就没有让她入团。
到前线之前,她家庭的教育很好,父亲是个作家,家里有很多书,《红楼梦》很早就读了,所以对人的感情、人性、世界上的经典,大致都知道。小时候读书,字认不全,不过严歌苓大致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就翻好看的地方看,《战争与和平》巨作,她只看和平不看战争。
中越战争打完以后,回到成都,严歌苓变得深沈,“跳舞的肢体表达,已经不能表达我了;我的表达想要更有力量,可以传达更远,我开始写文章。”
一开始写作,严歌苓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有爸爸帮我走后门,帮我投到杂志去,第一批作品就发表了。”她受到了鼓励,没经过退稿,就一直写下去。
1986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得了奖,1987年出版第二本长篇小说。1988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问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严歌苓才意识到中国作家挺不幸的,因为思想是被放在一个框架里。
到美国时,她到爱荷华(Iowa)青年作家写作中心,参观美国很多艺术家的基金会,观看那些青年作家讨论作品的气氛。严歌苓说:“我就觉得中国作家很可怜,他们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或发表什么,是有前题的,不能有自由的。一个作家不能有思想上绝对自由,就不能成为很好的作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向往美国。”
于是,她联系美国的学校,开始学英文,因为她觉得像她那样人文素质的人,中国的人文环境对她来说很不适合,经常会讲当局不爱听的话,当时她跟军队的系统比较近,军队也是不适合她待的地方。那时候爆发了六四,给了她最后一次的失望,不能在这个国家待了,一定得必须要走。
倾听故事与追问细节
经历了不断的起伏跌宕,生活有巨大的落差,给她留下了很多的故事,严歌苓觉得作为一个爱讲故事的人,首先是个好的聆听者(listener)。她有一个朋友,常会讲很多废话,但一百句废话里可能有一两句非常好,有很好的细节,不可能编造的;所以她就套上耳机,用一双非常同情的耳朵在倾听,边烫衣服边听电话。
她在讲故事之前,就听了各种各样故事,听民间故事,听外婆讲些莫名其妙的故事,狐狸精的故事等等。严歌苓认为每个人都藏着好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好书,任何人让他好好跟你讲,都可以发现很好的个人历史,都非常精彩。
“我对所有人的故事都特别的感兴趣,眼睛看到的是观察,我现在写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充满细节。”譬如写《第九个寡妇》之前,她到河南农村,就追问:“你吃树皮,榆树皮怎么采下来?”对方就跟她每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榆树皮采下来如何弄碎、磨成粉,最后成为什么状态,她就搞的很明白。
她倾听人家的故事,会设身处地听的非常入迷,也会非常难受,难受很多天,甚至好多年。“能否成为作家有很多东西都要先天决定的,你的同情心有多少,跟人家共感能力有多少,共感能力是写作时,确实站在人家的立场上,你经历一遍他经历的事情。”
“我是非常有训练自己的人,几乎没有一天是在虚度光阴,每一分钟我的雷达都是打开的,非常高度敏感。”她写的人物经常是混合著一些人的细节、形像、身世等,没人能发现最后张三是谁,李四是谁,她说要不然很不道德。
好小说家 会说故事之外
活到知天命的岁数,严歌苓表示,写到今天觉得最大收获是,找到跟自己性格、所有的一切状况都很吻合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满足。她非常欣赏作家这种生活方式,使她独立思考,不听评论家对她作品的好评或坏评。只有作家可以这样的生活──读书、写书,作者跟书在交流,她可以到老也是这种生活方式。
不过,她也警醒的想起在学校时老师的话,有位教欧洲与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老师,曾在严歌苓班上说:“你为何而写?你认为世上还需要你这本书吗?”(Why do you write? Do you think the world needs one more book?)因此她会先想,“这世界需不需要这样的故事,我要写这样故事的话,故事之外的意义是什么?”
“写每个故事,除了告诉读者这个故事之外,还想告诉点什么,这不是我一下能说出的,要通过我对语言的追求,对人物的塑造,然后一点一点,好像它出来了。”
撰写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严歌苓认为,每天她都能听到或从报纸上读到故事,特别是大陆现在有几个频道专门在讲些民间骇人听闻的故事,有很多故事比能够发动想像力到最最强的地步还要惊世骇俗,所以仅仅会说故事是不够的。
“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有在故事后面的信息是什么?如果这信息讲的很清楚,那不是小说家而是通俗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在你所有的形象和盘托出之后,每个人根据他的情感、背景、立场,得到张三李四不同的讯息,你就成功了。”
严歌苓说她还会继续讲故事,还有些故事没写出来,还有些精彩的故事等着她写,还有些故事尚未说服她,它将来成为一个故事,在故事之外的价值有没有,所以还不知道是否会写那样的故事。
这天前来听讲的听众,有远自美国的话剧编剧家沈悦,严歌苓说她在美国时常看沈悦的剧。也有出版《少女小渔》的尔雅出版负责人隐地,这是十几年前在台湾首次发行她的小说,后来拍成电影,当时给了她很多鼓励。还有电影导演李安的弟弟李岗,也是位导演,以及出版数本她的小说与套书的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等。严歌苓说:“看到老朋友们,感觉像个家庭聚会一样。”
演讲之后,她回答现场读者的问题──〈如果能选择人生 严歌苓想当医生或科学家〉。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