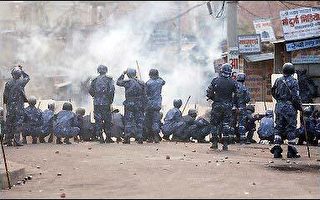【大紀元4月17日訊】近來陳水扁先生的「廢統」、「終統」,在華人圈和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大陸的許多朋友也捲入這場紛爭。但問起所「廢」所「終」之「統」究為何物,則論者昏昏而知者寥寥。
1990年10月7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親任主任委員;同年底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1991年2月23日,制訂《國家統一綱領》,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主張中國的統一,「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建議「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下,為增進兩岸人民福祉:大陸地區應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建立均富社會」。
海基會1991年3月9日開始運作。11月4日,派秘書長陳長文到北京,促成大陸於1991年12月成立對應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並於1992年開始兩會談判。第一次談判1992年3月23日在北京舉行,議題是:文書公證和掛號信函遺失的查詢、補償。
當時,台灣己開始民主化改革,實施憲政,政府行為必須接受議會的質詢和監督,海基會稱民間機構,為了不違背憲法,在議會反對黨的抗議聲中,被限定只能進行事務性協商。但是,大陸海協會在會談中,要求海基會接受「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作為簽訂協議的前提。海基會以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為由,拒絕接受和協商「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第一輪談判失敗。
為挽救破裂的兩岸談判,李登輝同意接受「一個中國」,遂由海基會致函海協會,要求海協會澄清「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出乎意料的是,大陸拒絕澄清「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復函稱:「海協會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兩岸事務性協商因此而轉變成「一個中國」涵義的政治談判,也就成為是選擇統一還是選擇分裂的政治談判。
1992年8月1日,李登輝主持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涵義》決議案,內容為: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台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二、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三、中華民國政府為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能與力量。
台灣「國統會」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涵義》決議案後,大陸對台辦、海協會發表聲明和談話,重申兩岸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至此,雙方均亮出底牌,雙方的立場如下:
大陸方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涵義,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底線是井水(民主)不犯河水(專制)。
台灣方面: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中國人,對等,和平民主統一。底線是對等。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舉行文書公證和掛號信函遺失的查詢、補償第二輪協商,由海協會副秘書長周寧與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主談。雙方交手了下面四個回合。
第一回合,周寧首先提出討論「一個中國」問題,許惠佑以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為由拒絕。
第二回合,周寧再提出「一個中國」問題,許惠佑讓周寧澄清「一個中國」的涵義,周寧以事務性協商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為由拒絕。
第三回合,雙方各自提出五個書面表述「一個中國」的方案,雙方各自拒絕接受對方的方案。
第四回合,為縮小分歧,海基會提出三項修改表述方案,並建議如不能達成協議,可各自口頭表述,周寧無權決定是否接受口頭表述,大陸海協會退出談判,談判破裂。海基會三項修正表述方案是:
一、鑒於中國仍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二、海峽兩岸文書查證問題是兩岸中國人間的事務。
三、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香港談判破裂後,10月31日,台灣陸委會副主任馬英九發表談話,表達立場說,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上,中共如果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們吃掉,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方不能接受不加注說明的「一個中國」原則。
11月16日,大陸海協會致函台灣海基會,同意各自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告知海基會:「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 並將海基會三項修改表述方案的第三項作為隨函附件云:「附貴會於10月30日下午所提出的口頭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資料引自「凱迪網絡•貓眼看人」三百門漁夫:《九二共識真相:大陸與台灣》,原標題:《九二共識真相:「陸獨(獨裁)」與「台獨(獨立)」》)
現在人們明白:所謂「統」,就是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在1990年成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和這個委員會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統一的主旨是自由、民主、均富。所謂「九二共識」,則是台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海基會認為「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則堅持「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共識」的要點卻是「認知各有不同」。
但馬英九先生早在13年半以前所說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上,中共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們吃掉」,卻是從諸多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一個先見之明。
「認知各有不同」的概念屬於「模糊的概念」。把本來明確的概念故意弄得模糊,則是「模糊概念」。前一個「模糊」是形容詞,後一個「模糊」則是動詞。「模糊的概念」和「模糊概念」統稱「模糊概念」,歷來是獨裁者的秘密武器。
1945年7月毛澤東對黃炎培先生大言:我們已經找到擺脫中國歷史治亂循環週期律的方法,這就是民主。這次談話除了令當時的黃炎培先生興奮不已,至今仍被一些人貫以「窯洞對」的美名。但毛澤東先生所說的「民主」,和黃炎培先生理解的民主,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當時毛澤東運用的就是「模糊概念」的秘密武器。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先生所說的「民主」,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或「無產階級民主」,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獨裁或者一小撮政治寡頭獨裁。
毛澤東關於民主的談話是模糊概念,而馬克思在156前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模糊的概念。當無產階級還是無產的階級時,他們是不能專政的;舉凡能實行專政的力量,絕不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理論,是一種攝魂術,使無產者和窮苦人民產生幻覺,以為他們能夠通過實行專政而掌握政權,為自己謀福利。
「言者無罪」源自中國古代文化,原意是發表與統治者不同的意見和批評統治者的言論都是無罪的。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有意模糊了這個概念,「言者無罪」變成了發表擁護統治者的言論和意見才是無罪的,而發表「錯誤的」即批評統治者的意見則是有罪的。
模糊概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缺陷,來自邏輯思維不健全。由模糊概念造成的歷史悲劇和人間慘案史不絕書。而在20世紀前半葉的「蘇區」、延安和1949年之後的大陸,模糊概念竟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是因為除了原來的模糊概念,又發明和引入了大量新的模糊概念。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就是古代的聯邦制,這種制度早在2200多年前就被秦始皇嬴政先生廢除了,代之以大一統的皇權專制制度。上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故意製造模糊概念,斷言中國的社會性質為半封建社會,為中國革命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務。五四運動時倡導「民主與科學」,針對中國專制與愚昧的現實。所謂的「反封建」,卻把反專制的主題轉移到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上去了,這就為後來保護並擴大專制主義埋下了伏筆。這是共產黨在20世紀製造出來的最大模糊概念。直到前不久,《中國青年報》復刊的「冰點」上,還使勁鼓吹「反封建」的陳詞濫調。
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在其《政治報告》中明確承諾:對於犯罪分子,「除了殺人、放火、放毒等反革命分子外,其餘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凡是殺人、放火、放毒的刑事犯,不論有無政治動機,全都貫以「反革命」惡謚。所以這個承諾本無歧意,就是除了殺人、放火、放毒這三類罪犯外,其餘的罪犯一個不殺。但「九大」過後不久,就接連下發「七三佈告」、「七二三佈告」、「八二八命令」等,大開殺戒,並且不斷升級,直到1970年初,掀起了瘋狂的公開揚言要殺人的「一打三反」運動。對九大報告中「一個不殺」 的承諾,則詭辯道:那個「等反革命分子」,就是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這樣故意的模糊概念,簡直連放屁都不如!
我過去講過一個故事:一群同行的人走到一條大河邊,面對如何渡河,意見紛紜,爭論不休。忽然出來一個聰明人,提議「採用最佳方案過河」。所謂「最佳方案」,就是超過所有其他方案的方案。至於具體內涵,大家不要爭論。於是一致通過。但具體實施時,分歧就出來了。有人認為最佳方案就是建一座橋,有人認為最佳方案就是造一隻船,有人認為最佳方案就是泅渡。這最佳方案原來是一個模糊概念。我的故事當時只說到這裡。直到後來那個聰明人掌握了一切權力,並且造成了橋,我才明白,所謂「最佳方案」,就是傾共同所有的財力,建一座最豪華的橋樑;從設計到施工,從預算到承包,全都由聰明人獨自說了算,財務不公開,不許查帳,不許批評;對於建橋過程中需要追加的資金,全都由大伙無條件供給。原來我以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什麼是「最佳方案」,後來才明白,一直被蒙在鼓裡的不過是我等愚民,那個聰明人卻是從一開始就什麼都明白。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說:「我們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什麼,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原先我以為,鄧小平先生能說這話,說明他很謙虛。現在我只能引用祥林嫂的一句話:「我真傻!」他早就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而「堅持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但是「堅持改革開放」,卻是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服務的,「一百年不動搖」。而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沒有完全搞清楚和完全沒有搞清楚的,是我們這些下愚之輩,而不是鄧小平先生和他的同僚們。
當鄧小平1992年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一些天真善良的人們忍不住又興奮起來,討論起「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法制經濟」,當然反對的一方也振振有詞。於是鄧小平及時拋出了他的一項發明:不爭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非是在「立國之本」基礎上的「強國之路」的延伸。十幾年的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國家政權壟斷下的市場經濟,政府繼續壟斷一切資源,個人的權利繼續被壓縮在最低限度;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正相反對。幻想市場經濟可以促進私有化和民主進程,不過一廂情願的白日夢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模糊概念,然而卻是對公認的市場經濟的模糊。
改革開放之初,善良的人們遺憾地認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條件下開始的。」官方宣佈:「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環節。」但為什麼大中型企業活力不足,卻不允許深入討論。「企業活力」對於包括經濟和政治在內的城市,對於渴望提高自己生活質量的人民,是一個模糊概念。在中世紀,成吉斯汗的鐵騎最有活力;20世紀,希特勒執政後,德國的經濟最有活力;中國90年代後期的「圈地運動」開始後,房地產業也一直最有活力。但這樣的活力和人民自由與幸福的增長有什麼關係?奧運會冠軍在賽場上表現出的活力,和躺在醫院門外求醫不得的病人有什麼關係?改革開放如果不能始終惠及下層人民,它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甚至值得詛咒的模糊概念。
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就是模糊概念。美國前總統裡根說過一句關於共產主義的名言:「如何判斷什麼樣的人是共產主義者呢,共產主義者就是那些閱讀馬克思和列寧學說的人;那麼什麼樣的人是反共產主義者呢,反共產主義者是那些理解了馬克思和列寧學說的人。」裡根先生的話只適合那些良知未泯的人,因而只說對了一半。那些置黨紀國法於不顧,拚命為自己撈取特權利益,在專制腐敗的道路上絕不回頭的共產黨人,也是理解了馬克思列寧學說的人,至少是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缺陷的人。
海協會死也不願和海基會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歷來堅持「一個中國」的模糊概念,是為了在國際上不斷擴大自己的話語空間而縮小對方的話語空間,直到有一天當自己壟斷了話語權時,就可以用自己對「一個中國」的闡釋吃掉對方。把「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改革開放」、「人權」、「民主」、「國家」、「民族」、「所有制」、「市場經濟」、「憲政」、「法治」等等概念,始終保持在模糊的灰色地帶,使人民在一次次的失望後又能永遠產生新的幻想,使特權集團在一次次獲得暴利後又能不斷獲得新的暴利,就是模糊概念的無窮妙用。模糊概念是獨裁者秘密而有效的武器,永遠不要掀起針對模糊概念的爭論。當狼要吃羊時,企圖爭論的永遠是羊,不聲不響地咬住羊的脖子的則是狼。它不需要爭論,因為它的目標和手段從來都是非常明確、毫不含糊的。
2006-3-14
──《觀察》首發(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