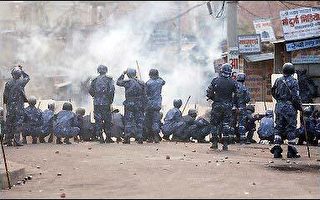【大纪元4月17日讯】近来陈水扁先生的“废统”、“终统”,在华人圈和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大陆的许多朋友也卷入这场纷争。但问起所“废”所“终”之“统”究为何物,则论者昏昏而知者寥寥。
1990年10月7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先生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1991年3月9日开始运作。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促成大陆于1991年12月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第一次谈判1992年3月23日在北京举行,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当时,台湾己开始民主化改革,实施宪政,政府行为必须接受议会的质询和监督,海基会称民间机构,为了不违背宪法,在议会反对党的抗议声中,被限定只能进行事务性协商。但是,大陆海协会在会谈中,要求海基会接受“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签订协议的前提。海基会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一轮谈判失败。
为挽救破裂的两岸谈判,李登辉同意接受“一个中国”,遂由海基会致函海协会,要求海协会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出乎意料的是,大陆拒绝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复函称:“海协会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两岸事务性协商因此而转变成“一个中国”涵义的政治谈判,也就成为是选择统一还是选择分裂的政治谈判。
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案,内容为:
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二、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三、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台湾“国统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案后,大陆对台办、海协会发表声明和谈话,重申两岸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至此,双方均亮出底牌,双方的立场如下:
大陆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底线是井水(民主)不犯河水(专制)。
台湾方面: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中国人,对等,和平民主统一。底线是对等。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第二轮协商,由海协会副秘书长周宁与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主谈。双方交手了下面四个回合。
第一回合,周宁首先提出讨论“一个中国”问题,许惠佑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
第二回合,周宁再提出“一个中国”问题,许惠佑让周宁澄清“一个中国”的涵义,周宁以事务性协商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为由拒绝。
第三回合,双方各自提出五个书面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双方各自拒绝接受对方的方案。
第四回合,为缩小分歧,海基会提出三项修改表述方案,并建议如不能达成协议,可各自口头表述,周宁无权决定是否接受口头表述,大陆海协会退出谈判,谈判破裂。海基会三项修正表述方案是:
一、鉴于中国仍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二、海峡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
三、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香港谈判破裂后,10月31日,台湾陆委会副主任马英九发表谈话,表达立场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如果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们吃掉,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方不能接受不加注说明的“一个中国”原则。
11月16日,大陆海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同意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告知海基会:“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并将海基会三项修改表述方案的第三项作为随函附件云:“附贵会于10月30日下午所提出的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资料引自“凯迪网络•猫眼看人”三百门渔夫:《九二共识真相:大陆与台湾》,原标题:《九二共识真相:“陆独(独裁)”与“台独(独立)”》)
现在人们明白:所谓“统”,就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先生在1990年成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和这个委员会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统一的主旨是自由、民主、均富。所谓“九二共识”,则是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海基会认为“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则坚持“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共识”的要点却是“认知各有不同”。
但马英九先生早在13年半以前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中共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们吃掉”,却是从诸多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先见之明。
“认知各有不同”的概念属于“模糊的概念”。把本来明确的概念故意弄得模糊,则是“模糊概念”。前一个“模糊”是形容词,后一个“模糊”则是动词。“模糊的概念”和“模糊概念”统称“模糊概念”,历来是独裁者的秘密武器。
1945年7月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大言:我们已经找到摆脱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周期律的方法,这就是民主。这次谈话除了令当时的黄炎培先生兴奋不已,至今仍被一些人贯以“窑洞对”的美名。但毛泽东先生所说的“民主”,和黄炎培先生理解的民主,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当时毛泽东运用的就是“模糊概念”的秘密武器。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先生所说的“民主”,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独裁或者一小撮政治寡头独裁。
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谈话是模糊概念,而马克思在156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模糊的概念。当无产阶级还是无产的阶级时,他们是不能专政的;举凡能实行专政的力量,绝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理论,是一种摄魂术,使无产者和穷苦人民产生幻觉,以为他们能够通过实行专政而掌握政权,为自己谋福利。
“言者无罪”源自中国古代文化,原意是发表与统治者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统治者的言论都是无罪的。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有意模糊了这个概念,“言者无罪”变成了发表拥护统治者的言论和意见才是无罪的,而发表“错误的”即批评统治者的意见则是有罪的。
模糊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缺陷,来自逻辑思维不健全。由模糊概念造成的历史悲剧和人间惨案史不绝书。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苏区”、延安和1949年之后的大陆,模糊概念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因为除了原来的模糊概念,又发明和引入了大量新的模糊概念。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就是古代的联邦制,这种制度早在2200多年前就被秦始皇嬴政先生废除了,代之以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上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故意制造模糊概念,断言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封建社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五四运动时倡导“民主与科学”,针对中国专制与愚昧的现实。所谓的“反封建”,却把反专制的主题转移到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上去了,这就为后来保护并扩大专制主义埋下了伏笔。这是共产党在20世纪制造出来的最大模糊概念。直到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复刊的“冰点”上,还使劲鼓吹“反封建”的陈词滥调。
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在其《政治报告》中明确承诺:对于犯罪分子,“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等反革命分子外,其余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凡是杀人、放火、放毒的刑事犯,不论有无政治动机,全都贯以“反革命”恶谥。所以这个承诺本无歧意,就是除了杀人、放火、放毒这三类罪犯外,其余的罪犯一个不杀。但“九大”过后不久,就接连下发“七三布告”、“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等,大开杀戒,并且不断升级,直到1970年初,掀起了疯狂的公开扬言要杀人的“一打三反”运动。对九大报告中“一个不杀” 的承诺,则诡辩道:那个“等反革命分子”,就是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故意的模糊概念,简直连放屁都不如!
我过去讲过一个故事:一群同行的人走到一条大河边,面对如何渡河,意见纷纭,争论不休。忽然出来一个聪明人,提议“采用最佳方案过河”。所谓“最佳方案”,就是超过所有其他方案的方案。至于具体内涵,大家不要争论。于是一致通过。但具体实施时,分歧就出来了。有人认为最佳方案就是建一座桥,有人认为最佳方案就是造一只船,有人认为最佳方案就是泅渡。这最佳方案原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我的故事当时只说到这里。直到后来那个聪明人掌握了一切权力,并且造成了桥,我才明白,所谓“最佳方案”,就是倾共同所有的财力,建一座最豪华的桥梁;从设计到施工,从预算到承包,全都由聪明人独自说了算,财务不公开,不许查账,不许批评;对于建桥过程中需要追加的资金,全都由大伙无条件供给。原来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最佳方案”,后来才明白,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不过是我等愚民,那个聪明人却是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明白。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原先我以为,邓小平先生能说这话,说明他很谦虚。现在我只能引用祥林嫂的一句话:“我真傻!”他早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而“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但是“坚持改革开放”,却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的,“一百年不动摇”。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没有完全搞清楚和完全没有搞清楚的,是我们这些下愚之辈,而不是邓小平先生和他的同僚们。
当邓小平1992年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一些天真善良的人们忍不住又兴奋起来,讨论起“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法制经济”,当然反对的一方也振振有词。于是邓小平及时抛出了他的一项发明:不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在“立国之本”基础上的“强国之路”的延伸。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国家政权垄断下的市场经济,政府继续垄断一切资源,个人的权利继续被压缩在最低限度;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正相反对。幻想市场经济可以促进私有化和民主进程,不过一厢情愿的白日梦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模糊概念,然而却是对公认的市场经济的模糊。
改革开放之初,善良的人们遗憾地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开始的。”官方宣布:“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但为什么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却不允许深入讨论。“企业活力”对于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城市,对于渴望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人民,是一个模糊概念。在中世纪,成吉斯汗的铁骑最有活力;20世纪,希特勒执政后,德国的经济最有活力;中国90年代后期的“圈地运动”开始后,房地产业也一直最有活力。但这样的活力和人民自由与幸福的增长有什么关系?奥运会冠军在赛场上表现出的活力,和躺在医院门外求医不得的病人有什么关系?改革开放如果不能始终惠及下层人民,它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甚至值得诅咒的模糊概念。
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模糊概念。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一句关于共产主义的名言:“如何判断什么样的人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就是那些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反共产主义者呢,反共产主义者是那些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人。”里根先生的话只适合那些良知未泯的人,因而只说对了一半。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拚命为自己捞取特权利益,在专制腐败的道路上绝不回头的共产党人,也是理解了马克思列宁学说的人,至少是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缺陷的人。
海协会死也不愿和海基会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历来坚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概念,是为了在国际上不断扩大自己的话语空间而缩小对方的话语空间,直到有一天当自己垄断了话语权时,就可以用自己对“一个中国”的阐释吃掉对方。把“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改革开放”、“人权”、“民主”、“国家”、“民族”、“所有制”、“市场经济”、“宪政”、“法治”等等概念,始终保持在模糊的灰色地带,使人民在一次次的失望后又能永远产生新的幻想,使特权集团在一次次获得暴利后又能不断获得新的暴利,就是模糊概念的无穷妙用。模糊概念是独裁者秘密而有效的武器,永远不要掀起针对模糊概念的争论。当狼要吃羊时,企图争论的永远是羊,不声不响地咬住羊的脖子的则是狼。它不需要争论,因为它的目标和手段从来都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
2006-3-14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